书家群体现象与书法史研究
在今天,想要界定史学研究的范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在“新史学”的关照下,任何一种研究都变得多维而立体,甚至很难去判断应使用哪些研究方法、运用什么样的研究理念才能准确表达。事实上,历史本来就很难再现。史学研究最大限度彰显着后来者对历史的人文理解和理论阐释,好在今天研究者有着一种“回观历史”或者“俯视历史”的优势,才能弥补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同样,书法史研究隶属于这样的范畴,既要满足书法历史的真实镜像呈现,也要满足艺术史的客观规律需要,如何把客观、理性同主观、感性相结合,有效开展书法史研究,特别是断代书法史研究,则成为衡量研究者学术洞察力的一个标准。
在古代书法史研究上,元代书法史研究大致会有三种倾向:一是赵孟(兆页)作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始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具有覆盖性、唯一性、放大性;二是古代书画鉴藏史中,元代的国家收藏和私人收藏都尽可能为学习者提供鉴赏的便利条件,书画题跋也大量出现。元代是古代书画鉴藏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三是关注了宽松自由的书法环境在不足百年间成就了篆隶复古而未能兴盛的事实,忽视了阻断明代对篆隶的延续和发展。相比而言,元代书法史研究缺少宏观研究成果,而张明《元代馆阁文人群体书法研究》一书,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回答上层建筑的政治取向与制度设置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书法发展这样的疑问。
一
封建社会帝王的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从积极方面看,帝王可以凭借至高无上的权利,制定与书法相关的一切政策,可以利用所有的手段和资源调控书法的发展走向,即便是帝王并不喜欢书法,只要给予一丝青睐就会产生巨大的蝴蝶效应;从消极方面看,帝王完全不在意书法的存在,甚至毫无兴趣而言,但是营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生态环境,仍然可以影响书法的发展。特别是当帝王对某位大臣或者某个活动格外关注时,那么大臣或者活动所涉及的书法也会因为爱屋及乌,发生始料未及的波动。
元代是少数民族政权,部分帝王与蒙古大臣的汉化程度有限,蒙古文、回回文、汉文是朝廷日常使用的三种文字。元代帝王中元仁宗、元英宗、元文宗、元顺帝对于书法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一方面通过设立宣文阁、奎章阁等与之相关的机构,建立完善的馆阁制度和职务制度来保障汉文化的有效传播与交流,所设置鉴书博士一职,前后约11人参与其中[1];另一方面帝王亲自参与讨论书法和学习书法,重用赵孟(兆页)、揭傒斯等汉族文人,提供展示书法的机会,向外界传达对书法的喜爱。作者指出元代帝王从忽必烈时期就开始留意汉文化,但也保持着相对的警惕性,避免被汉文化完全侵蚀。此后仁宗、英宗诸帝,重启科举,建立馆阁,给予汉族文人适当的恩宠。事实上,书法通常是帝王政治的一种手段,并非发自肺腑的爱好,“仁宗、英宗时有宸翰宠赐群臣”就是把书法当成帝王恩待臣子的一种手段,而“书法名家蒙古犹少”[2]应是一种正常状态。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书家拥有的机遇和空间。
作者通过对馆阁制度的深入研究,为学界标记出元代馆阁是一个孕育元代书法的重要基地,不仅主导着整个社会的书法发展趋向,而且培养了赵孟(兆页)等一众文人的书法审美取向,衔接了皇权与书家之间的关联,避免孤立地看待元代书法现象。首先,馆阁是国家政治的中枢机构,有着明确的职责分工,又是国家储才之地,有着严格的选拔要求和稳定的人员构成,绝非一般的群体所能比拟。这种稳定且标准一致的群体研究,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员流动或者取舍造成的研究不足。从作者给出的《元代馆阁任职人员表》来看,这个群体足够庞大,几乎涉及了有元一代大部分士人,想要抽丝剥茧梳理其书法问题,难度可想而知。作者通过对材料反复比对,有取舍,有判断,通过对不同时期馆阁书家及其审美取向研究,指出了元代书法发展的主体是馆阁文人书家群体,也是元代书法复古思潮的主要推动群体。[ 3 ]
其次,作者从馆阁这个制度入手,全面考察馆阁文人群体的书法情况,总结出馆阁文人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多民族、多文化意识形态的融合体,可参考作者《元代集贤院官员构成表》《元代翰林国史院主要官员构成表》等信息;二是以师生、同门、同年为主的强大关系网,如揭傒斯、揭汯父子,马祖常、马武子、马文人父子,许衡一门,王鹗一门,程钜夫一门等;三是以书画为媒介、以题跋为传播交流,如早期宣文阁,后期奎章阁、端本堂等书画活动。正如作者所称,元代馆阁文人群体是一个获取最多文化资源、掌握最大文化权利的群体。
可见,从制度视角进行书法史研究是一种常见方式,诸如唐代、宋代、明代、清代四个时期书法史研究都已经有相关成果。[ 4 ]这种方式是传统史学研究在书法领域的一种延续,有效而稳定。张明的元代书法史研究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即是从元代馆阁制度入手,全面考察书家书法情况。把馆阁和文人群体组合在一起,最大优势就是界定了一个研究范围,且这个范围不是由社会约定俗成,而是由帝王从政治层面制定制度而形成的。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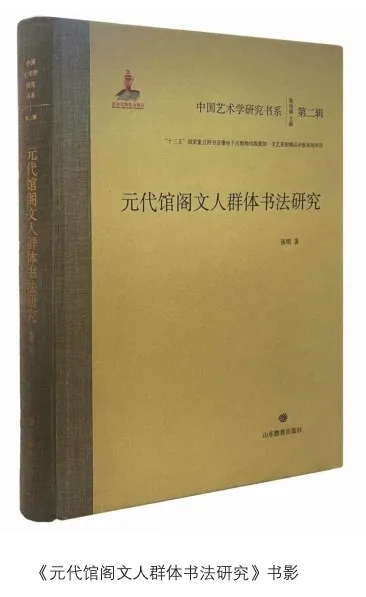
通常群体研究会有三方面优势:一是打破单一的个案研究,把点换成面,通过梳理个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完成整体的统一,既有个性关照,也有共性认知;二是群体现象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特殊群体能够反映社会具有的某种特征或者崇尚,起到一叶知秋、观滴识海的作用;三是群体更需要以“回观”的方式去关注彼此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历史层累过程中,放大或缩小的历史事实。当然,群体研究也有一个困难,即群体的界定及边界划分。以往的群体很难准确划分人物的归属,特别是边界可能无限扩大,研究者试图通过各种文化现象如某书派、某地域、某学派等将其联系在一起,但由于缺少严谨性,不能保障研究范围的准确和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或许从制度的视角会更加合理。特别是元代在很长时期没有实行科举,士人进阶主要依靠举荐的方式,从而使馆阁文人群体的任职流动性不大,相对稳定。这对于了解该群体书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毕竟这个群体代表着上层建筑对于汉文化的最高要求和最大影响而存在。作者关注了元代群体书法具有的四个方面内容:理学、复古、学颜、尚熟。
首先,在元初北方馆阁文人群体的作用下,理学北传并逐渐发展成为元代官学,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儒家伦理秩序,用以维系汉文化正统地位,从而引发了书法“复古”思潮。作者指出元初理学对于元代书法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重视小学、推崇颜书、篆隶复兴三个方面,其中重视小学的书法文字教育是基础,通过这一途径,将书品、人品并重的颜真卿书法纳入元代小学教育体系之中,进而达到明人伦、重教化的目的;同时,通过学习篆、隶书法,回溯文字本源,深究六书之义,以达到传经解道、伦理教化之目的。书法在元代理学家心目中业已成为宣扬礼仪伦常的道德载体,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元代书法观念的转变,开启了书法复古的先声,也为后世书法复古思潮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总之,元代理学的发现,解决了元代书法复古思想的根源问题。
其次,复古和赵孟(兆页)是元代书法史研究的两个重要核心问题,也是学者们津津乐道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两个问题也成为研究的关键。对于元初书法的复古,作者重点关注了王磐、姚枢、王恽、杨桓四人书法,并举《元初馆阁文人善书者统计表》。尽管元初的复古并未引起多大关注,却为此后赵孟(兆页)复古提供前期铺垫。赵孟(兆页)的高光时刻应是元成宗召写金字藏经的事件[5],此后的赵孟(兆页)不仅成为整个文艺领域的典范,也成为元代书法复古最彻底的践行者。然而作者把赵孟(兆页)置于馆阁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自然就有不同的认知与理解。作者弱化研究赵孟(兆页)书法艺术问题,仅仅从赵孟(兆页)的复古思潮、文人群体对赵孟(兆页)的解读、以赵孟(兆页)为典范的伪复古三个方面探讨。赵孟(兆页)作为元代书坛的重要人物,其具有的楷模作用不言而喻。时人学习赵孟(兆页),更多的是对赵孟(兆页)持有信任和遵从。今天,研究者并不过多地探讨赵孟(兆页)的缺点以及对于书法的一些负面影响,实际上这对于学习赵孟(兆页)并不意味着是一件好事。客观上讲,全面了解书家及其书法特点才能有效学习其书法艺术。在这样的思考下,作者认为赵孟(兆页)书法仍属“今”的范畴,虽然超越宋人,却未及唐人,而元代对于赵孟(兆页)书法的学习也存在一种盲目跟风的现象。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解赵孟(兆页)。
再次,元代对于颜真卿书法的推崇成为一个新焦点,这是在以往元代书法史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作者指出元代馆阁文人崇尚颜真卿书法有三方面表现:一是人品的崇尚;二是与王羲之并称;三是应用在小学教育中。作者的这个研究视角,打开了元代书法史研究的视野,借此可以继续了解李邕书法是否在元代流行,唐人对于宋元书法的影响具体有哪些特征,等等。如果大胆地去试想一下,宋代金石学的兴起是否增加了唐代各种碑刻的拓本流传,元代是宋代金石学后第一个受益朝代,拓本与《阁帖》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馆阁群体书家?很明显,从书法传播与接受的角度来看,元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期,仍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朝代。
最后,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是对晋、唐、宋三个时期整体书法风尚的一种总结式概括,深入人心,也成为学者研究这几个时期书法史时所依据的普遍标准。之后元、明、清三代的书法风尚也成为关注的焦点且各有理据,或是认同并直接沿用梁(山献)所称“元明尚态”,或是不再统一考虑时代特色而出现多元评价,或是以非书法的标准来衡量其书法特征。按照书法发展需要,元代也一定会存在某种书法崇尚或书学理念,但现实的研究中较少提及这方面的内容。作者通过梳理元代书法史料,以“尚熟”来审视这个时期的书法问题。作者认为元代继承了唐宋人对于“熟”的推重,其中郝经是“尚熟”理论的倡导者,赵孟(兆页)则是“尚熟”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由“熟”带来的兼通、复古观念,在实践中就有着对古法的过度推重及书写速度较快等特点,这些问题在元代书法理论著作中却更多表现出对书写技法的探讨。
作者所阐释的理学、复古、崇颜、尚熟等问题,都具有馆阁制度的背景,这在很大程度上夯实了研究结果。从馆阁书家群体出发,探讨思想观念、认知崇尚具有的普遍性,避免了以偏概全和盲人摸象的错误认知。
三
作者在书中始终围绕馆阁文人群体探讨书法问题,虚实结合,无论是制度还是风尚,都体现出一种稳定性,这或许就是制度框架的优势所在。即便是在众所周知的元代书画鉴藏问题上,作者独辟蹊径地注意到了王恽和袁桷,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独具慧眼。在整部书中,作者突出强调了郝经、王恽、柯九思、虞集等馆阁文人对书法持有的真知灼见,而且在很多问题上还是关键所在,这些在书中揭示的诸多细节都需要我们读书之余细细品味。
客观上看,元代书法史研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影响这一结果的元代历史研究也以一种式微的方式存在。在传统汉文化的思想领域中去审视元代,很容易把少数民族的思想、观念、习俗从中华民族的大文化中剥离出去,既孤立看待汉族士人的书法现象,又混同了汉蒙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对于少数民族书家的影响。如果我们试着从一种全球艺术史的角度去看待元代的书画艺术,把属于元代这个时段的书法发展置身于一种蒙、满艺术史的长河中去考察,或许能够收获一种对于元代书法新的认知。换言之,书法作为汉字独有的文化表现方式,如何在经历北魏、元、清等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后依然绵延有序、传承久远,就变成了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借助作者的研究成果,或许能为今天的元代书法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考:少数民族政权对于制度的建立既有承袭,也有创建。然而面对汉化问题,少数民族统治阶层并未达成一致的认同,相反这种态度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了制度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因此元朝政府对于汉文化的态度决定着元代书法的走向和发展。既然馆阁文人群体书家有着自由的书法生存环境,为何元代没有出现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理论著作?或者说元代士人对于书法的认识为什么难以升华到一种著述要求?元代虽然立国较短,但是书法仍然有宗唐、宗晋之分,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仍需探求。赵孟(兆页)书画造诣极高,然学术修养难以比肩宋人,政治上不能一展抱负,即便主盟过南方文坛,也很难说他代表了元代的文学水平,所以赵孟(兆页)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书家,仍然值得讨论。
总之,张明《元代馆阁文人群体书法研究》一书为我们展示元代书法研究成果的同时,更为我们思考元代书法史问题提供了研究思路和途径。
注释:
[1]黄君.北方书法论丛[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464.
[2]马宗霍.书林藻鉴[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50.
[3]张明.元代馆阁文人群体书法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22:4.
[4]从制度视角进行书法史研究的成果有:闫章虎.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9.李慧斌.宋代制度视阈中的书法史研究[M].海口:南方出版社,2011.张金梁.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陈佳.清代朝廷书法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
[5]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16.
作者:聊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本文责编:常海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