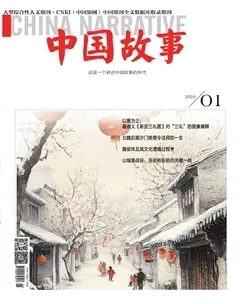驴头太子:《红史》与说唐小说的交汇点
【导读】《红史》是一部概述佛教起源、中原王朝历史和藏传佛教发展的藏族史籍。《红史》在对唐朝历史的记载中虚构了驴耳国王这一形象,该形象可能来源于史料和佛经故事的文学加工,并可能对后续清代说唐系列小说驴头太子的形象塑造产生影响。本文从这一虚构人物形象出发,分析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元明清三朝皇室基本都崇信藏传佛教。在长期交往交流中,汉藏文化出现了明显的交融现象。藏族史籍《红史》就体现了中原文化、藏文化以及佛教文化三者之间的交融。
一、藏族史籍《红史》对驴耳国王的描述
《红史》由蔡巴司徙·贡噶多杰撰著,创作于公元1346年,成书于公元1363年。它不仅是一部藏族地方史籍,还是一部从周朝到元朝时期的中国通史,内容虽然简单,但基本符合历史。但是,其中关于唐代武则天时期的一段文字记述却充满荒诞,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另外一个故事中说,女皇当初生了一个长着驴耳朵的儿子,因为羞惭,在儿子幼小时就派人去杀他,当时有一位吐蕃的大臣,没有让杀皇子而悄悄带去抚养……当女皇去世后,办理丧事时,吐蕃大臣将长驴耳朵的皇子领来,立为皇帝,称为驴耳国王。据说武则天母子二人的陵墓现在还在乾州以北的地方。女皇武则天被吐蕃人称为阿则老母。这个故事的说法不见于史籍的记载。”
《红史》对本故事的记载摘自《唐书·吐蕃传》。根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史料对照,这段记载是杜撰的。《红史》采用文学加工的手法,记述了武则天诛杀自己孩子的历史事件,并巧妙地借助吐蕃大臣的形象来遮盖武则天收复河西和西域的壮举。在这一时期,吐蕃处于劣势,多次请和于武则天,包括吐蕃的噶尔家族归降唐朝以及赞普向唐朝请和等事件。《红史》通过强调吐蕃大臣辅佐驴耳太子登基的功劳,从而塑造吐蕃大臣高大的形象,体现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
二、《红史》驴耳国王的来源分析
《红史》是与佛教有关的藏族史籍,故而从佛教故事寻找来源也是重要的途径。《红史》创作于元朝末年,王朝统治较为动荡,但西藏地区相对稳定,反元势力还未进入西藏。西藏的佛教经过元代几十年的发展,已是流派众多,影响广泛。当时西藏地区积极吸取中原文化,元朝刊印的有关唐朝的史书以及佛经也会引起西藏僧俗的注意和涉略。
(一)史籍关于吐蕃立唐朝皇帝的记载
在记录唐代的史籍中,首推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与《新唐书》。这两部史书均对吐蕃拥立唐朝皇帝的事件有所记载。具体而言,成书于公元945年的《旧唐书》记载:“戊寅之日,吐蕃军队进入京师,拥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并强迫前翰林学士于可封撰写制书进行册封任命。”而成书于公元1060年的《新唐书》则记载:“戊寅日,吐蕃军队攻入京师,拥立广武郡王李承宏为皇帝。”《旧唐书》写成于五代时期,北宋文人认为《旧唐书》内容过于繁杂,于是欧阳修和宋祁受命编纂了《新唐书》。当《新唐书》颁布之后,《旧唐书》书基本不传,故而西藏僧俗很难看到。《新唐书》在北宋编纂完成后,受到了南宋及元朝的多次刊印,因此西藏地区的僧侣与民众很有可能阅读到《新唐书》中关于吐蕃拥立唐朝皇帝的史料,再经本民族加工与融合,最终成为了《红史》中的内容。我们可以推断,《红史》中提及《唐书》,应当是指《新唐书》。
关于唐朝时期的历史记载,还有一部史书不可忽视,即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编纂,并经由皇帝赐名的《资治通鉴》。该书于1084年最终完成,随后在杭州等多个地方进行刊印。元朝时期,《资治通鉴》也得到了刊印传承。我们现今阅读的《资治通鉴》,实际上是清朝学者依据元朝刊印版本重新印制而成的。《资治通鉴》记载了763年10月吐蕃攻入长安等事件:“戊寅,吐蕃入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礼之孙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相”。元朝时曾在杭州刊印《大藏经》,西藏僧俗在此地人数较多。因此,《资治通鉴》关于吐蕃立唐朝皇帝的记载也很可能被引用于《红史》之中。
吐蕃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之事在《红史》中有提及,由此可见蔡巴司徙·贡噶多杰是知道这段历史的。《红史》对吐蕃大臣立驴耳皇子当国王这一记述很有可能是作者的误用。
(二)相关佛经故事的记载
根据韩林博士对武则天驴耳儿子的研究,“北凉昙无谶所译《大方等大集经》中,记载了这则国王的夫人生下一位驴头人身的孩子的故事”认为驴头人身最早的源头是出于佛经,具体出处在隋朝人那连提耶舍译的《大乘大方等日藏经》中。文中描述大致是:王后行荒诞之事后生驴脸儿子,但是此驴脸人身之人与佛有缘,他坚持苦修,坚定信仰佛法,从而成为仙人。这个荒诞的故事论述了佛法普度众生的作用。佛经《大方等大集经》据传与龙树菩萨关系密切,龙树亦被藏传佛教奉为六庄严之一。德格版《大藏经》中的《大方等大集经》也收录此故事。可以看出,在西藏地区,王后生驴头儿子的故事随着佛经不断传播,极大可能影响到编纂过《大藏经·甘珠尔》目录的蔡巴司徙·贡噶多杰。在佛教盛行的藏区,《红史》借鉴佛经中王后生驴脸儿子的故事来影射武则天。武则天称帝后男宠众多,“初为宠臣张易之及其弟昌宗置控鹤府官员,寻改为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故而蔡巴司徙·贡噶多杰记载的驴耳太子故事也极可能来源于《大方等大集经》。
总的来说,《红史》中关于驴耳国王的记载应该有两大来源:其一是对安史之乱时期的吐蕃立广武王为帝这一史料的误用,用以凸显吐蕃的历史地位,其二是借鉴《大方等大集经》中的佛经故事,突出教化众生的思想。
三、《红史》对说唐系列小说的影响
说唐系列小说主要出自清朝的儒家文人士子之手,多为以历史为主干,杜撰传奇故事,文学色彩浓厚,属于民间通俗读物。说唐系列小说出现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之后,为了满足民间对世俗读物的需求,儒家文人士子便用儒家道德礼教来教化万民,说唐系列小说对武则天的贬低便是儒家礼教思想的体现。
“驴头太子的创作思路可能来源于佛经,但骡头形象则是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封建社会,女人掌权是遭到抵制的,尤其是程朱理学兴起之后,封建伦理观念更加盛行,广大妇女沦为男人的附庸。武则天虽然作为史家唯一承认的女皇,但始终遭到不断的诋毁。明清时期,人们普遍对武则天进行贬低,甚至对她进行歪曲事实的编写,将其描绘得荒淫无度。其中“在说唐系列小说中,武则天被塑造成红颜祸水,与忠臣良将成了死对头。”清代乾隆年间的通俗小说《薛刚反唐》便是说唐系列小说之一,书中的骡头太子就是直接批判武则天的。
骡子是马与驴的杂交,无法再生育,小说以此对武则天进行讽刺。我们还要注意到,为什么会有骡头一称呼,骡头又是源于哪里?从《薛刚反唐》中吴奇、马赞的嘲讽语句可以看出,骡头太子与驴有密切联系。清代另一部说唐系列小说《说唐三传》中也有类似的故事,但是却用驴头太子进行称呼。两个小说相比,骡头太子即是驴头太子,而骡头太子更能体现当时文人对武则天的嘲讽,但是继续追其源头出于何处呢?
说唐系列小说可能引用了《大方等大集经》中驴唇仙人的故事,或者藏族史籍《红史》中驴耳国王的文学论述。在清朝时期,藏传佛教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民间的通俗文学极有可能受此熏陶。乾隆皇帝笃信藏传佛教,七十大寿时,特邀六世班禅进京。乾隆尽管已经七十高龄,仍亲自迎接年仅四十余岁的六世班禅,并谦逊地向其请教,自称幸见喇嘛。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针对儒家文人对乾隆笃信藏传佛教的谏言,乾隆作关于藏传佛教政策的《喇嘛说》一文,其中提到“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从上述两起事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支持,这也会促使儒家学者深入研究藏传佛教的经典。因此,有理由推测,说唐系列小说中骡头太子(或称驴头太子)的形象,其灵感来源于藏族史籍《红史》中对驴耳国王的记载。
但是在儒家思想中,驴头太子当国王这种结局不符合其价值取向,故《薛刚反唐》等说唐系列小说虽然也借鉴了驴头太子的元素,但结局却大相径庭:《红史》中该角色最终称帝,而在《薛刚反唐》等小说中,却被处死。这反映了不同作者根据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化需求,对故事情节进行了不同的改编和结局设定。
四、结语
“中国的疆域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在相对稳定的地域之内诸多民族间形成了以经济交流为主导的文化交流,在不断地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中,融溶成新的文化。”从文学作品相互渗透的内容可以看出,诞生于不同时代的作品,虽然有不同的创作目的,但它们共同揭示了我国各民族之间持续不断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参考文献
[1] 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9-09/27/c_1125048317.htm
[2]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3] 陈庆英,高淑芬. 西藏通史[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4] 沈卫荣. 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5] 蔡巴·贡噶多杰. 红史[M]. 东嘎·洛桑赤列,陈庆英,周润年,译.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6]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7]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8]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9] 韩林. 文化怪胎——驴头太子形象解析[J]. 明清小说研究,2014(4).
[10] 大正新修大藏经[M]. 大藏经刊行会,1924-1935.
[12] 韩林. 武则天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D]. 天津:南开大学,2012.
[13] 佚名. 薛刚反唐[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
[14] 乾隆. 乾隆御笔喇嘛说[M]. 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1998.
[15] 陈育宁. 民族史学概论[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