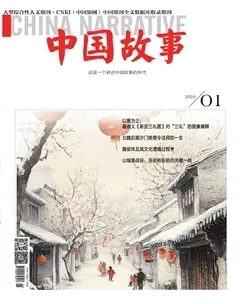刘亮程《虚土》创作的地理基因与地理想象
【导读】小说《虚土》是刘亮程从散文创作转向小说创作的首部作品,在其长篇小说序列中也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受地理基因影响较大。作品中的自然地理景观独具北疆特色,这种特色不仅深刻塑造了叙事主体与读者对于世界秩序的认知,还引领他们体悟生命哲思。这些景观与刘亮程在现实世界的亲身经历紧密相连、相互映照,进而影响并形成了刘亮程独特的创作视角——即“站在新疆看全国”。本文主要从地理基因、地理想象的角度分析刘亮程《虚土》创作的艺术根源、生成机制以及对文学与地理双向交流的显著推动作用。
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强调了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决定性作用,但局限在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而没有全面地探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双向关系。为了弥补单一“地理环境决定论”阐释文学现象的不足,邹建军在2012年提出了“地理基因”的概念,这一概念补充了社会历史批评在解释地理环境对作家个体影响方面的不足,推动了人与自然双边关系的全面探讨。该理论认为一个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是由地理环境基因、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三方面综合产生的统一体,并通过作家的语言文字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因此,要清晰理解文学作品中地理基因的作用,我们需要将作家与作品统一起来进行分析。
《虚土》作为刘亮程的第一部小说,延续了他散文创作中关于北疆的地理感知、地理审美、地理记忆与地理思维。《虚土》可被视为刘亮程具有自传性质的生命之书,凝结了四十四岁的刘亮程对父辈从甘肃逃荒到新疆的经历和本人在新疆成长的生命体悟。因此,从地理基因的角度分析小说《虚土》,我们能见证新疆沙湾县的自然环境基因、甘肃金塔的家族基因和家族文化传统的社会基因在刘亮程身上留下的烙印,以及地理感知、地理意象、地理记忆、地理思维等中介形态对《虚土》创作的影响。作者基于身上的地理基因将各种地理要素融合,构建出一幅幅生动的地理图式,最终以文学反哺地理,促进新疆地域的文化建构。
一、地理基因:《虚土》创作的艺术起源
地理环境不仅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也对作家创作起着基础性作用。《虚土》地理叙事的独特性与作家刘亮程的地理基因密切相关。
首先,刘亮程的地理基因主要是在新疆沙湾县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刘亮程在新疆出生,他在新疆沙湾县的老皇渠村和太平渠村度过了童年与青年。1961年,刘亮程一家为了逃避饥荒,从甘肃迁往新疆,最终在老皇渠村挖地窝子定居下来。时隔一年,刘亮程出生。八岁时,父亲去世,跟奶奶一并葬在玛纳斯河畔。十二岁时,母亲改嫁,刘亮程离开了老皇渠村的地窝子,随后迁往老皇渠村北部几十公里处、玛纳斯河下游的太平渠村。刘亮程曾在采访中说:“在这个村庄生活的十年,是从少年长到青年,对我人生影响最深的十年。”虽然他在1993年就离开了沙湾,在外工作了三十年,但是他所有的写作其实都在写这块地方。
刘亮程的创作源头可以追溯到太平渠村,那里的山水草木为其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与动力。太平渠村位于老沙湾镇北部,常年处在西风带上,气候干旱,临近玛纳斯河,沙湾县中部的洪积——冲积平原,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日照充足,土壤肥沃,适合种植小麦、棉花、苞米等农作物。北面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位于准噶尔盆地南缘的缘深地带,荒漠面积大,有多种沙漠植物——梭梭、红柳、胡杨、芨芨草等。玛纳斯河岸河湾多,水草条件好,适合畜养牛羊等动物。不管是玛纳斯河、金黄的麦田,还是北面远处的荒漠,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在作家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刘亮程在小说中描绘了大量北疆平原与沙漠地带的自然地理意象:麦地、沙漠、玛纳斯河、地窝子、老奇台、黄沙梁、八分地、柳户地、下野地、胡杨地、高土台、沙门子、戈壁、荒滩、铃铛刺、红柳、沙枣林带、榆树、灰蒿子、茼蒿、榆钱、蒲公英、苞谷、麻等。村庄的命名要么是根据具体生产地命名,要么是根据新疆的地貌景观和地形特点命名。刘亮程敏感地捕捉到了很多细微的地理意象,并将其运用于小说《虚土》中,凸显了新疆沙湾县的风光之美。
其次,刘亮程从父亲身上继承了甘肃金塔的家族基因。自小在新疆长大的他只有真正踏上故地,感受家族的亲缘关系与留存的历史资料之后,才能认领这个家乡。刘亮程曾论及家乡与故乡的区别,家乡不仅是一个人出生、成长的地方,更是和一个人血肉相连的地方。故乡存在于深埋祖辈的地下,是一个人精神血脉的延续与归属。由于父母逃荒的经历,刘亮程认为每个人的家乡都需要在历史的尘埃中去找寻、认领。以前刘亮程认为甘肃金塔只是父母的家乡,跟他没有关系,而当他站在叔叔家麦田中的祖坟前时,“我突然觉得,它是我的家乡”。
最后,甘肃老家的刘氏家谱和祖坟可证,刘亮程身上潜藏着中国古代家族文化的社会基因。他在对祖坟和家谱的观摩中,明白了“生命从来不是我个人短短的七八十年或者百年,而是我祖先的千年、我的百年和后世的千年,世代相传”,“因为有家乡,我可以坦然经过此世,去接受跟祖先归为一处的永世”。刘亮程将自己置于祖先与后代相接的宗族秩序和时间序列中,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迷茫与困惑。
刘亮程身上的地理基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伴随着行居环境改变,新旧地理基因碰撞与融合,拓展了刘亮程文学创作的地理视野。刘亮程因工作变动离开了太平渠村,去乌鲁木齐当编辑,也多次去南疆采风创作。如果说刘亮程第一部小说《虚土》中的地理叙事仍是围绕着生长之地——太平渠村,那么第二部小说《凿空》的地理叙事则是围绕着南疆村庄的古今之变进行书写。刘亮程小说创作中地理视野的拓展,以及他秉持的“站在新疆看全国”的创作观念,与他多年来在新疆广泛游历所积累的地理知识密不可分。
刘亮程的地理基因为小说《虚土》奠定了创作基础,他通过地理感知、地理审美、地理记忆、地理思维等中介形态,构建了一个展现新疆沙湾县自然乡村风光的独特艺术世界。
二、地理想象:《虚土》创作的生成机制
刘亮程在描写太平渠村自然实景的之外,对新疆北部准噶尔盆地南缘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一带,展开充分的地理想象。他将新疆的戈壁滩、沙漠景观和玛纳斯河孕育的绿洲景观并现,将虚土庄及其周围的村落有机联系起来,建构了一个意象丰满、形式新奇、虚实相生的虚土世界。总的来看,《虚土》创作呈现出了刘亮程地理想象的三个特点:
首先是三种地理想象图式。一是以虚土梁上、门前有一棵沙枣树的七口之家为中心的地理图式,讲述这一家的离散故事。这一地理图式与刘亮程的童年经历相互指涉。刘亮程幼时居住的地窝子前就有一棵大榆树,父母与兄弟姐妹五人构成七口之家。这一部分蕴含着作者大量童年的地理记忆,入情地诉说着童年的孤独和家人的离散。那个因看见了一村庄人离去而永远被留在了虚土庄的五岁小孩,就是刘亮程经历了丧父之痛的童年化身。创伤性的心理经验使得某个瞬间在心理空间无限延展。
二是以虚土庄为中心的地理图式,讲述了一个村庄的人逃荒、在时间中漂泊的故事。甘肃千年村庄的村民因为逃荒,一路西行到新疆,在戈壁滩西面的虚土梁上建造房屋、短暂定居。他们原本应继续向远处迁徙,但一部分人不愿离去,另一部分人做顺风马车的买卖,不停往远处奔走,也由此建立起虚土庄与其他村庄的联系。最终在远处奔波的人们发现,已经没有别的荒野可供他们居住,他们只能生活在虚土庄,于是又从远处踏上回家之途。
三是以虚土为中心的地理图式,讲述关于生命的终极奥秘。虚土是新疆戈壁滩上的一种特殊盐碱土,表面有一层硬壳,敲碎后就可见藏在下面的虚土,虚土之下掩埋着生命存在过的痕迹。虚土也象征着生与死之间脆弱、模糊的界限。“一个一百年的村庄,可以在三米深的土里找到人的脚印”。人留在空气中的痕迹常被西风吹散,人在地面上的痕迹却因为天上落土得以保留。
其次是与自然意象相交织的地理想象世界。刘亮程在《虚土》中拒绝用现代科学的知识体系来描述虚土世界,而是用五感的直接经验与心灵洞开的直觉来描述。例如,他对于时间的感知源自于农作物的播种与收获、衣物的磨损程度以及农具的使用损耗等;而对于空间的认知,则是通过日升月落、气候变化以及风向等自然现象进行判断。虚土庄的人都以自然中存在的事物来丈量村庄。他的小说字里行间透露出自然气息,也与其想象与建构的区域自然意象群相关。比较重要的自然意象有风、树叶和尘土,它们贯穿于小说关于生命存在与存在本质的主题探讨。刘亮程构想的虚土庄由村庄本身、地下村庄和梦中村庄三部分组成,与其相对应的是地上、地下和天空的位置,与三个位置相对应的是这个地方的三层生命,“上层是鸟,中层是人和牲畜,下层是蚂蚁老鼠。三个层面的生命在有月光的夜晚汇聚到中层:鸟落地,老鼠出洞,牲畜和人卧躺在地”。这时人的梦飘飞到最上层,死后葬入最下层,和蚂蚁老鼠为邻,鸟死后坠入中层,蚂蚁、老鼠死后身体被太阳晒干,被风吹到最上层。在刘亮程看来,天、地、人三个层面的生命可以通过风实现相互交流,最终的结局是天上落土,把所有生命的痕迹都埋藏在虚土之下,整个世界是土的世界。
最后是生命感悟与哲思相交织的地理想象情境。《虚土》在对人生目标与生命真谛的追问中,将时间空间化是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刘亮程用道路这一地理意象来表征人生,认为人生就是一场出走与回返的孤独旅程。每个人的一生就像从村庄的大路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小路,每个人探索出来的道路都只适合自己,无法在远处汇合,但可以在回到过去的路上相遇。尽管每个人都想把村子带到自己的路上,但是一个村庄不可能走上只有一个人知道的路,并且“每个人在心中独自经历的事情,比大家一块经历的要多得多。每个人记住的,全是不被别人看见的梦”。因此生命的本质之一是孤独,彼此之间有时是不可沟通的。刘亮程用蒲公英来象征生命的多种可能性。在他看来,人的生命轨迹与蒲公英具有同构的关系。刘亮程在提笔写作《虚土》时正处于四十余岁的年纪,内心对生命感到空茫、恍惚与孤独,便通过写作小说《虚土》参悟生命的本质。他看到每个人都有内心与现实的两副面孔,一副面孔是五岁的孩子,象征着人的童年;另一副面孔是在远方独自长大、成熟的我,象征着人的成年。他也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的目光在家乡,另一只眼睛的目光在远方。人如果不曾去过远方,就不会安然地居于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如果远去历练了一番,归来后就平静安然、从容自若。
三、“文学—地理”:文学创作与现实建构的双向交流
地理基因理论强调文学创作与现实环境的双向交流关系。或许用现实环境一词来代替自然环境更为恰当,因为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除了自然环境基因以外,还有生命基因、地理环境基因。作家在文学作品中的地理建构不仅会涉及自然环境中不同地理要素的重新安排,也会涉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考量。因此,作家从文学与地理双向交流的角度,更能展现文学创作中地理叙事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
首先,刘亮程通过《虚土》记录了20世纪60年代从甘肃、河南移民到新疆的汉族人民艰难的创业史和心灵史,具有历史价值。刘亮程的逃荒故事以父母的逃荒经历为底本。这些移民离开家乡,艰难地寻找一块适宜种植的生存之地,生存是他们的第一要务。他们循着一个方向前行,想知道停下来的地方是否适宜生存,也需要询问当地的村民,可能得到善意的反馈,也可能受人欺骗(例如虚土庄的人就曾受到黄沙梁村民的欺骗)。最终,甘肃移民在靠近玛纳斯河的虚土梁上安了家,由此虚土梁有了人居住,成了虚土庄。整体看来,行走和定居的过程中充满艰辛,但他们从未放弃生的希望。
其次,刘亮程小说的地理叙事勾勒了沙漠边缘、玛纳斯河岸的自然地理景观,展示了西风带上独具特色的北疆风光,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刘亮程以诗意的、直觉性的语言在清晰与模糊之间、在生命的睡与醒之间找到一种生命真实的表达。其一,刘亮程在《虚土》中实践了向梦学习文学创作的理念,他认为文学表达的技巧早就在作家生命早期的梦境中反复呈现,逐渐被作家习得。其二,虚土庄的人正是因为做梦,使他们具有了“在高处”的视野,“梦把天空顶高,将大地变得更加辽阔”。如果我们把目光只聚焦于当下,我们对于未来的生活会感到迷茫,在通往目标的路上也会迷路;如果我们把目光置于由生到死的百年时间序列之中,我们就能从整体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处境,面临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其三,《虚土》的叙事结构建构在多个虚土庄人的讲述之上,阅读的过程就是把梦的碎片一片片还原的过程,也只有读完整部作品,才能懂得刘亮程想表达的关于生命的主题。
最后,《虚土》取得的文学成就也会反哺新疆沙湾的地域文化建构,促进读者对新疆沙湾县的地理认知与地理审美,推动新疆沙湾县及周边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实现文学与地理的双向交流。刘亮程在新疆木垒县菜籽沟村的古老村庄建造的艺术家村落以及木垒书院,也正是依循着这一思路。他的文学成就会吸引更多的艺术家入驻菜籽沟艺术家村落,丰富新疆菜籽沟村的文化建构,深化地方的文化底蕴,也会吸引更多的读者、旅行者慕名而来。这不仅能够带动该地的经济发展,也为在现代化城市打拼、身心俱疲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供肉体与灵魂栖居的精神圣地,让新疆悠久而璀璨的文化走进更多人的内心,实现文学与地理的双向交流。
参考文献
[1] 邹建军. 江山之助[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2] 刘萌萌. 寻找“黄沙梁”——走进刘亮程的童年与故乡[OL].(2023-08-21)[2024-06-2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4829136902467050amp;wfr=spideramp;for=pc.
[3] 刘亮程. 把地上的事情往天上聊[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4] 陈颖,刘亮程. 新疆给了我一个看全国的视角[N]. 新疆新闻出版,2014(4).
[5] 孙正国,李皓.“惟山体”创作的地理基因与地理想象[J]. 当代作家评论,2020(2).
[6] 刘亮程. 虚土[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