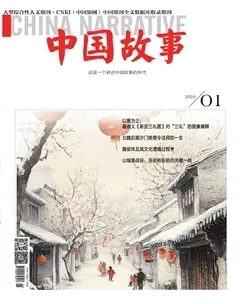性别书写视阈下的翟永明诗歌研究
【导读】翟永明诗歌中充斥的黑夜意识、死亡意象和反复出现的自白语调,呈现出鲜明的女性个体意识,标志着女性意识的崛起。本文以翟永明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为考察对象,从性别书写视阈出发,结合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成果,从文本主题、叙事风格、叙事方法三个方面切入,剖析翟永明诗歌多元、丰富的性别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叶,女诗人翟永明一组名为《女人》的组诗在《诗刊》发表,随即引起学界大量关注与强烈反响。著名批评家唐晓渡撰文称:“《女人》组诗的诞生,启示了一种新的诗歌意识。”翟永明独特的创作模式,为文坛中挣扎苦闷的女诗人们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并成为中国“身体写作”方法的发端,影响了其后林雪、唐亚平、海男等一批女诗人。提及性别书写,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此前的女性创作。从朦胧诗诗人舒婷开始,已有女性意识的萌芽,舒婷在诗歌中大力宣扬女性主体意识,力图瓦解传统的男性宏大叙事,虽未见成效但已是先声。
翟永明则进一步带动女性主义诗学向性别诗学过渡,性别诗学作为对女性主义诗学的更高层次发展,被视为是女性主义的理想国。而正如济南大学成红舞教授所言,完成女性主义诗学到性别诗学的转变是非常艰难的过程,需要处理好女性主体、身份和权力的三大问题,才能正确定位,从而建立两性和谐的性别诗学。翟永明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宝贵的探索,并具体体现在了创作实践中,她以身体叙事为方法,在诗歌中注入“黑夜”“家庭”等元素,采用自白式话语,突出表现了女性个体意识,并将女性个体放在历史、社会整体中,寻找除了被囚禁的女性“小我”之外的“大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典例”或“范例”。此外,翟永明不满足于性别意识的单纯表达,将女性身体塑造为超性别角色,以此来打破单纯性别视角的局限,打破过往性别写作常规,传递超性别意识。
一、“黑夜”与“家庭”——囚禁场和希望地
正如美国诗人杰佛斯所言:“至关重要,在我们身上必须有一个黑夜。”对很多诗人作家而言,黑夜是一个舞台,万籁俱寂之时,他们灵感迸发,创作行云流水。而对于诗人笔下的女性形象而言,黑夜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黑夜中的女性可以袒露白日难以抒发的情绪,可以在月光下审视压抑的秘密。同时,“家庭”常与“黑夜”伴生出现。家庭作为女性生儿育女的场所,是充满生命气息的希望地,但同时也是一个物欲横生的空间,在这里女性被囚禁,欲望不断生发而又被压制,与其说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不如将它归结为一种普遍的女性生存状态。
先谈“黑夜”,翟永明在《黑夜的意识》中谈道:“对女性来说,在个人与黑夜本体之间有着一种变幻的直觉。我们从一生下来就与黑夜维系着一种神秘的关系,一种从身体到精神都贯穿着的包容在感觉之内和感觉之外的隐形语言,像天体中凝固的云悬挂在内部,随着我们的成长,它也成长着。”在翟永明的诗歌中,“黑夜”本身或相关的意象高频率出现,承载特殊的意义。翟永明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代表女性权益的黑夜世界,与代表男权的白昼世界相对立。我们来看翟永明的诗《蝙蝠》:“蝙蝠只是蝙蝠/夜晚的使者白天的敌人/一个干枯瘦小的孩子/它是黑色的不眠者的灵魂”。蝙蝠亦可与黑夜相联系。蝙蝠的活动时间大部分在夜晚,它的到来意味着黑夜的降临,蝙蝠仿佛黑夜的使者,蝙蝠的活动时间限于黑暗,黑夜是它的囚禁场。翟永明将蝙蝠形容为干枯的、瘦小的孩子,与其本身形象充分匹配。干枯瘦小的是蝙蝠,同样也是在黑夜中被禁锢的女性,干枯的不只是身体,还有灵魂。我们还可以想到,黑夜同样凝聚着希望,在黑夜里女性可以打破白日的失语,大胆地表露自己的心声和情感。
再谈“家庭”,家庭是女性生活和生存的基本空间场所,在这里有生命的诞生和逝去,充满希望,同时又是女性的囚禁场,家庭生活循环往复,构成一种基本的生活状态。以翟永明在《编织与行为之歌》中重写的《木兰诗》为例,《木兰诗》中的女子在战争平息、朝廷封赏后回到了原有的家庭,回到了传统观念中给女性安排的位置,“是什么使得木兰双手不停?诱惑她的战争已经平息”,“日子重又简化:唧唧复唧唧”,在重复单调的平淡日子里,木兰似乎磨灭了往日战争时期所特有的激情,在纺织机的机械声中重复传统的女性生活节奏,似乎过去的征战生活只是南柯一梦。回归传统男耕女织模式的木兰,以有规律的生活模式替代了突发式的、难以预测的战争日程,似乎这是传统认知中女性最好的归宿。但这又是一个囚禁场,“她置入一颗孤独的心,消耗她的激情于是平静”, 此时的木兰和中国绝大多数传统女性一样,成为家庭生产的基本力量,也仅限于此,没有进入实质的消费系统。
翟永明的另一首诗作《黑房间》同样是家庭叙述的典范,诗作开头即有“天下乌鸦一般黑”一句,乌鸦与上述“蝙蝠”相同,同样可视为黑夜的代表,《黑房间》主要结构内容也是由“黑夜”和“家庭”组成,分别指代女性对父权的反抗以及由丈夫和父亲共同组成的男权社会。《黑房间》主要叙述的对象是四位少女,她们身处的黑色房间本来是属于她们的私有空间,但出现了“越过边境、精心策划的人”,即进入房间的男性。因此原有的边界被打破,女性不得不在黑色房间里设置圈套,用以自我防卫。在黑房间中,女性在努力寻找自我,但同时自我也在不断地沉沦和迷失。“在夜晚我感到/我们的房间危机四伏/猫和老鼠都醒着”,在这里,猫和老鼠的象征采取了模糊化处理,指代并不明确。女性既可以是猫也可以是老鼠,黑夜中女性是猫,是猎手,同时又是老鼠。作为猎物的角色来完成生命体验,从“多姿多彩、年轻、美貌”到“瓜熟蒂落的女人”,是猫和老鼠角色的转换过程,也是女性自我回归的过程,女性在黑夜中回归自我,解放身体,但同时也在纵欲中迷失,被禁锢在那一方小小的家庭里。而“卧室的光线使新婚的夫妇沮丧”的原因,是双方没有处于纯粹的爱情婚姻关系中,而更多像是一种商品关系,是以审视与被审视的状态而存在,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都以其婚姻价值为依据,因而失去对美好事物向往的源动力,从而感到沮丧。而情绪的宣泄自然需要一个出口,于是“孤注一掷”,对自己说“家是出发的地方”来聊以自慰,保留心中最后一块希望地,借此对抗绝望的现状。
二、自白风格的发展——感情私语的流露
翟永明多次提及自己深受美国自白派诗歌的影响,在她的随笔集《纸上建筑》中曾谈道:“我在80年代中期的写作深受美国自白派诗歌的影响,尤其是普拉斯和洛威尔……在那以后的写作中我始终没有摆脱自白派诗歌对我的深刻影响。”通过考察翟永明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创作,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到鲜明的自白语调,感受到她与普拉斯等自白派诗人的精神联系,发现翟永明和普拉斯创作的相似之处,翟永明曾在《独白》中写道:“当你走时,我的痛苦/要把我的心从口中呕出/用爱杀死你/这是谁的禁忌。”面对自己深爱的人,翟永明用激进的口吻表达出对爱人深刻又压抑的情感。而普拉斯在《爹爹》中所表达的情感更为炽热。普拉斯十岁失去父亲,因此父爱一直成为普拉斯感情的缺口,但有时父爱也成为压在普拉斯身上的重担,与一向追求自由的普拉斯背道而驰,在《爹爹》这首诗中,可以感受到普拉斯对父亲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爸爸,我早该杀了你/我有时间前你就死了”,诗歌起始就带有一种疯狂的元素,对父亲极端的爱由此可见,这种爱更趋于一种病理性,其后诗歌进行视角转换,进入回忆叙述,诗人用大段篇幅回忆与父亲在瑙塞特港口的生活,并描述记忆中父亲的模样,是“整齐的胡子”“雅利安的蓝色的明亮眼睛”“有裂痕的下巴”,普拉斯记忆中的父亲模样清晰又鲜活,话语透露出短暂的理性意识,随后疯狂再次占据诗人的意识,吞噬理性,“爸爸,爸爸,你这混蛋,我受够了”, 以近乎暴虐的方式进行情感收尾。此外,受普拉斯影响,翟永明诗歌中的自白语调与死亡意识交织,北京大学谭五昌教授称之为特殊的“死亡想象”,认为这是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一种耐人寻味的诗歌现象。死亡一向是中国传统避讳的话题,缺乏成为思想主流的条件,女性也是如此,在历史和文化长河中一直处于缺失的状态,翟永明正是通过对死亡意识的书写,表现女性由来已久的苦闷。以《静安庄》为例,全诗分为十二个月份,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从一月到十二月,死亡气息一直笼罩其中,“脆弱唯一的云像孤独的野兽/蹑足走来/含有坏天气的味道”,从一月进入静安庄开始,死亡的阴影就投射在“我”目光所及的所有地方,二月开始环绕村庄,视线所能看到的,全是破败的景象,有如“怎样才能进入静安庄/尽管每天都有溺婴尸体和服毒的新娘”,从四月开始死亡气息达到极致,“你尘世的眼光注视我/想起母亲愤怒的声音/昼和夜茫然交替不已/永恒的脐带绞死我”,窒息感迎面而来,使人难以呼吸,六月和七月往后,死亡彷佛已经成为静安庄常态,“夜里月黑风高/男孩子们练习杀人”,“青枫树不计时日/在这儿出生和死亡/旧宅的人离去/守夜者半睡半醒”,生与死交织在一起,死亡充盈在“我”的世界中,屠杀一切生命的迹象,痛苦、绝望将“我”包围,“我”困在围城里无法逃脱。
《咖啡馆之歌》后,翟永明诗歌的自白风格呈现新的转向。“通过写作《咖啡馆之歌》,我完成了久已期待的语言的转换,它带走了我过去写作中受普拉斯影响而强调的自白语调,而带来一种新的细微而平淡的叙说风格”。可以说《咖啡馆之歌》是翟永明前后期诗歌创作的分水岭,不仅体现在创作方式方法的改变,更表现为诗人创作心态的变化。1990年至1992年近两年的纽约旅居生活虽未给诗人带来创作产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却使得诗人内心真正沉淀下来,去思考一种变化的可能性。这既推动了对过去《静安庄》创作经验的总结,也为接下来的新诗创作做了准备,她努力去发现材料与材料之间的新联系,探索文本与主题、词语与词语之间的新冲突,向新的叙说风格靠近。
三、身体叙事的发展和转型——暴露式自我
翟永明的诗歌为了传达性别意识,常常采用身体写作的创作方法。女性的身体成为被描述的对象,与世界相联结,主动成为世界的镜像反映。翟永明曾谈道:“女性身体内部总是隐藏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毁灭性预感。”女性通过关注自身内部来达到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女性身体天生具有一种敏感度,这种敏感度具有穿透时间和空间的能力,能够越过理性和感性的纠缠而直达事物的本质。罗振亚认为,翟永明的写作一开始就是“女性之躯的历险”,通过女性身体来折射历史场景和个体命运。翟永明以女性身体为叙事载体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所主张的躯体写作理论。埃德娜·西苏在著作《美杜莎的笑声》中鼓励女作家重视女性身体的力量,将身体“投入”到写作中去,并指出:“写作……把她自身的力量交还给她,同时交还给她的还有……她身体被封印起来的巨大领地。”在西苏看来,女性长期缺席于历史的书写,女性必须写自己,必须用身体写作。通过写作,女性可以深入了解并解封女性长期以来被历史所封印的领域,从此正式踏入排斥她的历史本身。翟永明深受这种表达策略的影响,在写作中将身体叙事付诸实践,为女性锻造“反逻各斯”的武器。
在传统的评价体系中,女性展示自己的身体被看作是一种有悖常规的越轨行为,女性被教育必须保守地对待自己的身体,不能直白地袒露自己的欲望,如有一点欲求的表达便会被视为不端,甚至被扣上“淫”的帽子。在很多传统和现代文本中,为了博得消费者和阅读者的眼球,女性的身体被赋予了娱乐和游戏的性质,被无形的、有形的力量控制,向代表权力的男性躯体投诚。在这样的环境下,女性无法充分表达内心真实的诉求,欲望一再被压抑,言语被囚禁在苦闷的黑屋中。对此西苏表示强烈不满和厌倦,认为“女性只有写自己的时候,才能回归自己的身体,那不仅是被禁用的、当作危险陌生之物示众的身体,同时还是禁令的缘由和载体,禁止身体等同于禁止呼吸和话语”。翟永明深刻感受到禁锢在女性身体上的权力铁门,在诗作中力求还原女性被遮蔽的身体欲望:“啤酒眼泪般溢出/她舔了又舔/某种本能唆使她/突然抬起先天不足的眼光”“你身体上有用的部分/多么尊贵/在一切玫瑰之上”“与你丰满的吻/与你盛大的欲望/与紧箍我们腰身的爱”。在翟永明的书写中,女性的欲望得到了完整表达。在翟永明看来,女性的身体及其欲望不该羞于展示和表达,在思想上也不该有任何禁锢。在具体写作上,女性书写就该有一个广阔的空间,可以写她们的情色、身体和性生活,书写那些无限流动的复杂性,这不是一个冲动的驱使性行为,而是长期的冒险。
翟永明对身体书写的探索为中国新诗注入了新的活力,开拓了诗歌表现的新领域。但通过身体建立属于女性自身的书写体系,也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自我迷恋式的问题。有时候内心情感不加节制的流露,演变为某种病态式的镜像自恋,成为诗人向更深处探索的阻碍。翟永明自身也意识到这方面的束缚,在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中,她更加倾向于探索一种技术性的写作,专注于诗歌技巧的打磨,尝试多种风格的转换,诗歌写作渐趋成熟。
四、结语
翟永明坚持书写边缘地带的女性声音,努力冲破女性的黑夜,建构辽阔的女性叙事空间。作为新时代的女性诗人,无论是前期对自白语调和身体叙事的探索,还是近年来对未来世界的畅想和书写,翟永明始终保持先锋的姿态,追求诗歌创新的各种可能性,为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唐晓渡. 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读翟永明的组诗《女人》[J]. 诗刊,1987(2).
[2] 成红舞. 从女性主义诗学到性别诗学[J]. 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12).
[3] 吴敬思. 当代诗歌潮流回顾(六卷)[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4] 翟永明. 在一切玫瑰之上[M]. 沈阳:沈阳出版社,1992.
[5] 翟永明. 翟永明的诗[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6] 翟永明. 纸上建筑[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7] 西尔维娅·普拉斯. 西尔维娅·普拉斯诗集[M]. 胡梅红,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8] 谭五昌. 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9] 埃莱娜·西苏. 美杜莎的笑声[M]. 米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