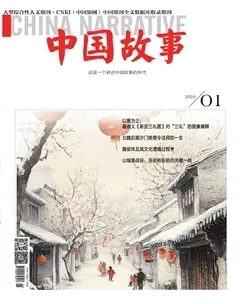承上启下:东汉末年史事的叙事模式
【导读】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作为记载东汉、三国时期史事的重要史籍,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两部史籍在时间断限上有所重叠,都对东汉末年的史事有所记载,却又有所差异,因此值得我们关注。作为中国史书的典范之作,它们为后世研究东汉末年历史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与思路。两部史籍中的一大交叉部分“董卓传”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研究空间。通过比较二者的叙事差异,本文总结出了《后汉书》承上、《三国志》启下的东汉末年史事的叙事模式。
西晋时,陈寿著《三国志》,记事上起汉灵帝光和末年(184年)黄巾起义,下讫西晋灭吴(280年);刘宋时,范晔著《后汉书》,记事起自汉光武帝建武初年(25年),终于汉献帝建安末年(220年),两部史书在184至220年的断限上有所重合。特别是《三国志》,记述了大量三国以前的史事。这并非是陈寿的历史断限不明,而是自有其内在的叙事逻辑。本文以两部史书中“董卓传”的记述为例,探究两部史籍的叙事模式。
一、两部史籍中“董卓传”的特点
《三国志》呈现出以魏、蜀、吴三国为中心的叙事模式,与三国时期“三足鼎立”的政治、军事格局相适应。同时又上承《史记》以来的史书编纂体例,保持了纪传体的史书编纂传统,为历史人物分立纪传,通过铺陈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来记叙史事。《三国志》传记的一大特点便是合传占比极高。合传,指的是史家把历史性质相近或互有关联的历史人物分类、归拢之后,再进行叙述、评价。相比于对单一历史人物的单独叙述,合传往往更能展现历史复杂多维的样貌。有鉴于此,中国近代史家梁启超对合传有着高度评价。
从传的体例上看,《三国志》的《董二袁刘传》采用合传形式,将同一时代的董卓、袁绍、袁术、刘表,连带他们的子女一同入传,整体篇幅较短,形式较为紧凑。这与《三国志》文辞简约的整体特点一致。这样的记述比较凝练,便于后人一览当时历史的全貌。但也有过于简单以致缺乏细节的问题,限制了后人对史料的进一步挖掘。故有后世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之事。《后汉书》则单独为董卓立传,记载了大量《三国志》中未有的细节,包括董卓军与黄巾军战前的兵力形势、朝堂上董卓威逼百官同意废立皇帝等,内容翔实,保留了大量史料、史著的原文,让今人在原始材料大量佚失后仍能窥得不少内容。
从传的内容上看,《董二袁刘传》对董卓的记述较为简略。《三国志》成书于西晋时期,距三国不远,或许是许多史料有所隐讳,故尚未面世。以裴松之为代表的后世史家对其做了大量注解,方才弥补史料匮乏这一缺憾。《后汉书·董卓列传》则大量引用历史人物的言论、著作,有助于后人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进一步认识。
二、共同的形象与差异的形象
《后汉书》的人物传记,既继承了《史记》《汉书》的优良传统,又有范晔自己的特色。范晔“看准某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关系、牵涉到一朝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就以他作为时代的中心,来归纳当时的历史,并为这个人立传记”,并“致力于人物个性特征的刻画”。
《三国志》在人物评价方面,具有“具体考察与辩证分析相结合”的特点。陈寿在回顾三国人物时,既能梳理出他们成败兴衰相互转化的历程,又能分析出他们各自的长短得失,并在此基础上整体分析多面、多元的历史人物。
(一)共同的形象——从豪杰到奸佞
虽然两部史籍都提及了董卓初起时的“豪杰”“粗猛有谋”,但占据多数篇幅的还是“奸佞”“逆贼”“残暴”等极度负面的评价,后文将详述这一原因。
董卓刚被何太后宣入京中稳定局势时,为震慑各方势力,他将自己所部士卒趁夜带至城外,白日再声势浩大地进城,如此反复,令各方相信他董卓兵强马壮,自此臣服。董卓蛊惑人心的手段不可谓不老到。在百官集会上,董卓公然宣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政。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陈留王,何如?”董卓篡夺、操弄皇权的野心暴露无遗。此时百官竟无一人敢言。董卓继续叫嚣:“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剑。有敢沮大议,皆以军法从之。”坐者震动,却不敢出言反对。独有尚书卢植直言不讳,当场批驳董卓的谬论:“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过千余,故有废立之事。今上富于春秋,行无失德,非前事之比也。”董卓本想搬出“伊霍之事”威慑群臣,眼见有人拆穿了自己擅行废立的把戏,一时陷入难堪的局面,只得愤怒离席。百官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独有卢植义正辞严,足见董卓此时已权倾朝野,少有大臣敢于反对。
(二)差异的形象——擢用人才
董卓意识到想要牢牢把握权柄,不仅要依靠武装力量的强大与忠心,也要赢得士大夫的服膺与支持,故特为党锢之祸中的“党人”平反:“乃与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俱带鈇锧诣阙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于是悉复蕃等爵位,擢用子孙。”董卓一向知晓天下士人痛恨阉人弄权。上台后,董卓或许有收买人心的考量,但他确实选用了一批人才。董卓此举,一方面可拉拢士人,使自己站到广大士人的一边,壮大本阵营实力;另一方面可借此抑制其他势力的发展。《后汉书》中这一段对董卓形象的重要记载却不见于《三国志》,《三国志》仅是引用了《献帝纪》的相关内容。史料的缺乏限制了陈寿的发挥,而刘宋的范晔则能将董卓兴废立之事的前因后果、外界反应和盘托出,叙事更加全面。
《三国志·董二袁刘传》记述简略,适合了解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概况。《后汉书·董卓列传》则更为详细,适合研究者挖掘细节。将二者进行对比阅读或按需选用,不失为一种最大程度发挥它们价值的方式。“三国时代是中国统一与分裂、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个时代”,反映到史学著作上,便是著述角度的多样与统一。历史人物在史著中呈现的形象,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
三、叙事重点的差异及其原因
《后汉书》《三国志》在叙事上有着一详一略的差异。叙事详略的差异不仅是由于史料的多寡,更在于叙事重点的不同。一上承、一下启的叙事重点,突出体现了两部史籍在记述东汉末年史事上的差异性。
(一)《后汉书》的上承:断代体例与历史叙事话语权
《后汉书》作为统一朝代的断代史,更多地在史事记录上发挥“上承”的作用。这不仅是统一朝代的断代史需要叙事完整,更是范晔作为南朝刘宋史家的时代使命:在南北分立的局面下,建构“大一统”的叙事体系,以争夺在历史叙事上的话语权。“其旨趣不仅是关于东汉历史本身的‘得失’,更有关于刘宋政权合理性之历史因素的考虑,即为刘宋政权的建立找到历史的根据,这是他历史撰写的重要目的”。
《后汉书》的撰述目的在于记述东汉史事。东汉末年的混乱局面由黄巾起义开始,随后走向纷乱而不可收拾,东汉的统治也一步步走向终结。因此,有必要详述其衰亡的过程,以备后世警戒、借鉴,发挥历史的垂训作用。东汉也是《后汉书》叙事的主要对象,故详为叙述。在这一点上,《三国志》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二)《三国志》的下启:开国群雄传与皇朝正统性
《三国志》作为记述三国鼎立时期的史籍,更多地在记述东汉末年史事上发挥“下启”的作用,即记述东汉末年史事是为了更好地记述三国史事。这种处理方式没有拘泥于《汉书》朝代史的范式,而是自然勾连起了分属两个朝代史分期(东汉、三国)下的同一历史时期。灵活运用断代史体例的叙事方式是陈寿对史学的一大贡献,也是中国史学“求通”的体现。《三国志》开创了纪传体国别史的典范。具体地看,《魏书》宏阔,《蜀书》简异,《吴书》齐整,三书总而为一部《三国志》,将三国历史的框架完整地勾勒了出来。
然而,唐朝的刘知幾对《三国志》将董卓等人收入列传的做法颇有异议:“夫汉之董卓,犹秦之赵高。昔车令之诛,既不列于《汉史》,何太师之毙,遂独刊于《魏书》乎?兼复臧洪、陶谦、刘虞、孙瓒,生于季末,自相吞噬。其于曹氏也,非唯理异犬牙,固亦事同风马。汉典所具,而魏册仍编。岂非流宕忘归,迷而不悟者也?”
刘知幾认为,董卓等人作为东汉之臣,自应列入记述汉朝的史书,不应编入记述曹魏的史书。显然,刘知幾在此坚持的,是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编纂体例。若以刘知幾“迷而不悟”的解释来看待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述董卓等人的做法,恐怕过于简单武断。笔者以为,不妨以“下启”的“开国群雄传”来看待陈寿对董卓等人的处理,或能得出新的认识。
董卓等人的“开国群雄传”在《三国志·魏书》中,处于本纪、后妃传后,曹魏诸臣传前。董卓等人缘何被放于曹魏开国功臣之前?显然,这并不是基于时序的考虑:董卓等人与曹魏开国功臣所处时代大抵相当,完全可以放到相对不那么突出的位置。陈寿的这一排布,当是为曹魏的“皇朝正统性”张目。
曹魏代汉在形式上仿效了上古“禅让”的模式,这就要求受禅者具有极高的贡献与威望。曹魏的开国君主虽是文帝曹丕,但奠定基础的当是被追尊为武帝的魏王曹操。曹操在东汉末世攘除众奸,一度稳定了汉室,功勋卓著,方有受禅之资。东汉末年的宦官“乱政”、群雄争霸导致朝局混乱,使汉室人心大失,进而失去天命支持,更是天命转移的良机。
曹丕还通过彰表“二十四贤”表明其与抵制宦官势力的“清流”士人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以此站到“清流”一边。进一步讲,曹魏的统治群体赢得了“清流”士人的支持,并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
由此观之,曹魏能从汉室手中顺利获得政权与法统,实有赖于群雄争斗。“开国群雄传”的这一安排,为曹魏政权的合法性作出了合理的铺垫,表明了曹魏的正统性——后来司马代曹,也为西晋政权的合法性做了历史线索的连贯铺陈。
在《三国志》和《后汉书》中关于曹操的记载亦有差异。在时间断限上,曹操处于东汉而非三国,但《三国志》有《武帝纪》,《后汉书》却并未给曹操立传。这种处理体现了两位史家在叙事断限上的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曹操是开启三国时期的主要人物,而非仅是东汉末年的一大枭雄。
在陈寿的笔下,曹操最初即是“尊君”的代表人物:冀州刺史王芬等人连结豪杰,密谋废黜灵帝,另立合肥侯。当他们“以告太祖(曹操)”时,“太祖拒之,芬等遂败”。曹操最初被董卓召见时,即高举反袁大旗,是其主张“尊君”的又一代表事例。
《三国志》重点在于记述三国史事,因而记述与三国关联密切的东汉末年之事是陈寿必然的选择。不过,记述东汉末年的史事更多的是一种引入铺陈,而非《三国志》叙事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这体现了《三国志》“求通”的撰述思想。《三国志》以“开国群雄传”的体例安排,在纵向上打通了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历史叙事结构;而《三国志》又记载了魏、蜀、吴三国史事,是为同一历史时段下的横向贯通。《三国志》叙事结构纵横兼具,完成了“启下”的叙事体系建构。
四、结语
《后汉书》《三国志》建立了东汉末年史事“承上启下”的叙事模式,为后世史家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解进一步丰富了史料,深化了后人对于《三国志》的理解,有助于更深入地探索原著者陈寿的叙事特点。
《后汉书》《三国志》作为断代皇朝史的历史著作,仍是以朝代的起讫作为史著编纂的断限依据。以朝代起讫作为历史的分期标准,将本来连续的客观历史进行人为分割,这是基于朝代立场对中国历史的一种描述方式,成为中国正史的主要编纂范式。然而,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本是天然连续的,任何界限都是史家所做的切分,暗含着人的某种主观认识。诚如赵轶峰所言:“历史分期作为一种知识形式,本身具有反历史的性质。”但就在这种看似切断了联系的朝代史模式下,中国史家逐渐形成一种“通”的史学思想,并长期在史学编纂的实践中孜孜以求。在“通”中,纵向的历时性与横向的共时性互为因果,历史的发展脉络纵横贯通,相互交织。在史学研究已大为深入的今天,我们仍应坚持并发扬这种“通”的史学精神。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创作尚应符合时代与实事,具有时代特色,史学撰述更应如此。我们应依照历史的具体背景而作出调整,重归历史语境,使史学体例与客观历史相调适,形成全面的史学认识。不然,以虚构的、反历史的“模型”去研究历史,尝试“一蹴而就”觅得“定论”,只会得出片面乃至无意义的结论;或是为别有用心者利用。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 裘汉康. 略论《后汉书》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与特色[J].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
[3] 庞天佑. 论《三国志》的人物评价[J]. 史学史研究,2002(2).
[4] 范晔. 后汉书[M]. 李贤,等,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5.
[5] 李建西.“铺首”“鈇钺”“鈇锧”新释——兼论金属铜的名称嬗变[J]. 文博,2020(1).
[6] 金文京. 三国志的世界:后汉三国时代[M]. 何晓毅,梁蕾,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7] 王亮军. 论范晔《后汉书》中的“大一统”意识[J].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1).
[8] 崔峰耀.《三国志》历史叙事研究[D]. 兰州:兰州大学,2021.
[9] 刘知幾. 史通通释[M]. 浦起龙,通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10] 徐冲.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1] 徐冲.“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J]. 社会科学,2012(6).
[12] 陈寿. 三国志[M]. 裴松之,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2.
[13] 赵轶峰. 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J]. 史学集刊,2001(4).
[14] 刘家和. 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5] 瞿林东. 论“通史家风”旨在于“通”[J]. 史学月刊,2020(7).
[16] 白居易. 白居易集:卷45[M]. 顾学颉,校点. 北京:中华书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