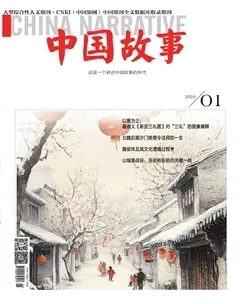刑名的悬解
【导读】王夫之援儒入道,重解庄子,将儒家思想注入《庄子·养生主》之中,对其做出符合儒家传统君民关系思想的重大改造。这一改造就形而上来讲,必然要牵涉到天人关系,但文本中并未直接描述天人关系,而是透过刑名关系与形神关系显示出来的,刑名关系牵引出了天人关系,形神关系才直接彰显了天人关系,王夫之极力凸显神的重要性和不灭性,就是要突出与神等价的天的主宰性和永恒性,进而引申出君的绝对性和至高无上。由此可见,君民关系是天人关系的现实表达,而君又是重中之重,倒悬与悬解皆依赖于君主一人,因此,君民关系中关于存在与意义的三重倒悬是中国古代政治结构建立的根本,也是王朝更迭、循环往复的症结所在,倒悬是帝制时代的常态,悬解则是封建时代的变态。
《庄子·养生主》中的“养生主”有两种解释:一是养“生主”,存养生命之主,即形体;二是“养生”主,主要探讨养生之道,养生的要旨在于存养精神,而“养神的方法莫过于顺乎自然”。这两种解释被认为是《养生主》一文中要探讨的两个面向。
《养生主》篇幅不长,但哲学意蕴丰富。人生有涯而知无涯、“缘督以为经”、 庖丁解牛、右师之介、泽雉樊中、“秦失吊老聘”、薪尽火传……这一系列寓言和故事构成了《养生主》的整个文本,历代名家也对其多有注释。郭象总括其为“夫生以存养,则养生者理之极也”,主张养生之道;朱子认为“庄子之意,则不论义理,专计利害”,对其多有批评之意;王阳明则表示“大抵养德养身,只是一事”,要求将养德与养生统一起来。
王夫之认为“养生”就要防止危害身心的三重刑罚,既有身体发肤的形体之刑,也有功名利禄的人世刑罚,亦有使右师独足的天刑。刑名关系直接涉及天人关系,天人关系则是刑名关系的哲学表达,而天人关系又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在古代,所有关系中最要紧的就是君民关系,君民关系就是天人关系的现实投射,君民关系在现实中又有着存在与意义的三重倒悬。王夫之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力图解除这三重倒悬,恢复三代圣王的君民关系,实质上就是要重构天人关系,拉近天人之间的距离,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王夫之的一系列观点要求改变君民之间绝对悬殊的现实境况,改善君主治下百姓的生活境遇和生存状态,使得“民重君轻”的民本思想不至于沦为空谈,带有一定的启蒙色彩。
一、生命的三重刑
王夫之按照自己的哲学脉络和思维逻辑对《养生主》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有三种刑罚对生命造成了戕害。
(一)形体之刑
他首先指明了几个重要概念,并点明主旨:“形,寓也,宾也;心知寓神以驰,役也;皆吾生之有而非生之主也。”这表明形体或身体是寓所,是宾位,居于次要地位,心知则是寓于神中的,这也就意味着心知与神是紧密相连的,而形体与心知都是生命自有的,并非是生命的主宰与核心,这里其实已经暗示了神的重要地位。首段最后一句说:“养生之主者,宾其宾,役其役,薪尽而火不丧其明;善以其轻微之用,游于善恶之间而已矣。”“养生之主者”能使身体、心知与精神各安其分,各得其位,那么“生之主”就应该是“性”,只有依靠人从天那里所禀受的本性,才能有如此清楚明白而又自然妥帖的安排。“性”又是运动变化的,能够“游于善恶之间”,这就是说,王夫之并未单纯地继承单一同质的性善论、性恶论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层次分明的性三品论等人性论观点,而是认为人性会有所变化,不能仅进行先验预设,而是要更多地考虑后天因素,与习、情等要素结合在一起加以探讨。
身体之性不只是个体之性,更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而存在,身体也是处在社会空间之中,社会的层级结构和稳定形态都要求名利与刑罚的双边制约,以确保社会的运转与发展。因此,身体之性就具备了社会属性,从这一角度来讲,社会之刑就是形体之刑。而身体之性又是与天关联在一起的,缘督为经,“以清微纤妙之气,循虚而行,止于所不可行,而行自顺,以适得其中”,天是无善无恶、超脱善恶的,由天贯彻到人,由天刑落实到个人,自然顺遂,行止自如,天刑胜过人刑。
(二)名之刑
“大名之所在,大刑之所婴,大善大恶之争,大险大阻存焉,皆大軱也。” 这是在讲刑名关系,大名与大刑缠绕之处就是善恶交锋争斗的地方,也是艰难险阻所在的地方,但刑名又是人世间不可避免的网罗,“避刑则必尸其名,求名则必蹈乎刑”。逃避刑罚必然趋向于功名利禄,求取功名利禄又必然会陷入刑罚的泥潭而难以自拔。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像庖丁解牛一样,“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既“依乎天理”又“因其固然”,使得“名者自名,刑者自刑,瓜分瓦裂,如土委地,而天下无全天下矣”。天下虽然不全,但我之情乃全,我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神完气足,足以养天年而终余年。
(三)天刑
刑名虽有内在的现实关联和事实逻辑,但也需要与外在超越领域——天相关联,从而为人世间的刑名提供形而上学的基础。右师之介乃是天之刑,而“名者,天之所刑也”,天之刑涉及天的维度,天之所刑的名与人间刑罚的刑就是人的维度,如此一来,刑名关系本质上就是天人关系,而天人关系隐喻的是君民关系。先秦诸子对于天人关系各有不同的看法,但天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实际上先秦诸子并没有进行明确清晰的论证,无论是孔子罕言“性与天道”,还是孟子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或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亦或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都具有模糊性与含混性,都在实质上以一种微妙而灵活迂回的态度避开了这一问题。他们将天人关系这一需要论证的结论当成先验前提予以论证,这无疑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真正对这一关系予以证明与确立的人是董仲舒,他对传统的天人关系进行了改造,提出“天亦人之曾祖父也”的观点,建立起了一套“天—天子—父—子(人)”的天人关系学说,其看似在建构天人关系,实际上在确认君臣父子的尊卑关系。王夫之承接了董仲舒的这一思想,“盖天显于民,而民必依天以立命”,“天位者,天所位也;人君者,人所归也。为主器之长子,膺祖宗之德泽,非窃非夺,天人所不能违”,民众依赖天或天的具象化——天子来生存与生活,而天子的地位是由天来授予的,那么皇权至上与皇位世袭也具有了正当性与合法性,天人关系或者君民关系也由此固定下来。
二、三刑的悬解
右师之介代表的是人的非常状态,即一种残疾缺陷的状态,但这也是最坏情况下最好的状态,“宁近右师之刑,勿近樊雉之名”,这种非常状态亦是悬的状态,对常人是一种困缚,“天悬刑以悬小人,悬名以悬君子”,这又将天与人结合起来,进一步分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又与善恶挂钩,这就是从人的角度判定善恶,但王夫之又讲,“然悬于刑者,人知畏之;悬于名者,人不知解”,就天的角度来看,刑名善恶的区别没有意义,就人而言,则有知与不知的分别,这就要求悬解,解开约束,恢复常态,破除生死。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薪尽”是指个体生命的消亡,包括个人肉体和个体精神的终结;“火传”则指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而非个体精神的存留。换言之,“薪尽火传”是在讲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的动态关系。个体小我融入整个宇宙大我之中,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境界,这样才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这是一个宇宙论的讲法,王夫之则从形神关系上立论,把天直接等同于神,那么人就只能对应于形了,“盖人之生也,形成而神因附之。形敝而不足以居神,则神舍之而去;舍之以去,而神者非神也。寓于形而谓之神,不寓于形,天而已矣”,人首先有形体,再有神的附着,形与神有先后次序的差别。形体是人存在的基础,神则是独立自主、可以脱离形体而存在的,但又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与核心。如果说形体构成了人的生存场域,确保了人类的存活与存在,那么神就建立起了人的生活场域,是主体间性产生的关键所在,使我与他人有了真正的区分,保证了我之为我的生存意义和生活意义。人的世界由物的世界转化为事的世界,即不再是单纯无意义的自然界,而是完全意义上的属人世界。人来赋予这个世界意义,同时,人也赋予自身意义,力图完成个体的人格化和社会化的建构。人不只是一个自然人,更是一个社会人。
天落实到人之上谓之性,此性“至常不易、万岁成纯、相传不熄”,具有天的特性,而又“来去适然,任薪之多寡,数尽而止。其不可知者,或游于虚,或寓于他,鼠肝虫臂,无所不可,而何可听帝之悬以役役于善恶哉?”如此一来,各物自有其性,无所不可,不一定会拘泥于善恶。“传者主也,尽者宾也,役也”,生生不息、传之不尽的是性,燃烧殆尽的是形体和心知,换言之,形体与心知共同构建了性,性也能使“宾其宾,役其役,死而不亡”,“哀乐不能入”。
确立这样的形神关系,对应于身心关系的重构,由非常状态的身心关系转向了常态的身心关系,也是由悬到悬解的转变。那么,既然身心都是变动不居、有生有灭的,那么人性也是运动变化、日生日成的,因此,王夫之的社会历史观也是运动变化、不断发展的,这就倾向于唯物史观,具备了一定的唯物主义特质。
形神关系背后是天人关系,天人关系是君民关系的虚拟化、神圣化,君民关系则是天人关系的真实化、世俗化。王夫之在篇章中多次强调神的重要地位和核心位置,“其神凝”“神虽王,不善也”,这实质上是在强调君的绝对地位和主宰含义。神为天,即君为天,君权天授的观念依然笼罩在王夫之的头脑中。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阶层所建构的话语体系,其话语对象是君主。他们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们要维护等级森严的封建秩序,自由、民主、平等这些理念根本无处容身。因此,所谓的“万物一体”境界,更多地是针对人与自然事物的和谐共处,当然,也不排除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友善关系,但这不是平等,而是人际交往准则和社会交往规范在境界论上的升华与展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结构由平面化转向立体化,就意味着阶层分化,这已经蕴含着不平等了,但这种不平等也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演进与进化。伴随着封建社会一系列制度律例的制定,这种不平等就会被固化下来,所谓的平等只会体现为封建制度下的细节平等和技术平等,而不会显现为完全的平等,平等就成为民众所向往和追求的一个理念。
君民关系具备存在与意义的三重倒悬:
第一重是存在的倒悬。中国古代王朝常常扭曲了这样一个道理:明明是百姓敬献万物以养君,却被说成是君赐予万物以育民,君民的供养关系被颠倒了过来。
第二重是意义的倒悬。孟子讲民重君轻,从百姓之中诞生的君主应当为百姓做事。这种对上古圣王的政治幻想其实是一种经验主义的逻辑倒推。寄希望于遥远的古代社会,认定古代比现代更好,相当于要由已知达到未知,这就丧失了对未来的判断能力。未来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自在之物,这样的断裂就使得我们走进了经验论的死胡同。过去推论不出未来,因果链条就被解构了,这样的幻想只能像泡沫一样烟消云散。君主拥有绝对权威,予取予夺,掌握生杀大权,持赏罚之柄,戕害百姓,百姓居于弱势地位,只能逆来顺受,直到忍无可忍,改朝换代,如此,君民的意义就倒悬了。
第三重是存在与意义的倒悬。孟子言,“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面对残暴不仁的君主,是可以诛杀他的,这不是弑君而是诛杀独夫民贼。君的存在被意义遮蔽了,君不再是君,而是桀纣一类的独夫,也就是说,政治意义上的君主存在就被取消了,君主德不配位,取而代之的是“一夫”。语言名词上的转换,表示意义代替了存在,但存在不是完全消解了,而只是暂时退场了,仍隐匿于事的场域之中,意义暴露在了人的眼前,占据了原来存在的位置。存在只能在意义的笼罩之下,成为意义的影子与镜像。存在与意义是事物的一体之两面,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意义遭到了抹杀,那么存在也就崩解了。看似是诛杀独夫,其实就是在弑君,意义优先不能瓦解存在优先,诛杀独夫和弑君本就是一事,但通过意义的改变和前置就赋予了弑君合理性,也就是实质上肯定了以下犯上、以臣弑君的合理性,这暗含了孟子对于社会现实“礼崩乐坏”的无奈接受。当然,孟子将这一合理性的程度与范围限制在一定的框架之内,但在实际的运用上,却可以将之扩大化,为自身的不臣之举(如清君侧)辩护,存在与意义的置换在这一层面就有了充分展现。这三重倒悬是否也存在悬解的可能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悬解的可能性取决于君而不决定于民。“民重君轻”“君舟民水”都是在以君为主的前提下展开的,在这种畸形的社会结构下,只能依赖于圣君贤相来达到悬解的暂时功效,而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悬解,这是“王夫之们”难以挣脱的藩篱。
三、王夫之对《庄子·养生主》疏解的意义
从时代背景来看,天人关系源自君民关系的逐渐崩解与重新确立。天人关系形成与确立,需要社会土壤与现实基础。先秦对天人关系的初步思考,是分封制度土崩瓦解和君主集权制逐步建立的反映。周代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宗法分封制,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步消解。这意味着个体不再被束缚在严苛的血缘宗法制和等级制下,而是直接敞开,面对世间万物和天地。这种转变是“礼崩乐坏”的精神开端。人一旦在现实中不再直接面对等级制度所要求的规范和约束,就会自然地将目光转向天地。从这一角度讲,先秦诸子将人的目光从自身转移到了外在的客观世界,这才需要考虑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即人与自然之天的关系。但先秦诸子所论述的“天”又绝不止自然之天一种,更有意志之天、主宰之天,等等,这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一般而言,我们最开始认识的天应当是自然之天,就像泰勒斯所认识的水一样。这个水可能是河水、江水、溪水,但不太可能是抽象的水的概念。因为这种抽象的逻辑思维方式,直到巴门尼德建立起形而上学本体论时才具有。泰勒斯说“大地浮在水面上”,这明显是对城邦情形的现实刻画。但水是万物的本源,即万物都在水中循环、往复、生成、变化,这是一个通过观察而归纳总结出的理性结论。同理,天的多重含义是由自然之天引申出来的,经过长期的发展与演化,天最终被固定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宋明理学中的理学与心学都将天作为自身理论的终极依据,这其实是一种思想的惯性,代表着中国的文化早熟。文化早熟的根源在于政治早熟,政治早熟是由于帝制时代兴起。帝制延续了两千多年,文化包括文化的核心——哲学,其基本架构和思维方式也就没有发生根本转向。
诚然,朱子开辟了儒学的新方向,陆王(陆九渊﹑王守仁)拓展了为学的新路径,但最后的落脚点都是在道德上。道德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这种基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哲学与文化,注定了中国哲学是境界论,即强调个人品质修养和道德境界提升,披上了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但这只是表象,实质上,这种境界只能凝结为个人的境界,绝对不能上升为群体的清醒意识判断。根据“德必配位”的传统,孟子说人人皆有尧舜之性,人一旦实现了先天具有的尧舜之性,那么也应当拥有尧舜之位,即天子之位。如果人人都实现了尧舜之性,那么人人就应该具有尧舜之位,但这又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暗含的是一种政治结构的扁平化和政治地位上的平等,这是集权君主无法忍受的,也是整个封建社会无法容忍的。
因此,后世哲学家对人的本性加以收缩和限制,不再从政治上立足,而从个人的道德人格入手,提倡道德圣人,鼓励个人存心养性以臻至品德圆善完满,以期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和社会结构稳固。因此,我们所说的天人合一不是绝对的、永恒的宗教式合一,而是相互对待、相互成立的对象化统一。
四、总结
王夫之对于《养生主》的阐释既立足于庄子的文本,又糅合了自己的思想与观点,引儒入道,“以儒解庄”,以儒家思想来解释道家学说,通过刑名关系与形神关系展现天人关系,将“天之刑”和“神”对应于“天”,将“天之所刑”“人之刑”与“形”对应于“人”,揭示了天人关系的至高境界——天人合一。这种合一并非绝对同一,而是对象化的合一。因此,天人关系实质上是君民关系的哲学表达式,使君民关系具有了形而上的基础,解释了君民关系何以可能。而就形而下的角度而言,君民关系是天人关系的现实刻画和直接依据。君民关系的三重倒悬(存在与存在的倒悬、意义与意义的倒悬、存在与意义的倒悬)是天人关系在封建帝制时代倒悬的有力证明。
王夫之希望解除这种倒悬的状态,给予百姓更多的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但囿于时代而又无可奈何。因为悬解的完全实现必须要消解掉君民关系,彻底摧毁封建制度,让所有人在法律地位上平等,这是君主与士大夫绝对无法接受的方案。故而只能维持倒悬—悬解的动态平衡,而不能收到拨乱反正之效。到了近代,外部力量的刺激打破了这一僵局,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2] 郭象,成玄英. 庄子注疏[M]. 曹础基,黄兰发,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1.
[3] 朱熹. 朱子全书:第23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微教育出版社,2002.
[4]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第一册[M]. 北京:线装书局,2012.
[5] 王夫之. 王夫之全书[M]. 长沙:岳麓书社,2011.
[6] 董仲舒. 春秋繁露[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7] 聂敏里. 西方思想的起源:古希腊哲学史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