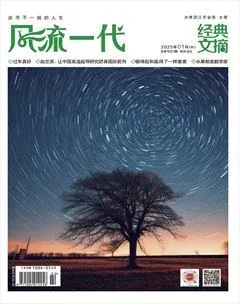那些年我们犯下的错
一场罕见的大风雪肆虐了整个松嫩平原,我钻进路边一个闲置的用来看场院的小草屋躲避风雪。一进小屋,还没来得及抖落帽子上的雪,就被一阵唧唧喳喳的叫声吸引了。定睛一看,原来是麻雀,估计有几十只,看来它们是从草屋破败的窗户里钻进来避难的。我一惊之后是狂喜,拿起书包就去打飞窜的鸟儿。
许是被外面的风雪吓昏了头,它们竟然不知道再从那个破窗户飞走,只是惊恐地乱窜。就这样,一只只麻雀跟下饺子似的被我打下来,扑棱着翅膀挣扎,露出灰白色的肚皮躺在地上抽搐。我激动得用颤抖的手一只一只捡拾,塞到书包里,一五一十地数着,恨不得把书包里的书都掏出来装鸟儿。我兴奋地在风雪中跋涉回家,戴着手闷子紧紧地捂着书包,生怕会有一只麻雀从里面飞走。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那时候我还上小学。那场罕见的风雪大到吹倒成排的电线杆,压塌好多破败的草房。那天早上我们家是从窗户里爬出来的:门已经被大雪死死地堵住了,而窗户是向里开的。爬出来之后才发现,整个房子在雪中只露出一个尖顶——也许,这么清晰地记住那场暴风雪,还因为那一场“杀戮”。
小时候,我们是“无恶不作”的野孩子。拿竿子捅屋檐下燕子的窝,就因为它们把粪便排泄到我们的头上;爬到高高的树上掏喜鹊窠,摸到喜鹊蛋直接磕碎,吮吸蛋液;至于抓一只蚂蚁拔掉它的触角看它漫无目的地乱窜,捉一只蜻蜓拴一根细线控制它的飞翔,早已经算不得杀戮了。那时,我们这些“野孩子”是不会为伤害一个无辜的生命而羞愧或忏悔的,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育我们该怎样去尊重一个生命,哪怕是和人类不一样的生命。饥饿和贫困让我们的双眼冒着野狼一样攫取的光,在我们的眼里,任何能够填饱肚子的东西,都是美味。在我们的眼里,大人杀猪宰羊、宰杀鸡鸭根本不是杀戮,而是一场狂欢,因为干瘪的肚腹终于见到荤腥了。
直到成年后,看一部纪录片:可可西里的戈壁荒滩上,被剥了皮的藏羚羊尸横遍地。羚羊尸堆里,一头还没有气绝的血肉模糊的藏羚羊在艰难地蠕动,那是怎样的一种蠕动啊!惊得我坐在电视前忘了呼吸,失魂落魄一般,怔怔地说不出话来。幼年一只只摔到地上抽搐的麻雀,还有那些被我们“杀戮”的蜻蜓、蚂蚁,从记忆的深处顽强地浮现,挥之不去。
每次回忆起幼时的“杀戮”,我似乎都会短暂性地失明、失聪、失语,脑子里只剩下一片杂乱无章的混沌。很庆幸我们没有执迷不悟,没有在“杀戮”的道路上走得太远、陷得太深。我们该感谢时间,是时间让我们长大成人,消除了身体里的戾气,或许我们也该感谢生活的逐渐富足,让我们摆脱了饥饿的威胁。
经历过艰难苦恨,尤其经历了很多生离死别之后,我们开始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有时不经意撞上一张蛛网,看到一只蜘蛛惊慌地逃离,就会微微一笑,仿佛那是一个惹祸的孩子,然后轻轻把头上的蛛丝剥离,甚至内心对破坏蜘蛛捕猎的网有了一丝歉意;或者在树下站一站,有蚂蚁爬到身上,再也不会惊慌失措地拍打甚至有碾死它而后快的想法了,看着小蚂蚁在自己毛茸茸的胳膊上“跋涉”,突然而生一种怜悯。苏轼说的“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吧?
夏夜,月朗风清之时,静对一树繁花,沉浸在一树花带给我的美好之中。风移影动,枝叶婆娑,仿佛听得见花朵在窃窃私语。在这静谧的夜里,我为能感知到还有一种生命以不同于我的生存状态存在着而欣慰,油然而生的一种怜惜之情,把内心浸得柔软纤细。知天命之年的我,再也不会像小时候跑上去抱着一棵树使劲摇晃,然后快意于下了一场花瓣雨了。
(杨乐摘自2024年7月14日《今晚报》,考拉的梦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