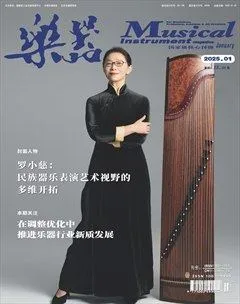沪上兴盛的后起之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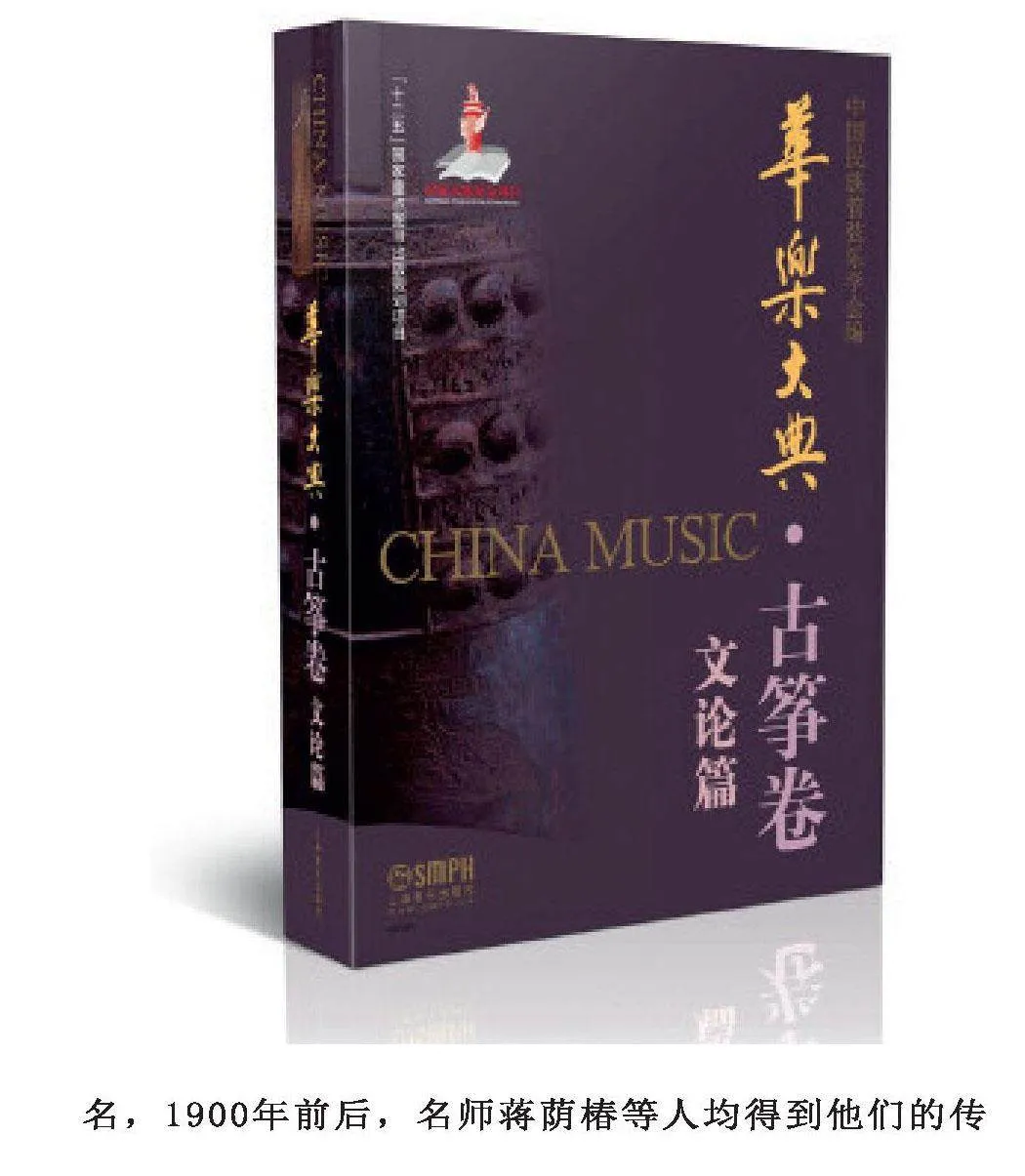
古筝艺术浙江流派作为现当代古筝艺术流派的后起之秀、一支劲旅,其形成与发展遵循着艺术发展规律,有其历史之必然性。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良好的外部及政策大环境、浙派筝人“守正创新”精神及其他外在因素的推动,共同促成了这一筝艺流派的形成与发展。
浙江,历来有筝乐之传统。直到今天,浙江全域的古筝艺术在整个国内古筝艺术发展中也是排在前列。山东、河南、广东、江苏、陕西、四川、湖北、辽宁及北京、上海等地,可以说都是古筝艺术发展的大省(市)。尤其是中国音乐金钟奖古筝比赛自创立以来,其中有很大一批来自山东、河南等籍(地)的青年筝手,如山东籍的程皓如、丁雪儿、任洲洋、高阳、邓翊群、杨雨桐,河南籍的宋心馨、刘颖、姚伊新、王钰,他们中又多数成为当今专业院校古筝专业教师。在浙江,则源源不断地向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输入大批古筝演奏人才。如80年代以进修或读书求学形式赴沪习艺的毛丽华、曾玉珍、吴萍、徐俊雅、葛梅君、王蔚,90年代以来陆续赴上音的盛秧、盛茜、祝杭红、赵岚、王茜、段廉、倪蕾、谢涛、叶思阳、王雨婷、赵墨佳,去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则有袁莎、章英、王琦、叶逸斯,再到青少年的胡许愿、张歌窈、汪韵乐,以及在中国音乐学院硕士毕业的单瑞雅等等,组成了蔚为壮观的古筝“浙军”。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些省份历来就有擅筝习筝的一个优良传统。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浙江筝派通过一干有志之士的努力发展,俨然成为传统古筝艺术流派中的后起之秀。这是20世纪古筝艺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典型个例,同时又是中国古筝艺术发展事业上的一件大事,一个重要现象。
悠久绵长的历史渊源(1900年以前)
浙江筝,又称杭筝。杭州旧称武林,故又有武林筝之称。流行于江浙一带。
筝,相传在东晋时已传入建康(今南京)。《晋书·乐志》中记如下:“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已来,稍有增广。”《古今乐录》籍中又记:“吴声歌旧器有篪、箜篌、琵琶,今有笙、筝。”南朝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吴声歌曲》之一中,如:“郎作《上声曲》,柱促使弦哀。譬如秋风急,触遇伤侬怀。”又如《上声歌》:“初歌《子夜曲》,改调促鸣筝。四座暂寂静,听我歌《上声》”,这里的《子夜》《上声》都是筝歌的形式,记录了艺人自弹自唱的情形。在宋、齐、梁、陈各朝,筝流见于上层社会,受到统治者们的喜爱。他们犹爱为筝撰述称颂。自曹魏以来,由统治者亲自为筝撰赋的文学作品就达到八篇。如梁·简文帝萧纲《筝赋》“听鸣筝之弄响,闻兹弦之一弹,足使客游恋国,壮士冲冠。……命丽人于玉席,陈宝器于纨罗,抚鸣筝而动曲……”,这其中就记录了宴享场合中命美人抚筝的情形。再如陈·顾野王《筝赋》“调宫商于促柱,转妙音于繁弦;既留心于别鹤,亦含情于采莲。始掩抑于纨扇,时怡畅于升天。”在这里就提到了《别鹤》《采莲》《纨扇》《升天》四首乐曲,由此可见,在当时筝这件乐器受欢迎的程度之高。在这个时期,筝以12弦、13弦两种型制并存。隋代的雅乐用筝就是传自梁、陈。且13弦筝最早见记于《隋书·音乐志》。
至唐,公元822年(穆宗长庆二年),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其一生所写三千余首诗中,有近两百首写西湖山水。其中不乏有关筝的记载和描述。《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中,“……移领钱塘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篥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虚白亭前湖水畔,前后只应三度按。便除庶子抛却来,闻道如今各星散。……”诗中提到他在下榻的虚白堂(今凤凰山西麓)教练歌姬排演大曲《霓裳羽衣曲》。其中一位名叫谢好的歌姬,是善筝妙手。而白居易本人也常以弹筝自娱,评头论足,好不潇洒。这可以说是筝在杭州出现的最早记录了。
五代时,浙江钱氏吴越国,以新起都市杭州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据《宋史·吴越世家》,其中记载钱俶王向北宋纳贡,其中就包含本国的乐器“胡琴、五弦、筝”等。这成为筝在杭州流传的力证,也侧面说明了当时杭州手工业发达到已有乐器制造的能力,为后来武林筝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北宋末词人吕渭老,檇(音zuì)李(今浙江嘉兴西南)人,擅弹筝,会作曲。其《鼓笛慢·水龙吟》词中,“十里尘香,五更弦月,未收弦管。正秦筝续谱,宫箫定拍,候来冬按”,提及他正在为秦筝谱写新曲。在《选冠子·雨湿花房》词中,“明眸似水,妙语如弦,不觉晓霜鸡唤。闻道近来,筝谱慵看,金铺长掩”;《薄幸·青楼春晚》中“尽无言闲品秦筝,泪满参差雁。腰支渐小,心与杨花共远”,《思佳客·江上何人一笛横》中“玉人水调品秦筝。细看桃李春时面,共尽玻璃酒一觥”,《倾杯乐》中“隔座藏钩,分曹射覆,烛艳渐催三鼓。筝按教坊新谱。楼外月生春浦。”凡此种种,都印证着吕渭老对筝的喜好,而且从词中我们发现当时已经有了专门的筝谱。
北宋苏东坡(熙宁五年至七年任杭州通判)曾与词人同好张先同游西湖,留千古词篇《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据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东坡在杭州,一日游西湖,见湖心有一彩舟渐近,中有一女风韵娴雅,方鼓筝,二客竞目送之。一曲未终,人翩然不见。公因作此长短句戏之。”熙宁七年仲冬(10月),东坡由杭州通判调知密州,在途经润州(今江苏镇江)时与友人集会于该地风景名胜甘露寺多景楼,席间留下了即兴之作《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又做《润州甘露寺弹筝》诗:“多景楼上弹神曲,欲断哀弦再三促。江妃出听雾雨愁,白浪翻空动浮玉。……”
南宋时,因宋金战争,政局动荡,音乐发展主流从宫廷流转到民间。虽有教坊,并专设有“筝色”①,然人才零落,礼乐则“率多未备”“权一时之用”。一些职业弹筝艺人流散于民间,宫廷需要用乐时,“迫呼市人”“临时点集”几成常态。然而这却使武林筝在民间的发展有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在《武林旧事》中记录了叫上名来的乐曲《会群仙》等数首,可见宋时筝在杭州已流传较广泛。词人韩疁(音liú)《浪淘沙·丰乐楼》中提到湖畔涌金门丰乐楼的弹筝韵事。丰乐楼,南宋杭州城(时称临安)官办酒楼。因傍西湖而享有“湖山之冠”美誉。“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中的楼指的就是这座丰乐楼。词中提道“三十六梯人不到,独唤瑶筝”。“独唤瑶筝”可以看出筝在宋代宴享中的地位之高。宋末元初的另一位寓居临安(今杭州)的典雅派词人张炎喜爱听筝、通晓筝艺,素来与歌姬筝女往来,为她们抒怀、代言,“把冰弦弹断,苦忆颜回”(《声声慢·中吴感旧》)、“漫长门夜悄,锦筝弹怨”(《解连环·孤雁》)等描述,以及“花最盛,西湖曾泛烟艇。闹红深处小秦筝”诸如此类,无不让人向往杭州筝乐流行的情景。元初另一位散曲家张可久,庆元(今浙江鄞县)人。他曾为桐庐典使、昆山幕僚,时官时隐,足迹遍及江浙、皖、闽、湘赣等地,晚年久居杭州西湖。他也是一位有名的筝艺家,留下了众多写筝乐筝人的散曲,如《越调·小桃红·夜宴二首》之一的“香风深院,明月十三弦”,《双调·水仙子·友人席上》“绛罗为帐护寒轻,银甲弹筝带醉听”以及《越调·凭栏人·晚晴小景》中写游历西湖观弹筝之“金羽翩,柳外莺,玉手膝上筝,晚风花雨晴,小楼山月明”。这位散曲作家凡宴席出游必弹筝助兴,以奏筝听筝为乐。凡此,均从侧面反映了筝乐在杭州流行之盛景。
周密②,词坛才子,“琴棋书画”莫不通晓。在其词中多处题写笛、箫、琵琶、筝等乐器。《四字令·拟花间》中“筝尘半妆。绡痕半方”、《齐天乐·蝉》中“槐薰忽送清商怨,依稀正闻还歇。故苑愁深,危弦调苦,前梦蜕痕枯叶”、《花犯·赋水仙》中“冰弦写怨更多情,骚人恨,枉赋芳兰幽芷”。筝在古人印象中,“施弦高急”“危弦高张”,弦易断、码易倾,故常以“危弦”来代指筝。“冰弦”意在强调制弦的材料,同样代指筝。词人蒋捷,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南宋咸淳十年(1274)进士(南宋灭,隐居不仕),是一位擅筝的隐士。在其存世九十余首词中,有数首提及笙箫、笛(横笛)、角、笳、秦缶、陶瓮、琴、筝乃至弦索合奏。“宝钗楼上围帘幕,小婵娟、双调弹筝,半霄鸾鹤”(《贺新郎·约友三月旦饮》)、“梦冷黄金屋,叹秦筝、斜鸿阵里,素弦尘扑”(《贺新郎·怀旧》)、“最堪叹,筝面一寸尘深,玉柱网斜雁。谱字红蔫,剪烛记同看”(《祝英台次韵》)、“新谱学筝难,愁涌蛾弯。一床衾浪未红翻。听得人催佯不睬,去洗珠钿”(《浪淘沙》)等等。尤其是末两首词,都提到了“筝谱”。《贺新郎》中是说很长时间不弹筝,致使筝尘积厚,雁柱网丝遍布,而且筝谱红色的谱字也淡暗了。《浪淘沙》则说,筝有了新谱,学起来相当难,都愁上眉头了。接上面北宋词人吕渭老一再提到“筝谱”的词可见,宋时,人学筝、弹筝均有谱可依可参了。再者,还有生于会稽(今浙江绍兴)的宋末词人王沂孙《齐天乐·蝉》“怪瑶佩流空,玉筝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如梦令》“妾似春蚕抽缕。君似筝弦移柱。无语结同心,满地落花飞絮”等。上面的词人都与江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筝入词,从侧面反映出江南之地,筝(艺)的流传之广,以及无论游玩宴享还是个人自遣都体现出文人们对古筝艺术的喜爱。
又传,为给康王赵构压惊,成立了专门的“安康社”,杭摊这种说唱艺术形式由此兴起。这种艺术形式随着民间盛行的瓦肆勾栏逐渐流播开来,且流传不衰。同时,民间的器乐合奏活动悄然兴起并渐成气候。19世纪初,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区在民间盛行丝竹音乐活动,发展到清道光年间(1821年)已具有一定规模。《嘉兴府志》中曾有“采苏杭之丝,截洞庭秀竹,变吴越佳音,集弦索精粹,江南有丝竹者也”的记载。晚清琵琶大家李芳园就是平湖派琵琶的代表,其后人不仅是平湖琵琶艺术的传人,亦是丝竹“清音”的能手。而比他更早一甲子之余的来自无锡的乾隆时期琵琶大家华秋苹,兼收南北而集成的《华氏琵琶谱》(嘉庆年间集成)更是近代浙江筝乐曲的一个重要来源,直接影响了现代浙派古筝艺术的发展。而集伴奏说唱于一体的杭摊艺术的职业艺人至清咸丰、同治的二十年间,竟多达三百余人,他们结社称“恒源集”,清末民初改称“安康正始社”,并且名演员辈出,鼓噪一时。据载,清末民初已有演奏丝竹乐的组织“文明雅集”,之后相继有“钧天集”“清平集”“雅歌集”等演唱昆曲、滩簧并奏丝竹乐的组织产生。演奏江南丝竹的组织有“清客串”和“丝竹班”两种。其中,“清客串”为市民阶层自娱性的组织,演奏的地点多在茶馆、私人住宅等,常奏八大名曲。这种丝竹乐的风格细腻淡雅。一般是在亲友婚丧嫁娶等场合前往演奏。“丝竹班”则是民间职业性的音乐组织,在农村中以吹鼓手兼奏者居多。其风格与“清客串”“清音”刚好相反,粗犷朴实而热烈。有些技艺精湛的民间器乐艺人也被召选入宫,专为皇家供事。
在清代末叶有确切记事的民间筝手、艺人是不多的。在《华乐大典·古筝卷·文论篇》收录有金建民所撰《中国古代筝手史料辑要》一文中的清朝(1644~1911)这一节中记录了一位叫“蒋檀青”的筝手。所撰如下:“蒋檀青,绍兴人,移居北京。善吹笛、弹琵琶,工南北曲,尤擅弹筝。咸丰(1851~1861)时任升平署内廷供奉,以多才多艺而负盛名。后遇战乱,避难于江淮间。为生活所迫,只得抱琵琶沿途卖曲为生,潦倒以终。”“升平署”是清代宫廷为管理演戏事务而专设的机构,始于康熙年间。该机构主要任务是收罗民间艺人,教习年轻太监和艺人子弟以为宫廷应承演出。署内的演员由太监充任的被称为“内学”,“外学”则是指民间戏班的职业演员,又被称为“内廷供奉”。从这里可以了解到蒋檀青是被升平署从民间选去宫廷的民间艺人杰出者,并有皇家银米供奉。然而,内外交困、战乱四起的时局,最终导致蒋氏命运潦倒以终。这种写照甚至是清末民初大部分民间艺人的缩影。在《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浙江卷》中亦有少许有关近代浙江筝的材料,在该集“综述”中说道:“浙派古筝,据演奏家王巽之(已故,1956年起任教上海音乐学院)说,浙江有王云程父子,在弹奏弦索大套曲上颇负盛名,1900年前后,名师蒋荫椿等人均得到他们的传授,善掐大套名曲。1920年蒋授王巽之大曲六七首,如《海青拿天鹅》《将军令》《月儿高》等。”
在民间能出一位技艺精湛的器乐手,在民间必然有草班传承的传统。而筝作为民间丝竹合乐或为说唱曲艺等做伴奏而延续承传也就不足为奇了。上面提到的王云程就是在清末民初散落于民间丝竹乐社的弹筝人代表。还有杭州清末丝竹艺人沈寄清在其1921年编“无师自会”《中国音乐指南》(世界书局印)序中写道:“我国之有丝竹,即我国乐,亦即我国萃也。其声之清逸隽雅,疾徐高下,使听者神往,且清新悦耳,怡情养性。尤为公余唯一有益心性之佳品。……余自幼即耽于此,迄今十余年。……”在册中还刊有《三六》《花六板》《四合如意》等江南丝竹曲谱。然大环境毕竟乃时局动荡之秋,民间的艺术受到巨大的冲击也是在所难免。然而却有一众志士,他们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影响,有着文化艺术共同的爱好,他们团结同好为优秀的民间艺术承传续命。20年代在杭州创办的国乐研究社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乐社。在这里,筝不仅存在于杭滩曲艺说唱伴奏这种形式中,还在丝竹乐合奏中占到了一席之地。而事实也恰恰如此,20世纪中叶之前包括说唱曲艺、戏曲音乐、传统器乐在内的各类社团纷起林立,古筝这件乐器通过民间丝竹合乐、滩簧等说唱曲艺等形式延续留存下来,并在新世纪逐渐脱离其母体,逐渐向筝独奏艺术发展,迎来她的新生。
注释:
①北宋循唐制设教坊,“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色有歌板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龙笛色、头管色、舞旋色、杂剧色、参军等色。”(吴自牧《梦梁录》),艺伎是属教坊管理。南宋时城内隶修内司、城外隶殿前司管理。管理上基本循北宋体例,“选取乐工弟子……准旧制”(《宋史·乐志》)。
②周密(1232~1298),祖籍济州(今山东济南),生于富春(今浙江富阳)。自幼随父周晋仕官四方奔走,转辗东南浙闽山水。景定二年(1261),任浙西帅司幕官。端宗景炎元年(1276)任义乌知县。宋亡,入元不仕,隐居湖州弁山。景炎二年举家移居杭州。始居洪福桥姻亲杨府,后杨府家业毁于大火,迁居湖滨杨氏别墅,后移居杭州癸辛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