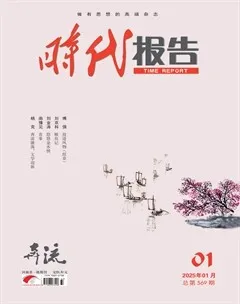狄氏春秋(连载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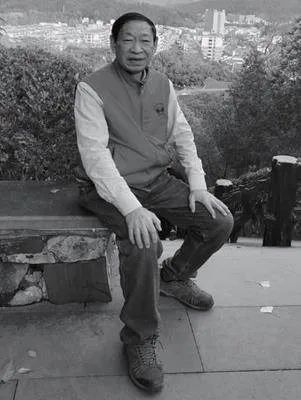
第二章 巨商承烈避乱石塘
承烈降世
福建闽县,位于福建省东部的闽江下游,是当时安稳时局下一个依山傍水、气候宜人的好地方。
这是一个下着绵绵细雨的傍晚,青石板铺就的路上湿漉漉一片,显出一份南方的温润之感。街道两旁的商贩在忙活了一天之后,大都已经回家了,家家屋里的炊烟就是催促他们回家的信号。只有一些旅店、饭馆依旧开着门,点起了灯笼,准备迎接晚上的客人。而那些青楼楚馆,此时才刚刚开门。
一个身材挺拔的中年人穿着官袍匆匆走过街道,行色匆匆,连伞都没来得及打,衣服头发已经被洇湿了一片,他却毫不在意。他的后面跟着一个匆忙奔走的家仆。街上的人看到他,都恭恭敬敬地喊一声“狄相公”,声音里饱含着恭敬。中年人虽然很是匆忙,但对这些淳朴百姓恭敬的招呼,还是含笑点头回应,谦和有礼。他,就是几年前刚来此地落户的狄群,当地人都尊称他为“狄相公”。
这天下午,狄群还在县衙办公的时候,突然接到家仆禀报,说夫人临产了。狄群赶忙匆匆了结手头上的事情,叫上家仆往家里走去,心里又是欢喜又是激动。
狄群在松林狄氏第十七世堂兄这一辈中,也算是一个佼佼者,不仅独自在外面闯出了一片天地,而且大小博得了一个官职。在外人眼里,狄群的有出息,就是狄氏家族世代官宦的最好证明。可是,在家族内部,他的地位却不怎么高,倒不是因为他不是大房后代,而是因为他年届而立,还没有儿子。他常年在外,但与松林老家还保持着通信联系,因此知道几个堂兄弟都有了子嗣,目前为止,他已经有了如琪、如师等四个侄儿。可是,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他,还不能为自己这一支续接香火。他是读书人,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看得很重,所以虽然如今在外面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在家族内部,始终有抬不起头的感觉。
去年秋天,他得知自己的夫人有了身孕,高兴得每日尽展笑颜。五月初九,孩子就要出世了,他的激动就更是可想而知了。他只祈祷,千万老天爷保佑,看在自己一向为民为善的分上,能给自己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
赶到家中的时候,孩子还没有诞下,只听得内房中夫人凄厉的叫声和产婆丫鬟来来去去的身影,这愈发让他心焦不已。可是按照规矩,他又不能进产房看看,只有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走去走来。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房中各处也点起了灯笼蜡烛。可是狄群的孩子依旧还在母亲的肚子里不肯出来,好像无比留恋那个温暖的世界。
狄群也还在院子里走着,只有冰凉的春雨才能让他的焦虑稍稍好些。家人来劝他进屋躲雨,却被他呵斥一番赶跑了。
突然,天上一阵霹雳打下来,漆黑的夜空霎那间被照亮了,然后就是轰隆隆的雷声碾压着大地的耳膜。狄群被这雷电一振,差点就跪在地上祈祷起来:“千万保佑他们母子平安!”
雷声隆隆不息,夹杂着闪电霹雳,衬托着这个雨夜越发难熬了。这雷电足足闪了又一炷香的时间,方才缓缓散去。就在雷声还在耳边没有完全消散的时候,突然狄群就听到产房里传出一阵“哇哇”嘹亮的婴儿啼哭声,紧接着就听产婆高叫道:“恭喜狄相公喜得贵子!”
听到这个声音,狄群终于忍不住一下子跪在了地上,感谢老天的庇佑。
这一年是西元1304年,元大德八年。这一年,松林狄氏第十七代狄群生下了第一个儿子,也是他唯一一个儿子,取名“承烈”。这一年,开启了狄氏家族一个新家族传承的传奇,开始了一段精彩纷呈的家族历史。狄承烈,就是这个注定要开启一个家族命运的——光明狄氏初祖。
少年轶事
“晚来总比不来好,晚来的儿子是个宝。”儿子降生之后,狄群没事抱着这个迟来的宝贝儿子,心里乐呵呵的,比吃了蜜还甜。
狄群不仅是当地人人仰慕的“狄相公”,而且是本地有名的文人,一向以“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自诩,连自己的书房名字都叫“桐叶楼”,因为他平生最欣赏的就是唐朝的陈章甫,更喜欢李颀《送陈章甫》那首诗,经常吟诵不绝:“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
对于这个30多岁才得来的儿子,狄群期望甚深,从小就开始教他背诵《三字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并给他讲解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以期能把儿子培养成一个饱学之士。元仁宗在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程朱理学定为考试内容。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狄群一面兴奋不已,一面为自己有先见之明暗自得意。从那开始,他对11岁的儿子要求更为严格,每天都要检查他的课业。
也许是由于狄群的要求太过严格,使得儿子承烈产生了逆反心理,也许是由于承烈遗传了父亲好动游侠的性格基因,对于读书,他实在兴趣缺缺。每到父亲要检查他课业的时候,承烈总是愁眉苦脸好像要上刑场一般,因为基本上他没有一次能按照父亲的要求完成课业,都要被父亲狠狠责罚。应付父亲的责罚,承烈倒是经验丰富,父亲的竹篾还没打到身上,他就开始大声喊疼,然后母亲肯定过来阻拦父亲责罚自己,父亲对他也舍不得真打,就这么雷声大雨点小过去了。闹到最后,父亲总是无奈地说一声:“儒子不可教也!”就转身回书房看书。
相对于读书,承烈兴趣更大的是“听书”。元朝的时候,说书已经相当发达,这个从唐代僧人讲“变文”衍生出来的行当,千百年后,已经成了普通百姓消磨时光、消遣找乐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当时百姓了解世界、分辨善恶的最重要渠道。随着说书先生口若悬河的讲说,一段段传奇的故事,一张张绚丽的图画,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就仿佛在承烈的眼前展现出来。他那聪明而善于幻象的小脑袋里,就装满了水浒一百单八将,三国里的成王败寇。不过,他最喜欢的,是大唐三藏取经的故事(后来吴承恩据此写成《西游记》一书),那一路上的惊险遭遇,那么多他想都想不出来的怪物和地方,让他做梦都梦到自己变成了那只猴子,跟随唐三藏走了好多地方,看了很多景致,经历了很多事情,醒来之后,他就想:要是我也能走那么多地方该有多好啊!
有一次父亲狄群要承烈读《史记》,几天后父亲问他:“承烈,史记里面的人物,你最喜欢哪一个?”
狄承烈想都没想就脱口说:“我喜欢吕不韦。”
父亲惊讶之下问他为什么。狄承烈说:“因为当一个商人可以走很多地方。”
小承烈的话让狄群失语了三分钟,他原想儿子会喜欢仲尼孟子,再不济欣赏韩信霍去病也好,谁曾想他竟然欣赏一个商人!儿子的“顽劣无大志”,让他感到惊讶、震惊。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劝说儿子,循循善诱道:“孩子,你要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有读书,你才能明白事理,只有读书,你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当上大官,才能光耀门楣。说书先生也应该说过,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读好了,你就想要什么都有什么了。”
狄承烈歪着脑袋想了一下,对父亲说:“父亲,你说得不对。说书先生说了,三教九流之中,九儒十丐,读书人的地位一点也不高。我不愿意读书,我要做一个商人,走很多很多地方。父亲大人你读万卷书,儿子我走万里路,岂不是个随所愿?”
听了狄承烈的话,狄群被噎住了。虽说在元朝中后期,皇帝也开始重视文教,重开科举,把程朱理学作为考试内容。可是当时读书人地位低的实际情况,不可能因为这一个命令就转变过来。所以,对于承烈的话,狄群也没法反驳。
又想想自己小时候对外部世界的好奇,自己对游侠生活的快意,狄群长叹一声,就没有再说什么了。从那以后,他就没有再逼着儿子一定要读书。父亲态度的转变让狄承烈有了更大的自由,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供自己支配。这个时候,除了听书和玩耍之外,狄承烈还有了另一个爱好,就是到账房师爷那儿,听账房师爷讲一些记账、经商方面的知识。
说来也怪,承烈对于读书缺乏兴趣,但是对这些看似比读书枯燥百倍的账目,却有着惊人的天赋,账房先生只要说一点,他就知道下面的应该怎么计算,碰到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办。这一点让账房先生惊讶不已,惊呼他为“经商奇才”,要不是承烈是老爷的儿子,他真有收他做徒弟的想法了。
跟账房师爷边玩边学的这段时间,给狄承烈以后经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有了这些知识作为积淀,加上他对于商业的敏感和广结天下豪杰的慷慨侠义,让狄承烈后来成为一代巨商。
经商之路
日子就这么无忧无虑地过着,不知不觉间,狄承烈就长到了16岁。
有一天下雨,狄承烈闲着无聊,一个人坐在小酒馆里点了一盘花生米、一壶老酒,自斟自饮自己解闷。这时,他注意到一个穿着土布短褂的强健男人站在小酒馆门前避雨,那个男人盯着自己桌子上的酒眼馋得很,狄承烈都能听到他喉咙吞口水的“咕噜”声。看那个男人的打扮,狄承烈知道他应该是在码头上给人扛包、做苦力的“苦哈哈”,但是他生性慷慨不羁,并没有因此瞧不起这个男人,反而对他很感兴趣,想要结识一番。于是,狄承烈邀请那个男人进来一起喝酒。那个男人看了他一眼,觉得这个公子很有诚意的样子,也就没有矫情,坐在长凳上喝了起来。
两个人边喝酒边聊天,他们都觉得对方言谈不羁、性格豪爽,很是对脾气,就交上了朋友,狄承烈也知道了这个男人叫赖阿牛。
那天之后,狄承烈经常找赖阿牛一起喝酒,跟他谈天说地,虽然赖阿牛说的一般都是他们的生活经历,但是对于从小在官宦富裕之家长大的狄承烈来说,却感到很是新鲜。从中他也了解到下层百姓的生活是多么艰苦,“丰年能吃饱,灾年无饿殍”,狄承烈听赖阿牛说,这是他们最大的希望。
一次狄承烈在街上遇到两个地痞,非要缠着狄承烈买他们在海边捡的贝壳。狄承烈对那个东西丝毫不感兴趣,可是两个地痞看他穿着华贵,知道他有钱,就死缠着他不放。这时候赖阿牛正好就从旁边经过,三拳两脚就把两个地痞赶跑了。通过这件事,狄承烈才知道这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赖阿牛,竟然有一身功夫,他就缠着赖阿牛学功夫,赖阿牛没办法,传了他一套“太祖长拳”。狄承烈如获至宝,每天勤练不辍,虽然没有修炼成什么绝世神功,可是却也身强体壮很少生病。
相交日久,一个偶然的机会,狄承烈发现,这个赖阿牛不仅有一身好功夫,而且还是传说中的“明教”中人。这个发现让他吃惊不已,也让他那颗年轻的心暗自兴奋和激动。
20多岁的时候,狄承烈开始做生意,一开始他收购当地的棉花到浙江、松江一带:一来因为松江有他的狄氏宗亲,二来因为松江有纺织棉花的技术,对棉花的需求很大。后者是他从来闽县探亲的松江的一个堂兄说的。他先是小批量地试着跑了一次,获利甚丰,第二次就把全部的本钱都投了进去,开始他真正意义上的商人生涯。
没想到,这次商人生涯并不顺利。他在路上遇到一伙江洋大盗,这群盗贼打着的就是“摩尼教”的旗号(当时,明教在福建称“明教”,在浙江称“摩尼教”)。狄承烈他们雇用的几个武师根本没有力量对付这群盗贼,就在他们手足无措的时候,狄承烈急中生智,跟那个盗贼首领说:“你们这伙人肯定不是明教的,明教中人只对付欺压良善的恶霸和官府,怎么可能拦路打劫我们正经做买卖的商人?”
那个盗贼首领就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摩尼教的事?”
狄承烈说:“我认识一个明教里的人,他为人善良淳朴,一点坏事都没做过。”
盗贼首领不相信,以为狄承烈冒充明教的朋友,以期躲过此劫,这时候狄承烈就说了赖阿牛的名字。听完,盗贼首领说了一句:“得罪了!”就带着人走了,狄承烈的东西他们一点没有动。这次经历,是狄承烈经商生涯的第一次危机,也是最大一次危机,如果这次失败了,他可能以后都不会再走经商这条路。
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狄承烈此后的经商之路可以称得上顺风顺水,很快就通过经商积累了万贯家财,成为当地的富豪。
26岁的时候,狄承烈有了一个儿子,按照族里的规矩,他给儿子取名务本。这时候,通过经商,他已经成为当地的富裕人家。经商有成,又喜得贵子,这段时间,是狄承烈最为顺利、也最为舒心的几年。他对已经年迈的父亲说:“父亲,经商也可立足,不一定非要诗书才能传家。”
但是,这时候的狄承烈还不知道,随着朝廷和天下大势的变动,他的人生轨迹,也将随之而改变。
商人领袖
狄承烈喜得弄璋之喜的那一年,他26岁,为西元1330年,至顺元年。此时,和狄承烈同年的元文宗图帖睦尔为帝,这是他第二次当皇帝,丞相是燕帖木儿。
两年前,就是这个燕帖木儿率兵攻入上都,拥立图帖睦尔为帝,因图帖睦尔兄长和世.游牧漠北,图帖睦尔采取燕帖木儿的建议,立兄长和世.,是为元明宗,图帖睦尔自己被立为皇太子;后燕帖木儿又毒死和世.重新立图帖睦尔为帝,改元天历,史称天历之变。
图帖睦尔再次为帝的消息传到福建,狄承烈闻讯,慨然叹道:“数年之内,重器屡迁,燕帖木儿玩弄朝廷于股掌之间,翻云覆雨,权势倾天。皇帝与丞相两不和,下凌于上,非国家百姓之福。”
果然如他所言,上面政局紊乱,下面的官员无所适从,贪污腐败之风横行,最终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在狄承烈35岁那年,他已经成了当地有名的富商,家资百万,上养老父,下育幼儿,家庭和睦。此时,他正处于人生事业和家庭的鼎盛时期。这一年夏天,一场台风袭击了福建沿海各县,狂风骤雨,三日不息。这毁灭性的天地之威,致使房屋被毁、庄稼颗粒无收。中产之家瞬间变为赤贫,贫困之家即刻就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
闽县县城内,随处可见衣不蔽体的难民,他们脚步虚浮无力,眼神里流露出的是深深的绝望。狄承烈从松江回来,亲眼看到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无力地在路上走着,走着走着老人就倒下了。狄承烈跑过去一看,老人已经没有了呼吸。他拉起伏在老人身上痛哭的孩童,定下决心:我要帮助这些人。这个孩童,十几年后成了狄府最忠诚、最能干的管家。
回到家里,狄承烈跟老父狄群讲述路上见闻,狄群此时已赋闲在家颐养天年,平时很少出门,听到狄承烈讲外面状况如此凄惨,不由道:“受此天灾,黎民受难,难道官府就眼睁睁看着不成?”
狄承烈长叹一声,说:“朝纲紊乱,官府腐败。那些当官的一心只想着剥取民脂民膏,哪里会真正关心百姓死活。更可恶的是有些商人,趁此机会,大肆囤积粮食,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狄群喝了一口铁观音茶,望着儿子说:“那你准备怎么做?”
狄承烈狠狠一拍桌子,道:“我虽不曾读许多圣贤之书,但是圣贤教导之‘仁’字不敢或忘,仁者爱人,即使不能救助太多人,但是即使把这房子拆了,我也要尽我的力量帮助那些人,否则,我这辈子良心会不安。”
狄群点头道:“好,你就按照你所想的去做吧,不用顾及家里。我为有你这个儿子而自豪!”
说做就做。当天,狄承烈邀集了几个相熟的商人,他们都是当地的富商巨贾,共同商量设立粥棚救助难民之事。被邀请来的商人大都心存犹豫,舍不得自己辛苦攒下来的家业。
见此情形,狄承烈站起身来,环视四周的人,沉声道:“我狄承烈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商人,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如果在平时,谁就是短了我一文钱,我也是不愿意的,即使拼了命也要讨回来。当年做第一笔生意的时候,我就遇到了几十个带着长兵利刃的劫匪,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没有退缩,硬生生把货物给保了下来。”
在座的商人听到他这么说,都会心一笑,大家都一样,不是为了那孔方兄,谁愿意冒着危险到处奔波,去做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商人?大堂的气氛稍稍缓和了一下。
狄承烈接着说:“商人逐利,这是天经地义的,自古而然,所以对于开粥棚接济难民的事,大家有所犹豫,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商人,但是,同时我们还是一个‘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人!作为商人,我们逐利,作为人,我们要有良知,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商人是一个身份,是一种职业,做人,如何做人,才是我们最根本的。如果连人都不会做、不配做,何谈去做一个真正的商人?”
顿了一下,狄承烈说:“如今,就在我们屋子的外面,有无数的百姓没有衣穿,没有饭吃,他们随时都会倒下,再也爬不起来。他们是谁?他们是我们的乡亲,是我们的同胞,是跟我们一样流着鲜血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所需要的,仅仅是一碗粥,就是这小小的一碗粥,就能让他们活下去,就是这小小的一碗粥,他们就会对你们感恩戴德。在这乡亲遭难的时刻,我不愿意躲在自己的屋里数自己柜子里的银票,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想象,若干年后,人们回忆起这次灾难,会有人问:那个时候,那些有钱人在做什么,他们为难民做了什么?我的子孙会为我的无作为而羞愧,我即使在地府里,也会感到自己的脊梁骨被戳得生疼。相反,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站出来,尽我们的力量去救助他们,几十年后,甚至几百年后,被我们救助的这些人的后代,他们会记得:在自己的先人陷入最困难的境遇的时候,是谁帮助了他们,他们会带着感激的语气念着一个一个的名字,他们会念到张玉峰,说到陈大云,说到……”他说到哪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就指着哪个人,被指到的人,不由得都挺直了自己的腰杆。
狄承烈的演讲起了作用,大部分的商人还是有着起码的良知和道德感的。最终,经过狄承烈的多方努力,两天之后,五家粥棚同时在闽县县城和几个城门边设了起来。无数的难民蜂拥而至,“狄大善人”的名字,也在这些难民感激的谈论中传播开来。灾难过后,那些靠着粥棚幸存下来的人们,都在家里设了狄承烈的长生牌位。
为了救助难民,狄承烈的家产缩水了一大半,但通过这件事,他也成了当地商人的领袖,谁遇到什么事,都喜欢找他商量,一个年轻商人说出了大家心里的所想:“去找他商量不怕被骗,因为他是一个有良知的商人,他不会干昧着良心的事。”
公元1350年,元至正十年,天下纷乱,盗贼四起。就在两年前,白莲教起义,黄岩人蔡乱头起兵造反,方国珍几个兄弟聚啸海上……但是这一年,商人们最关注的不是这些,他们最关心的是元朝政府下令变更钞法,铸造“至正通宝”钱,并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纸币。
发行交钞的消息传到福建,闽县的商人自发聚集到狄承烈的家中,商量这件事对商人的影响。
交钞的前身是宋朝时期在四川一带流行的“交子”,由几个大的银庄发行,代替市面流通的铜钱和银钱。因为交子携带方便,而且可以随时在银庄兑换,所以很受商人欢迎。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纸币的雏形。
懂得一点经济知识的人都知道,一张纸之所以能代替银钱充当交换媒介,前提是有足够的金属货币的支撑,而且发行者要有良好的信誉,百姓才会愿意用这些“纸”来交易。一般来说,对于信誉良好的交钞,商人们都是很欢迎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不用带上沉重的银子和其他金属货币跑来跑去,方便省事得多,也更加安全。可是,大家对交钞也很警惕,怎么看都觉得这一张纸比不上银两实在。
商人们聚集在狄承烈的家中,就是商量如何应付朝廷颁发的交钞。
商人们坐在狄承烈家的大堂里,品着狄承烈从松江带回来的上品龙井,相互交谈着,争论着,谁也说服不了谁,性格粗暴一点的争得脸红脖子粗,看样子马上就要拳脚相向了。只有狄承烈坐在红木椅子上,一言不发。
一个胖胖的商人见这样下去不行,就站起来说:“承烈兄一直没有说话,不知道你是怎么想这个事的?”
他话音一落,大堂里的争论就都停止了,纷纷看着狄承烈,想听听他说什么。
狄承烈不慌不忙地喝了一口茶,说:“我认为,交钞不能用,不用二十年,它就会变成一堆白纸。”
商人们纷纷大乱,又交头接耳地互相讨论起来,大堂里瞬时间又是闹哄哄一片。狄承烈的判断让他们一下子消化不了。
那个胖胖的商人再次站起来,制止了大家的争论,对狄承烈行了一礼,说:“承烈兄为何有如此说法?能否解释一下。”
狄承烈也不卖关子,说:“蒙古人入主中原,夺我神器,此乃亘古未有之事。蒙古人一向以异族自居,对待汉人,则极力打压。几十年下来,汉人们积累了太多的怨气。如果蒙古人能待民以宽,则还能勉强维护统治,可是,如今天灾频仍,政治混乱,天下人怨声鼎沸,蒙古人的统治,已经是强弩之末。现今白莲教与明教结合,势力庞大,有问鼎天下之实力;方国珍聚啸海上,基本切断了南方与朝廷的海上通道,朝廷财政困窘。如今汉人纷纷觉醒,只要打出‘驱除鞑虏’之口号,义旗所指,蒙古人必定望风而败。汉人之天下,终究要让汉人来掌控。你们说,蒙古人发的交钞,汉人朝廷会承认吗?我断定,二十年之内蒙古人必败,所以,二十年之后,中统元宝交钞必定成为一堆废纸。”
这一番议论有理有据,从天下大势的纷争走向着眼,让那些只盯着眼前的一般商人叹服不已,纷纷称谢而去。当然也有些商人并不认同狄承烈的判断,依旧坚持使用交钞,几年之后,这些人无不叹息:“悔不听承烈兄之言!悔不听承烈兄之言啊!”
果然,由于财政困难,元朝朝廷大量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物价上涨,交钞迅速贬值,民间百姓都不愿意使用交钞买卖,不用等到元朝灭亡,交钞就形同废纸了。
石塘霞晖
在浙江省的东南部,有一个叫石塘的小镇,这个地方临近海上,但是地方狭小,又不处于军事、经济重地,所以这些年外面的世界纷争不断、战乱连连,石塘镇,却依旧安宁平稳,在这乱世之中,就像一个世外桃源。
几年前,石塘镇上新迁来一户人家。这户人家一来到这儿,就买下了一个大院子,出手阔绰。他们家里的下人都穿着精美、身强力壮,跟本地居民的相对贫弱一对比,显得煞是显眼。一开始,本地居民对这个外来户有些警惕,走路都远远绕过这家宅院,好像生怕被这家人欺负一般。没到一个月,村民们就改变了态度,原因是这家人并没有因为富有而显得盛气凌人、高人一等,却显得谦谦有礼、待人接物都很随和。前一阵子因为粮食歉收,李家寡妇带着五个孩子马上就要断粮,五个孩子饿得都没有力气叫唤。这个大户人家的主人偶然路过,看他们可怜,就送给了李家几袋粮食,李家寡妇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人家,只有跑到人家大门口磕了三个响头。从此以后,当地人都称这户人家叫“狄善人家”。
这户在石塘镇落户的人家,就是狄承烈一家。
原来,由于朝廷腐败无能,加上天灾人祸,各地的盗贼、起义军此起彼伏,战乱不断。狄承烈见闽县很不太平,顾及家中老少的安全,所以决定在别的地方找个落脚之处,自己则在两处走动,等到战争平息下来,再把家人接回来。
可是,战争越打越烈,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1348年的时候,就有方国珍聚众海上,跟元朝朝廷作对,不仅打劫朝廷海运粮草,一般的商人也遭了池鱼之殃。不久,他投降了朝廷;没过几天安生日子,却又反水了。此后他又好几次或投降或反叛,搞得人们晕头涨脑。加上福建又有陈友定死战朱元璋,闽浙之间,在这反反复复中,越发不太平了。无奈之下,狄承烈狠心结束了在闽县的生意,跟着家人一道来石塘避难。
把家人送到石塘前后,狄承烈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儿子的事。
决定在石塘另外安家是在他40多岁时作的决定,这时候,他儿子务本已经14岁了。狄承烈自己小时候不爱读书把父亲气个半死,但是对于儿子务本,却要求他一定要好好读书,不能有一丝一毫懈怠,要求之严厉,比他的父亲不知道厉害多少倍。
狄承烈因为在当地商人中威望甚高,所以关于他的小道消息也是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他的家事,不少人也都知道。狄承烈要求儿子读书的事,就使得有些商人以此开他的玩笑。有一次在茶馆,狄承烈跟几个商人闲聊,其中一个就说:“承烈兄小的时候很是有个性,令尊逼你读书,你是死也不答应,还以‘九儒十丐’之说反驳之。但是现在承烈兄却要求令郎读书,且甚为严厉,这不是逼迫令郎‘不肖乃父’吗?”
同坐的商人都笑了起来。狄承烈却道:“诸位笑话我,我却不以为可笑。你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还敢请教?”其中一个商人见他说得甚是郑重,问道。
狄承烈道:“我当年不读书,部分是由于顽劣不堪造就,也是因为当时读书无甚用处,所以转而经商。以现在情形看,我当日的选择,乃是正确的。可是,那是几十年前的选择。诸位岂不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乎?现今之势,元人必败,汉人得天下,乃是必然之势。试问一旦汉人得天下,当以何者为尊?自古以来,有‘士农工商’之说,商人卑贱,自古而然,因为元朝是蒙古异族统治,所以情况才不一样。可是,汉人得天下之后,必定不会沿袭蒙人所为,只会传承汉人传统,读书人在将来几十年内,必定重新成为四民之首,商人的地位,将再次沦为社会下层。所以我要求犬儿读书,实是因为大势所趋不得不尔。”
一番话下来,再没有商人敢嘲笑狄承烈的作为,他们都在琢磨着怎么来为自己的儿子重新安排将来了。
狄承烈对儿子的严厉教育取得了成效,务本小小年纪就博通经史,那些被请来教务本读书的秀才先生,都对他赞不绝口,纷纷说:“狄家二郎,将来定非凡品。”让狄承烈高兴得比捡了三千两银子还要高兴。
狄承烈隐居石塘的时候,务本小小年纪,已经考中了秀才,前途可谓无量。狄承烈在家无事,儿子又不用他操心了,无聊之下,竟也捡起了多年不看的书本,读起书来。每日晨起打打拳,上午读几卷诗书,下午到村中逛逛,跟村里人讲讲外面的世界,充当他们的“说书先生”,其乐也融融。
未几年,元至正22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奠定下了统一天下的霸业;1367年,朱元璋败张士诚,1368年称帝,建都南京,国号“明”。
但是这些事,跟狄承烈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他安安稳稳地呆在石塘,享受着平和安静的暮年时光。1367年的一个夏天,朱元璋称帝的前一年,家仆们很奇怪老太爷早晨没有起床练拳,叫了几声也没有声响,进门走到他床边,却见老太爷安静地躺在床上,好像睡得很熟一般,把手探到他的鼻孔下,老太爷已经没有了呼吸,家仆大惊,带着哭腔喊道:“老太爷西去了,老太爷西去了!”
狄承烈在睡梦中结束了他63岁的生命。下葬于面对曙光的石塘山。他睡梦中会梦到什么?小时候被父亲逼着读书?听赖阿牛诵读《光明经》?经商遇险?赈济灾民?还是教养儿子读书?
没有人知道了,也没有必要知道了。光明狄氏初祖狄承烈,有一个精彩的人生,留下了一个绵延千百年的家族后代。这,就够了。
作者简介:
狄绍梅,1938年出生。1958年起开始在《东海月刋》《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等多种报刊发表诗歌。2023年在《浮玉》刊物上发表长篇纪实文学《心迹喜双清》,2024年11月,杂志社为其召开作品研讨会。一生挚爱文学,晚年致力于纪实文学和回忆录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