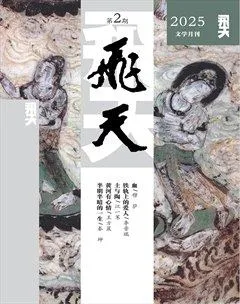半明半暗的一生(组诗)
与父夜饮
有一年大雪,酒后
父亲在院里磨刀
一边磨,一边发誓
要宰了欺负我们的仇人
那时的他,二十多岁
有着公牛一般的脊背
和闪电一样的脾气
现在,坐在我对面的父亲
已被岁月的溪流,冲刷出
满脸沟壑。他胆怯、寡言
低着头,自顾自喝着酒
夜色中,像一件喑哑的酒器
现在,又有大雪扑窗
与我对饮的男人
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
几乎就是刚刚,我才发现
对面这座沉默的大山
在时间的大雪中,已慢慢
白了头
酒"器
一生嗜酒的人,会把酒
当作这世上另外的亲人
一生嗜酒的人,酒杯或碗
会长成他身体里的器官
一个无依无靠的人
整日以酒度日
现在,平整的进村道路上
多了一只,踉踉跄跄的酒器
夜"雨
拉开窗帘
看灯光扑进雨声中
平静、舒缓
神的催眠曲
有一种沉甸甸的安宁
让我想起白天的稻田
金色照亮河谷两岸
这是收获的季节
玉米的骨头长满黄金
如果祖父活着,他将跟随
此起彼伏的鸟群重返田野
土地慈悲,深秋的田野
又一次安抚了,一个农人
半明半暗的一生
回多乐屯
我们在黄昏之时抵达多乐屯
父亲站在昏暗的庭院里迎接我们
他刚刚从地里回来
衣服上沾满泥巴和鬼针草
那个固执寡言的人
朝我们笑着
院里的暮色是铜质的
他脸上的笑也是铜质的
我们空着双手,没有什么
需要递给彼此。只有他
还习惯性地握紧拳头
还习惯性地,紧紧攥着
刚从地里带来的,暮色和秋风
繁"花
落在沟渠里的花,覆盖了流水
又被流水交给了河流
落在瓦片上的花,覆盖了屋顶
又被屋顶交给了春风
落在祖父脸上的花
也落在怀里的孩子身上
春风慈悲
吹醒了村庄
也吹醒了屋后的山坡
满山繁花,把祖母的新坟
又往天空的方向,抬了抬
暴雨来临之前
一场暴雨来临之前
会让满天的乌云
提前告知
那件佝偻在地里的衣服
直起身子
找到一处可供避雨的地埂
或者灌木。一场暴雨来临之前
会第一时间,提醒斗笠和蓑衣
在电闪和雷鸣中,找到那个
惊慌失措的人
一场暴雨,会下在清晨
让准备出门的水牛和犁铧
再歇一歇。一场暴雨
也会久久地,悬停在黄昏的天幕
等牛羊从山上归来
等锄头和竹篮到家了
才灌下来
过白水镇
这个午后
再次经过白水
工业时代的小镇
有一座火电厂
一座铝厂
两只巨大的胃
不分昼夜地反刍着
人们按部就班的一天
头顶是即将坍塌的乌云
320国道上
行人稀少
操着不同口音的货车师傅
忙着运输各自的生活
火电厂的烟囱
像几根高耸的柱子
支撑起白水镇摇摇欲坠的天空
白色的烟雾往上攀爬
让大地对天空的支撑
获得了一种坚实的延伸
过白水镇
我也只是匆匆一瞥
路上奔跑着铁
卖菌子的人还没有下山
骤雨初歇
就在刚刚,那个坐在山坡上
痛哭的女人,哭塌了天空
那么多倾泻而下的泪水和哀嚎
那么多令人惊惧的闪电和雷声
从她的身体里,喷涌而出
她那么瘦小,却装得下
那么多悲伤和绝望
她那么胆怯,却敢一个人
坐在昏暗的坟地里哭
现在,骤雨初歇
雷声消散。惊魂未定的人间
只剩头上的闪电,还在
一刀刀,割着天空的皮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