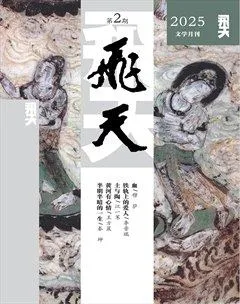字词中的日常凝视与哀矜(评论)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朱熹注曰:“言君子但因所见在之位而为其所当为,无慕乎其外之心也。”这一来自古人的规约,不仅关乎如何行事,也可引申为某种疗救当下诗歌写作弊病的洞见:诗人不应沉溺在对宏大叙事或“诗与远方”的幻象中以虚假主体身份假声歌唱,而是将自己置身于真实处境中感知、体验,然后书写。这是理解和判断现代诗的一个标准。质言之,在字词中凝视日常生活,在沉思中反刍那些曾经草草吞咽的生活之细枝末节,以便重新感知被时代的光与暗笼罩的琐碎而平庸的日常之诗性与力量。江一苇的写作就是在对往事、故人、出生地与生活琐事的不厌其烦的悲悯书写中为普通到凡庸的生活抗辩:“我需要唱歌来为自己壮胆/以便好好活着。”(《歌唱的秘密》)
一
读江一苇的诗,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微小事物的眷念。在他笔下,“阳光收起了它的锋芒/所有卑微而渺小的事物/都在尽力避让,安静地活着”。他试图用文字的微弱光芒照亮这些事物,使它们的存在被看见,“而庞大的事物总是看不见的/它常常逼着我/将眼泪收回去”。正是感受到了庞大事物对个体而言那无形却巨大的压力——庞大事物坚硬无比,它们不相信眼泪,更不会珍视泪水,这些普通人会为之动容的卑微而渺小之物,这压力犹如鞭子,诗人像羊儿“在一条鞭子的驱使下走向回家之路”。
江一苇将自己的出生地选马沟在诗中置于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在第一本诗集《摸天空》中,第一辑“选马沟记事”用41首诗来深描一个位于渭河源头的小村庄,其中有对父母、堂哥、友人、乡亲饱含情感与悲悯的书写,也有对此地以耕种为主的生活诸多细节的描摹与呈现,一些诗作直接题名为诸如《选马沟的冬天》《选马沟的牛》《选马沟的口音》《选马沟的秋天》等。通过这些作品,江一苇为自己出生和成长的村庄在纸上镂刻文字肖像,使得这个在地图上可能根本不会标出的小村庄重新诞生。但他对选马沟的书写,不是陷入怀乡病泥淖的虚假美化,而是离开多年后依然葆有的一种源于内部眼光的体察与省思。“在选马沟,我喜欢的事物不多/虽然她是我的出生地/但每次提起,总有过于沉重的底色”。“我只是喜欢这里的安静”“田野里劳作的人们/地下沉睡的人们,互不干扰/各自安于各自的生活”。(《我喜欢的事物》)诗人清醒地认识到,“选马沟没有忧伤的事情/农民的忧伤看不见,没有内容”。并非没有幸福与忧伤,而是因为“乡村的语言太匮乏了”,当人们想试着说出自己的情感与生活时,总是止步于“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这是面对家人反对,但他仍坚持在诗中不断书写选马沟的原因。
在新近出版的诗集《献诗》中,第四辑“雨落选马沟”收录诗作42首,选马沟依然在其书写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选马沟是一座巴掌大的村庄,落后,闭塞/老一辈的人们,很少有人读到初中。这里的人/只信一个理:只要肯出力,地里就会有好的收成”,这里的人认为在外工作的人都手无缚鸡之力,没用。因此“我”向他们吹嘘“说不定哪天、我的诗会选入你们孩子的课本”,此后一起喝酒的人沉默,然后频频向“我”敬酒,他们表示也希望孩子们多读书,能外出工作。在此诗的结尾,“我”惭愧之余顿悟:“这世上也没有一首诗,是写给目不识丁的农民”。(《把一首诗选入课本》)在另一首《流水的一生》中,“在外面我常常这样介绍自己,我是渭河发源地人。在渭源/我也常常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锹峪河边人/但我从不介绍我的出生地/因为即便说了,也没有人会知道/这里的河流没有名字,它只是一年年流着/正如一个人的乡愁,它只会翻山越岭,永不干涸”。正是这农民被诗歌遗忘的命运与流水一般永不干涸的乡愁,使得选马沟始终在江一苇的诗歌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但他的乡愁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乡之情,而是蕴涵着某种复杂的现代性体验:一方面,他意识到“在同乡眼里,我是选马沟的叛徒”“而事实是,我已经有十多年/不曾下地劳动。我只是将父母/置身于想象的青山绿水间/将乡亲,安放在虚构的日升月落里”;另一方面,他也清醒地察觉到不仅自己被生活改变了,更重要的是那个念念不忘的地方也在时代中被改变了,“当我终于回到了故乡/我发现,在一排排破败的房屋前/我早已没有了故乡”。江一苇的诗歌很少使用“故乡”这个词语,在很多地方使用“出生地”来称呼选马沟。对他而言,“我有一个出生地,但我无法叫她故乡/那里大多数人已不相识”。这执拗的对两个词语的语义差异的强调凸显了某种现实与情感认同方面的断裂与矛盾。他写道:“其实,这些年在外面,我也有乡愁/我的乡愁是小时候滑过的冰车/是溪畔的野花和青草,蹁跹的蝴蝶/是上学路上分食的一块糖和撕下的糖纸/是一头牛,瞳孔里的白云/被蓝天的画布染成了希望的颜色”,乡愁是记忆中那些承载昔日快乐的具体事物,现在已遥不可及,“故乡是越来越厚的隔膜”。
在《雨落选马沟》一诗中,习惯在下雨时给母亲打电话问询庄稼长势和收成情况的“我”,面对“六十多岁的母亲,去县城务工/已有三月。县城的活计无关庄稼只关乎工时”这一新现实,加之老实的母亲严格遵守“上工期间不能接打电话”这一规定。“我”手足无措,乡愁已经被时代的变化所斩断。这无疑是一种现代性的乡愁,不仅离乡者改变了,更重要的是那个承载着记忆与情感的故乡也已沦陷在时代的浪潮中了。
面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变化与沦陷,江一苇说:“我只在我的诗里写下对他们的爱。……明知表达的无用和不确定,却总身不由己。”通过那些亲人们看不懂且视为无用的诗行,他用自己的爱与悲悯将出生地选马沟铭写在文字中,在字词中重新命名和创造了一个故乡。
二
江一苇在《墓志铭》中写道:“我的一生只在做两件事:写诗和原谅别人/写诗是为了有借口活着/原谅别人是为了能原谅自己”。读他的诗,会发现这两件事往往是一件事:写诗其实就是他原谅别人和原谅自己的方式。这里所谓“原谅”,不是居高临下将别人视为过错方的宽恕谅解,而是一种水平的凝视,是对别人生活和情感的体贴入微,体现在诗歌形式上,呈现为一种不加评判的叙述。
“我曾见过一位善于画雪景的画家/现场作画——/他依次在纸上画上了远山、峭壁、古松、苍鹰/一幅冬雪图就完成了//整个过程,他没有一笔//是在画雪,而雪却早已笼盖了四野。”这首题为《冬雪图》的诗作可视为江一苇对诗该如何写的夫子自道:不是带有评判的讲述,而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叙述呈现来渲染烘托诗意。要呈现不要讲述,换言之,叙述者的特权受到限制,不在叙述中进行概括和评判。这已成了福楼拜以来现代小说的某种不易原则。诗歌领域对这一原则的挪用和实践,体现在对叙述的倚重已成当代诗的重要形式,造就了不少杰作,但其弊也日益显现,诗人有时混淆了作者和叙述者,往往在诗尾对前面已经通过叙述完整呈现了诗意进行蛇足式概括或评断。
江一苇在创作中采用叙事化策略来呈现日常生活本身诗意的作品为数不少。在《怯懦的英雄》《父亲的秘密》《犁地的父亲》《农妇王芝香》《那时候的爱很穷》《编耱的堂哥》等描写亲人的诗作中,通过第一人称叙述对细节进行描摹,使得亲人的形象跃然纸上,亲切感人。如《怯懦的英雄》中,我因为“父亲一生胆小”“曾常常嘲笑他的畏首畏尾,也曾常常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自惭形秽”,但当父亲数次在危险来临时将我护在身后,虽然他的双腿还在颤抖,还是少年的“我”重新对父亲的观感发生了变化:“我从未在现实中见过英雄/那一刻,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我从未告诉过他这个秘密,我只是默默记住了那一刻/并将他写在了我三十二开的作文本中”。通过描写“我”对父亲认识的变化,呈现了我对勇敢的重新领悟和成长:能让一个胆小的人变得在紧张颤抖中仍然选择了勇敢面对的,唯有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而《犁地的父亲》中:“我跟在父亲身后,默默地看他犁地/其实父亲不喜欢我跟着他/他说泥里滚爬的孩子长大没出息/可我就偏爱这样看着他/看他像个小学生一样,在一块块/不规整的作业本上,认真地写下一行行字迹”。虽然诗是事后的回顾,但这种将“叙述者我”切换到“亲历者我”的、从成年视角向童年视角回归的“二我差”置换使得整首诗童趣盎然,亲切感人。
这种用充满感性细节呈现的叙述使不可见的情感变得可见可感,让人觉得真实可信。江一苇在《农妇王芝香》中围绕着母亲的名字这一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常常被忽略不计的细节展开叙述,其中暗藏某种难以言说的爱却无法表达,“我长这么大从没说过爱你/是因为村里没有这样的语言,说了,你也不懂”。他是深谙乡土社会文化语法的人,在乡土传统中情感教育和表达都是匮乏的,“爱一旦说出,就会变得可疑”。《那时候的爱很穷》叙述了某次我和母亲去山上打蕨菜,“往回走时/天空忽然下起了暴雨/跑往山下的途中/我不小心滑倒/从山上滚了下来/母亲顾不上解下背篓/直接顺着我摔倒的方向/老鹰扑食一样跳了下来/山坡上撒落的全是又鲜又嫩的蕨菜”。这样的叙述亲历者之“我”的所见与后来的叙述者之“我”的所见形成张力,前者看见的是母亲“老鹰扑食一样跳了下来/山坡上撒落的全是又鲜又嫩的蕨菜”,后者则感叹道:“那时候的爱也很穷/亲人之间除了生命/再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来”。后者无疑是一个已经成熟到足以理解这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的行为,能领会其中所蕴藏的一个母亲对儿子不顾一切的爱,才能在回顾中打捞这些充满爱的细节,用文字构建的感性细节去擦拭那些当时并不理解的行为之情感意义,使其在文学光芒的照耀下可信可亲。
这些叙事的诗,其意义是不在日常生活之外去寻找某种具有超越性的事物,不耽溺于诸如远方、异乡之类虚幻想象之物,而是将目光重新投向当下的日常生活,呈现生活本身的诗性。诗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而是以说话的方式重新凝视普通到似乎不值得一提的日常生活世界,在克制而不动声色的概述中夹杂着对具体细节的再现,以此来爆破日常生活本身的凡庸包浆,使其内在的诗性显现出来。诗人的写作不是某种凌驾生活之上的审视,而是一种重新跃入生活世界的凝视。这凝视将自己置身于芸芸众生之中,故而能以一种谦逊而温良的姿态来看待他人和自己。江一苇大量写亲人的诗,充满了对亲人的温情与理解,也有不少篇幅书写生活中认识或陌生的人,比如渭河源头的麦客、那个身患阿尔兹海默症修理时间的人、住在隔壁却不认识的女人,以及“这个镇子上出了名的穷人”。在《穷人》一诗的前半段,概述了此人不仅穷,而且命途多舛,没有亲人,遭遇诸多不幸,行为乖戾,领导和富人都怕他躲着他。这概述是其他人眼中的穷人,诗人看见的是:当他被卡车压死后,亲戚们蜂拥而来无比激愤地使他的命价一涨再涨,但“没有人注意到/还有个半大的孩子/面无表情地站在炕沿上/持一张崭新的奖状/糊着裂缝的墙壁”。对具体的细节的深描,具有“刺点”式力量,使人在感叹愤怒中对穷人的处境和生活产生了悲悯。
“在人间/必须要给自己最大的同情”,这并非自恋,而是源于江一苇对自我的体认:“忽然觉得自己就是正被赶去屠宰的羊群中的某一只/瘦弱,矮小,还一直在埋怨跟不上大部队的脚步”。(《在闹市》)正是这种清醒地将自我置身于芸芸众生中的认识,使得他的诗既不高于生活,也不低于生活,而是以内部视角去呈现日常生活平庸中的诗性与力量。江一苇自称他的写作“很庆幸,还能和土融为一体。”日常生活的泥土被悲悯温良的情感之火烧制而成的诗,犹如历经千百年留存下来的碎陶片,“即便碎了,依然坚硬无比”。
责任编辑 郭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