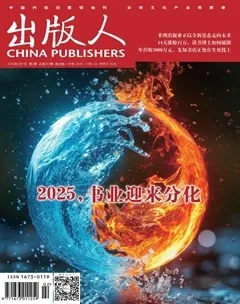放声歌唱:儿童文学的史诗性表达
张忠诚近年来创作了一系列关于东北抗联的儿童小说,新作《谁在林中歌唱》延续并拓宽了其平民英雄书写实践。“歌唱”是一个重要的叙事元素,对小说的故事情节、情感基调、叙事结构和人物命运等方面发挥了统摄作用。这本书采取了音乐叙事与成长叙事叠加、缠绕的协奏复调叙事结构。这种结构使得个人命运、时代变迁与歌唱融为一体,形成同构与互文结构,为东北十四年抗战谱写出《义勇军进行曲》一样激扬的史诗性颂歌。
歌唱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既是一种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情感和更新认知的工具,又荷载着“撄人心”的独特艺术内容,撬动起关于世道人心、家国情怀的复杂主题。
每一次歌唱都与人物命运、历史进程、革命情感紧密相连,体现了个体在苦难中的反思与成长。小德子发现了哥哥已经牺牲的真相以后,情绪低沉,郁郁寡欢,说不出话。荷姐为他写了一首歌。他抱着白桦树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他胸中“那一团团的悲伤化成轻薄的雾气,散开在了春天的树林里”,那首歌也最终演变成一个全新的文本。这种由绝望悲伤到期颐,由等待迟疑到坚持笃定的对比和翻转,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革命队伍的温暖支撑下,在自我苦难的救赎与消解之中,孩子们内心对生命和未来的希望之花次第绽放。德子的复杂情感形态以具象化的方式在歌曲变奏中流淌、变形演绎、升华,对亲人的悼念之情升华为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念、不屈意志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这种用歌唱书写情感变化和精神升华的叙事手法,使得小说的叙事更加丰富和立体。
齐声合唱也是小说中歌唱的一个重要形式,承载着深刻的社会和心理意义,体现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合唱时,每一个人放声歌唱,又聆听来自四面八方、不同音色、不同腔调的听觉力量,以“立体环绕音响”的感官狂欢一再确认个人对于宏大声音的敬献,就像涓涓细流汇聚成为革命能量的浩瀚海洋。这就是从“我”到“我们”的认知萌芽,“小我”汇入“大我”的集体主义意识觉醒的仪式。
歌唱更是情感感染力和抒情爆发力的有效载体。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吟唱,如《摇儿歌》《哈达歌》,这些旋律或激昂奔放,或低沉柔美,构成了一幅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让读者深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人民的坚韧。合唱团在湖边学校重生,谱写的校歌表达了面对艰难困苦时的乐观和勇气。面对日寇的围追堵截,他们唱起了“起来歌”,在歌声和枪炮轰鸣中突围。“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这个场景中,在战场的惨烈、战士的柔情的反差和映衬中,悲愤的情绪、不屈的意志、宏伟的气势都成为合唱多声部的一种,作品也因此迸发出强烈的感染力和爆发力。至此,《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家的声音标志,作为中华民族的听觉共同体,穿透了空间的界限,跨越了历史的界限,甚至破除了小说的文本壁垒,凝聚起爱党爱国爱人民的“默契同盟”。到了故事结尾,小德子也独当一面,实现了新一代人在战争中、苦难中、在歌声里的觉醒、成长和崛起。
在创作中,张忠诚巧妙创设了音乐叙事、心灵成长叙事两条线索,二者互相缠绕、虚实交融,音乐的抽象性和心灵的内在性相结合,使得叙事既有实体的情节推进,又有抽象的情感流动,建构起东北十四年抗战时期人民大众的“情感结构”。人物在音乐中找到慰藉与力量,实现了精神独立和心灵成长;音乐与人物命运的唇齿相依,随情感脉动更新迭代,赋予了音乐更复杂多重的审美意象。《谁在林中歌唱》以多棱镜的形式再现了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的革命者的奋斗史,歌唱了那片土地上、那片森林中无数平民的英雄气概与抗争精神,成为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史诗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