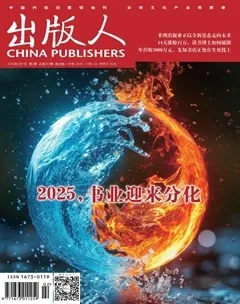余泽民:“弃医从文”的多元人生
他期待国内出版业能为这些海外的中国文化传播者搭建长久、稳固的平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
如果说,生活的妙处在于每一个明天都是未知的,那余泽民在过去数十年里,从中国到匈牙利所走出的轨迹,称得上是一部冒险小说,过程中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转折与惊喜。
如今,作为海内外知名的旅匈作家、翻译家、大学教授,特别是作为中国出版业与匈牙利文化界的重要桥梁,余泽民回看自己走过的路、尝过的苦、遇到的人和经历过的事,他说自己就像一只变色龙。
余泽民毕业于临床医学和艺术心理学专业,在布达佩斯诊所做过医师,后来又陆续当过厨师、老师、家教、记者、导游,还写过剧本,演过电影,“现在踏实下来当作家,搞文学翻译,还为中匈双方充当书探,扮演了出版中介或代理的角色”。他原创的文学作品、翻译引进的匈牙利文学作品屡屡荣获各类文化奖项。例如2017年,余泽民获得了“匈牙利文化贡献奖”(Pro Cultura Hungarica díj),他的译著马洛伊·山多尔《烛烬》获得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译著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撒旦探戈》获评2017新京报·腾讯“年度十大好书”。2002年10月,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余泽民协助作家出版社引进了《英国旗》《船夫日记》《另一个人》《命运无常》四本书的版权,并承担了翻译工作。此后,他持续译介中匈经典文学作品,被誉为“匈牙利文学的中国声音”。
在他荣获“匈牙利文化贡献奖”时,颁奖词里有一句话说:“他一个人相当于一个机构”,余泽民非常喜欢这个评价:“这二十年来,我确实是以一己之力将当代匈牙利文学‘搬’到中国的。现在粗算一下,我翻译出版了约三十部书,如果算上在杂志里发表过的,总共译介过近百位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五分之三是匈牙利的。现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疯狂。”
“弃医从文”:多元身份下的文化探索
余泽民说:“年轻的时候不信命,人到中年我开始信。我这大半生都在不断变换身份,其实是命运的指引。”
自高中起,他就是一个文学青年,怀揣着坚定的文学梦想,对经典文学作品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看《红楼梦》,我能把练字写秃的毛笔‘葬’在院子里的枸杞树下;看《封神演义》时,我能坐在廊檐下的青石台阶上看天上变幻的云发呆,想象斗法的天神和厮杀的天兵”。在北京医科大学上学时,余泽民不仅读厚厚的医书,还读中外名著。同学们争着选“内”“外”“妇”“儿”几大热门科室,但他出于对人性的好奇,选择去当精神科医生,因为他觉得那里会有故事。偶然的机遇,本科毕业后他进入中国音乐学院读艺术心理研究生,多年后回想当初这个决定,他说自己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在那时就潜意识地认为这个专业离人性更近、离文学更近。
1991年,26岁的余泽民带着异国梦,只身登上了前往匈牙利的火车,决定独闯世界,如他所言:“想趁着年轻,光着脚到世界上走走。”那时的他还不知道,在前方等着他的是怎样明暗交织的生活,那里有他无法想象的“生活的鞭挞”,也有让他钟情一生的文学和荣耀。他把自己想象成《在路上》的主人公,想有朝一日写一本自己的《在路上》。于是他开始写日记,写周围发生的人和事,写自己的所思所想,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靠近文学。这些日记后来成了他写小说的一手素材,取之不尽。这段艰难的岁月,虽然充满了挫折与无奈,却也为他日后走上文学之路埋下了种子。
回看自己“弃医从文”并远走异国的经历,他说,自己这大半生所学的知识或本事全都没有浪费——学医学,让人的身体对他来说不再神秘;学心理学,使他对人性产生了极大的敏感和关注,也培养了观察力和理解力;学艺术,放大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与激情;出国闯荡的经历,更是让他在生活的锤炼中,不得不将所有本领都使出来,一旦有机会就要紧紧抓住。
比如他后来创作的《纸鱼缸》,作品里运用了药理、生理和解剖知识;翻译《平行故事》,书中也常涉及身体文化和医学知识,作者纳道什在创作过程中,也曾多次向医生朋友请教医学问题……专业的医学背景,让余泽民在翻译或创作的时候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丝毫不会露怯。
机缘巧合:所有的路都通向文学
而后来走上翻译之路,在余泽民看来也是“老天的安排”。
1993年,他在匈牙利借住在一位从事出版的朋友家,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匈牙利著名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也就是《撒旦探戈》的作者,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好朋友。1998年,他还陪同拉斯洛来到中国,沿着李白的足迹走访了很多文化名城,这段经历不仅加深了他们的情谊,也让拉斯洛深受触动,甚至将余泽民写进了自己的书中。回到布达佩斯后,余泽民对拉斯洛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他是我这辈子认识的第一位作家,而且我们在中国朝夕相处了那么久,我很想知道他写了些什么”。彼时,恰巧房东出版了拉斯洛的小说集《仁慈的关系》,于是他便翻着字典,吃力地读了起来。最初,他只是想通过翻译自学匈牙利语,便尝试着翻译了其中的一篇《茹兹的陷阱》。由于对匈牙利语语法和文学表达的不熟悉,他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篇八九千字的作品的翻译。但正是这次艰难的尝试,让他逐渐掌握了翻译的技巧,也让他对匈牙利文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自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翻译,三年内陆续翻译了十几位作家的二十几部短篇作品,并对匈牙利文学深深着迷。
而故事的开头,他提到的那位房东——亚诺什,就是因为余泽民的医学技能而结缘的。据他讲述,刚到匈牙利不久,亚诺什曾到诊所找他看病,后来更是在他处于生活低谷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让他借住在自己家近十年。他们二人亲如家人。亚诺什是匈牙利文化名人、出版家,因为余泽民而喜欢上了中国文化,20世纪90年代亚诺什出版《道德经》《易经》时,余泽民还帮忙手写了书中的中文部分。许多年后,他和妻子艾丽卡又帮助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其他国内出版社向匈牙利推广中国图书,他们与亚诺什默契合作,共同出版了《山东汉画像石汇编》《中国年画集萃》《汉字》《中医关键词》和《中华文化与思想术语》系列。
2002年,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出版机构竞相争取其作品版权。经过一系列戏剧性的波折,余泽民与作家出版社的两位年轻编辑郭汉睿、朱燕联手,开启了自己作为书探的首次尝试。他精心挑选了四部书籍推荐给出版社,并协助他们拿到版权。随后,他将自己之前积累的翻译作品发给他们,得到了编辑们的肯定。于是,他便开始了长达两年的熬夜翻译工作,完成了《英国旗》《命运无常》《船夫日记》《另一个人》等作品的翻译。
凯尔泰斯的作品在国内成功出版后,余泽民的专业能力迅速获得了业界的认可和赞誉,他也顺势成为国内出版业在匈牙利文学领域的书探。在他的努力下,几位在国际上极负盛名的匈牙利作家的作品被陆续引进中国,包括艾斯特哈兹·彼得的《一个女人》和《赫拉巴尔之书》,道洛什·久尔吉的反乌托邦小说《1985》、马洛伊·山多尔的《烛烬》和《一个市民的自白》等。
搭建桥梁:让中匈文化双向互通
从26岁那年乘坐火车抵达匈牙利的一刻开始计算,迄今,余泽民已经在匈牙利生活了33年。谈及这么多年来,哪种身份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他给出的答案是“中国人”。
33年来,他的生活被北京和布达佩斯两个地方平分,但他始终是中国国籍。近年来,他还被聘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欧洲学院特聘讲课教授,时常需要回国授课,每次一待就是一个月左右;同时,他还是匈牙利罗兰大学翻译学院笔译课程专业导师、匈牙利鲍罗什学院文学翻译课程专业导师。多重身份下,他得以结识不少中匈双方的优秀作家、翻译家、编辑;再加上他本人从事翻译和写作工作,熟悉双方的文学和图书市场,既了解作家,也了解读者。所以作为一名书探,他扮演的角色远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版权中介,他置身其中,身体力行,在翻译和创作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加深对中匈文化的理解和共情。
谈及自己在中匈文化传播上的优势,他提到了妻子艾丽卡。艾丽卡的身份与他相似又互补,她是匈牙利汉学家,毕业于罗兰大学中文专业,还曾在中国留过学,如今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翻译过鲁敏、邱华栋、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艾青、杨练、吉狄马加、梅尔的诗集,以及一些中国艺术、历史、文字相关的图书。有些专业性较强的书籍,如《汉字》及涉及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的《中国时刻(全四册)》,则是他们二人合作翻译的。余泽民特别提到:“吉狄马加的诗集《我,雪豹》是艾丽卡翻译、我校订修改的,我们还请匈牙利著名诗人拉茨·彼特和苏契·盖佐在我们译稿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进行‘匈语诗歌化’,像这样三方合作打磨出来的诗歌译本,我相信是品质‘最奢侈’的译本。”在翻译《山东汉画像石汇编》和《中国年画集萃》时,他们还请来了知名汉学家姑兰(匈牙利原名是卡尔玛·伊娃Kalmár éva),“姑兰于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她在中国生活过15年,主攻戏剧和当代文学,她的加入为我们的译本又把了一道关”。就这样,他们夫妇二人携手,架起了一座双向互通的中匈文化传播桥梁。
在余泽民的经验里,中国古典文学在匈牙利乃至欧洲范围内影响很大。“在匈牙利,我认识的读书人家中,几乎书架上都有一本匈文版的《道德经》;早在五十年前,孔子、老子等先贤的哲学经典,屈原、李白、杜甫等人的诗集就都有了匈文版。《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在匈牙利都流传甚广。”
但他也坦言,在对外翻译传播中国经典文化的过程中,译者少,好译者更少。“老一辈汉学家大都是做学问的,有水平、有情怀,也有韧性,每个人都有自己专攻的领域。比如陈国老先生专攻古典文学,高恩德老先生专攻现代文学,姑兰专攻戏曲和当代文学,而且他们一做就是一辈子。”反观现在,海外懂汉语的人里能真正被称作“汉学家”的很少,多是翻译或“中国通”,迫于生计,愿意沉下心来做文学翻译的人屈指可数。
另外,他还着重提到,翻译和出版资助对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至关重要。“比如,匈牙利有汉学家想翻译阿来的《尘埃落定》、张炜的《古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还有学中文的学生想翻译严歌苓、白先勇的小说,但是他们需要翻译和出版资助;匈牙利当地出版社对中国的文学新面孔又缺乏了解,不愿冒险。”所以,中匈双方对此的支持非常重要。他特别强调,中国出版业的“走出去”不仅要考虑如何外译,还应该考虑外译成功后如何进行有效的宣传推广,这些都需要实打实的资源投入,需要有人真正落地执行,而不该停留在表面和形式。
“很多身在异国的中国文化从业者都对推广中国文化满怀热情,但光靠我们个人的情怀和资源,这些事情难以持久地做下去。”他期待国内出版业能为这些中国文化传播者搭建长久、稳固的平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
余泽民的故事,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部冒险小说,更是中匈两国文化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生动注脚。他会锲而不舍地往返于中匈文化之间,也在这座双向互通的桥上,期待更多同路人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