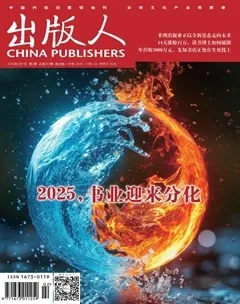寒风中破局
市场下行与书业底层逻辑的坍塌互为因果,共同指向了书业诸多不可承受之痛。
我们可能要接受书业市场端持续下行的现实了。
出版转制国企税收优惠政策得以延续、全民阅读的推进力度仍在持续加大、图书生产端仍保有较大规模……这些利好消息无疑提振了行业的信心。
变化也一直在发生。人工智能带来的新一轮技术浪潮同样在出版业掀起了波澜,中信出版、果麦文化等出版“大厂”均已投入其中;图书品牌化成为大众出版市场的趋势,多家出版机构强化了旗下产品线的品牌化力度;文创、谷子成为热门板块,上海书展变身文创展、“谷子经济”驱动资本市场增长,也让书业看到了相关板块的潜力;课后服务成为地方出版集团转型的重要抓手,多家地方出版集团将之视为头号工程;市场教辅的爆发式增长令人瞩目,与投流书一起托举起零售市场的体量;渠道的变革一刻也没有停歇,书业对视频号、小红书这些内容平台的爆发天然地敏感,一有迹象就会一拥而上……
市场的凛凛寒意也被绝大多数从业者所感知。2024年下半年以来,多数出版机构的反馈都是“每况愈下”,有资深出版人喊出,这是从业以来最难的时候。数据可以佐证。开卷数据显示,2024年总体图书零售市场码洋同比下降1.52%,总体(不含教辅教材)市场码洋同比下降4.83%。总体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1129亿元,恢复到2019年的88%。中金易云数据显示,2024年图书市场码洋为1111.64亿元,同比下降10.50%;当剔除文教类的刚需产品后,其他大类图书销售同比下降17.23%。综合来看,不仅图书零售市场规模连续出现下滑,作为出版业基本盘的教育出版也面临挑战——评议教辅的监管政策日趋严格,人口红利的消退也让教育出版市场的前路变得越发难测。
不仅如此,市场下行的不良反应已经开始向出版全产业链蔓延——经销商爆雷、出版机构缩减品种和人员规模、中小型图书公司现金流紧张成普遍现象、文化纸厂家订单近乎负利润、许多印厂机器空置……
回顾过去几年里各书业媒体的盘点总结,从业者们已经对“拐点”“迷茫”“逻辑崩塌”“经验失效”等诸多关键词脱敏,但到了当下这个节点,所谓的“盘整期”已经是一种乐观表达方式,在认知层面,出版人或许要做最困难的准备了。
困境
市场体量下滑的背后,是出版人遭遇的多方面的困境。
渠道乱象已经到了让书业无以为继的地步。折扣只是一个老问题。过去,传统电商平台叠加了优惠券、满减等政策,图书的实际销售折扣在数据统计时体现得并不明显。内容电商的崛起进一步拉低销售折扣的同时,也让折扣数据更直观地体现出来。开卷数据显示,2024年1—11月,少儿类、社科类、文艺类图书在内容电商的销售折扣分别为36%、42%、47%。这一组数据相比整体市场的图书销售折扣更具参考价值。再考虑到流量费用和销售佣金,也更残酷地体现了图书在内容电商平台的利润空间。
不仅如此,和其他消费品类似的是, 在内容电商渠道,图书的流量生意也成为“白牌”绞杀的战场。过去两年里,内容电商的图书品类涌入了诸多“流量玩家”,他们利用流量玩法和资金优势,通过买断版权拉高图书定价,压低图书折扣,跑量投流。这种流量生意要求出版机构既要在组织结构上有极强的快速反应能力,又要有极致的成本压缩能力。因此,受限于版权与印制成本、内容调性和原有的渠道优势的传统出版机构,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几乎都无法染指。这类公司往往选择刚需性强的少儿和教辅图书作为主营品类,以大量生产雷同内容进行测试的方式,找到适配算法倾斜的产品,既改变了消费者对图书折扣的认识,也抬升了算法的流量费用。在激烈的竞争之下,这门生意也越来越不好做:许多公司从一开始的薄利多销到投流微亏,寄希望于流量能溢出到其他平台,再到现在,已经将图书定位成课程、咨询等高客单价产品的引流品, 靠流量卖书的利润空间也越来越狭小。除此之外,这类产品往往以高定价的套装形式出现,抬高了整体市场的码洋规模,表面上托举了市场体量,在码洋数据统计层面缓冲了图书市场的下行,实际上却给多数出版机构制定增长目标提供了错误的判断依据。如果去除开卷数据统计中“内容电商销量占比超过90%”的图书产品,再来看市场规模,数据显示,去除这部分产品的销售数据后,2023年开卷监测的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为664亿元,2024年1—11月的这一数据则为658亿元;与之对应的是,2019年开卷统计的数据为1286亿元。这或许可以大致体现出图书市场下行之后的真正体量。
把眼光放到产品端,长销品和腰部书的衰退更值得警惕。电商平台的图书榜单在失效,阅读推荐的核心也从阅读推广人转变为以销售为目的的主播。因此,过去许多年里出版机构赖以生存的长销产品和作为“现金奶牛”的经典图书,在这一轮渠道洗牌当中被大量淘洗出局,新的品种又很难在短视频电商这种容量小、销售周期短的渠道里迅速成长为销售主力。图书市场的销量结构也出现了分化,二八定律不再适用。开卷数据显示,2024年1—11月销量前1%的品种对应码洋贡献达61.9%;销量前5%的品种,码洋贡献高达83.7%,相较于2023年,这两个比例都有所提升。滞销书也在扩大,《出版人》在2024年的一篇稿子里分析道,2019年至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销量数据中,年销售数量小于5本的图书平均占全部图书品种的34.3%;年销售数量小于10本的图书,平均占全部图书品种的43.8%;2023年销量小于10本的图书超过百万种,这无疑指向腰部图书的衰退。出版业尤其是大众出版赖以生存的“风投机制”开始失效,长尾效应正在失效,书业生产系统的平衡被打破,品种冗余的生命力转化成了产能过剩的负担。
这一现象也给整体市场带来了极强的不确定性。虽然图书零售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供给侧驱动市场,但是市场链条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如今,出版机构的茫然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经营确定性的缺失。
合作伙伴是不确定的。有的经销商因为经营不善留下一笔呆坏账,有的因为不想再守着图书微薄的利润而转行;一年前辛辛苦苦建联的1万个达人里,可能有8000个来年就不卖书了,头部达人正在放弃图书业务……业绩是无法规划的。阅读的需求在转移,做新书越来越难,根据中金易云的数据,出版机构只要卖出1.1万册左右的书,就能进入新书销量的前1%。市场的量会从何处来无法预估,算法的眷顾是一个“黑箱”,一条短视频就可能引爆一本书的销售。但这种爆发又是速朽的,开卷监测《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这本老书在2024年实现了近300万的销量,峰值月销超过70万册,但是仅仅半年后月销量下滑到不足3万册,这样的大起大落可能非常考验决策者的心脏和机构的投流费用。
头部出版机构在内容端必然追求更强的确定性,例如到期的畅销书版权拍出高价,把公版书玩出新花样,大举进军热门品类并以此扩大规模,提升老书的运营力度。中小型出版机构则尽一切可能降低风险,压缩品种规模,压缩人员规模,大众出版的中小型图书公司的最终归宿可能就是小工作室或者个体户。
可以说,在当下,书业的出品系统和销售系统都遭遇了极大的调整,品种规模和码洋规模都失去了意义。回到业务去审视,书业从一个创意、创造型产业,几乎已经变成了劳动密集型、生产型产业,出版业越来越像制造业,享受不到内容、版权的红利,利润微薄,但是又无法以销定产。版权不属于出版机构,要么是作者的,要么是海外出版机构的,因此由版权衍生的商业开发出版机构自然无力涉足;在用户端,出版机构也没有主动权,用户数据被互联网平台所掌握。不论是对上游作者的创作支持,还是对用户的增值服务,多数出版机构都无法提供。
代价
市场下行与书业底层逻辑的坍塌互为因果,共同指向了书业诸多不可承受之痛。
首要的是书业的管理模式亟须优化。
一方面是考核不科学带来的动作扭曲。当下,码洋作为行业通行多年的单位,已然失去了统计价值,但是仍有不少出版机构将发货码洋和回款的绝对值作为考核的主要指标,这也导致了“超发超结”成为不少出版机构的应对手段。过去两三年,因为业绩压力陡增,部分出版机构“超发超结”的力度进一步加强,有的出版机构甚至在当年11月就已经预结第二年第一季度乃至上半年的销售回款。除此之外,过去书业的账期普遍在一年以上,如今由于内容电商的崛起,账期被压缩到3~6个月,在某种程度上也致使出版机构未来业绩被提前透支。
当市场处于上行阶段时,这种“寅吃卯粮”的方式并不会有负面影响,甚至会驱动出版机构不断增长。问题在于,当增长不再,那些在年底“怼”出去的货又将如何消化?一家出版社的发行人员在盘库时发现了一年前发出的货原封不动地被退回,包装都没拆,只能沦为直播间的引流瑕疵品。不仅如此,“超结”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论是提高返点还是降低销售折扣,都会压缩出版机构的利润空间。可以预计的是,如果市场形势没有发生变化,出版机构的业绩压力会进一步加大。2025年,可能有部分机构会面临一季度甚至上半年“净发为负、回款为零”的危机。
这实际上是短期考核带来的矛盾。国有出版机构肩负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任务,势必要完成特定的指标任务,但是在实际考核中很难评估出版作为创意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指标,因此出版的长期主义就非常仰赖管理者本身的眼光、能力甚至是道德品质。对于中小型民营公司而言,虽然没有实质性的考核指标,但是普遍现金流紧张,迫于生存压力也很难做长远布局。
另一方面是出版企业制度性的落后。时至今日,“一本书的实际盈利”对于多数出版机构来说仍然是一笔糊涂账,出版机构往往既算不清楚成本,也监测不了实销,同时在机构体外有大量的“僵尸库存”。缺乏零售能力的出版机构困在一个个B端客户里,在各类条款上受制于人,尤其是面对电商平台时,既掌握不了定价权,又被随意退货。
转型的迟缓也让出版业面对需求转移时缺乏工具。很遗憾的是,出版业在过去日子比较好过的时候,并没有真正解决转型方向的问题。轰轰烈烈的“数字化转型”并没有给营收业务带来新的支撑点;自研内容也鲜少培育出成熟团队,IP研发也主要是“拿来主义”;由于缺乏并购路径,市场上也没有出现能够与平台抗衡的集团或者联盟;对比海外出版集团商业模式的转型,国内出版转信息服务、出版转教育、出版转娱乐,也未见有明显的迹象。
这些无疑都是危险的信号。出版的价值仍旧存在,依然承载着人类文明进步和文化传承的使命,但是出版机构的日子可能不好过了,正如著名出版人佘江涛公众号的一篇稿件里所说的:“出版有未来,出版社不一定。”出版机构应该如何思考未来,找到生存路径?
何解
无论如何,分化已经到来,如何迎接新的市场结构与业务逻辑?我们走访了许多出版人,收获了几个关键词。
调整预期。对于书业而言,经历了21世纪头20年的高速增长,面对市场可能持续的下行,从资产管理方到管理层再到业务一线,或许都要适应新常态,重新调整预期。对于机构而言,如何从追求量的绝对增长转向质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精准。这是一个被出版机构频繁提及的方向,选题和营销的精准将成为基本要求。因为市场通道狭窄,泥沙俱下、草莽发展的内容生态不复存在,“拍脑袋”和“微操”带来的伤害可能比之前要大许多,盲目的选题决策和跟风的代价出版机构将难以承受。对于出版机构而言,当腰部的价值不再,可能需要重新思考自身的使命与定位——要么追求一年出10本书改变世界;要么做100本有精准用户与流量保障的书,在极其细分的领域里拥有定价权,品牌化就是路径。这是一道选择题,也可能根本没得选。营销的精准在于出版机构设置议题、引领舆论的能力逐渐式微,从过去放卫星、“雨打沙滩万点坑”的营销方式变成了带着内容敲开一个个小型会议室。当经典图书的共识消退,营销的精准也承载着重塑经典的使命。如今一代人的经典图书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垂直细分领域的图书需要新的生态位构建。行业从来不缺优质的内容,但是优质内容如何响应这一代人对于国家、社会乃至个人关键议题的认知需求与情绪需求,需要营销的介入。果麦对《窄门》的营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一本100多年前的小说被塑造为“纯爱”作品,并收获相应的销售回报,这也是通路。
回归人本身。人工智能所描绘的未来图景还未完全展开,但是这一年的噪声已经让各行各业感受到了技术浪潮的势能。对于书业机构而言,必然要充分跟进技术变革的趋势。但是追逐的目的是什么?过去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指望这个老行当真正驾驭技术浪潮,那么技术革命中区分人与机器的边界,重新找到“出版人”的定位,就变得尤为重要了。那些人工智能做得很好的,人力就应该转向,让位给效率与成本。对于出版机构而言,最终还是要回到出版人本身,这个行业说到底是人的事,因此,如何在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乃至业务方向塑造平台以聚拢超级个体,释放创意效率与商业能力,或许是大型出版集团的方向。
跳出出版。需要承认的是,图书距离内容消费的中心越来越远了,新一代人在接触纸书之前,已经被包括短视频、游戏在内的其他内容形式驯化过了,等他们成长起来,还真的会爱上阅读吗?这或许是存疑的。现在来看,“谷子”、二次元、文创这些概念层出不穷,过去许多小众的内容消费需求已经成长为主流了。出版机构也是时候跳出出版,更换话语系统,再重新思考如何去抓住未来这一代人的阅读需求,才能有真正的一席之地。
无论如何,书业有其韧性,也有其核心价值和自身逻辑,终究会跨越周期,重塑产业生态。而在当下,向新而行、步履不停远比坐在屋里做乐观或悲观推测更有价值。■
——2018年上半年馆配市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