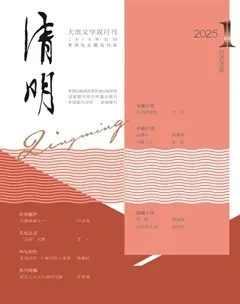岭南讲座之一
第一讲:开场的话
同学们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在岭南大学的教室里相遇。中国有句古话,叫“教学相长”,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老师的教和同学们的学,大家可以一起进步。
你们的老师告诉我,第一节课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同学只是先过来试听,听过第一节课后,才会慎重考虑要不要选这门课。
这多少让人感到有点紧张。我本来就对上课有种天然的恐惧,不知道怎么当老师才好。现在听了这样的提醒,难免会变得更加紧张,更加手足无措。不过,我也私下安慰自己,如果真没有多少人来选这门课,也挺好。人少了,或许我还可以更轻松一些。
对我来说,人生最害怕的事,就是当众演讲。必须非常坦白地告诉同学们,我几乎没有上课的经验,是一个没有真正当过老师的人。想到现在居然要在讲台上讲课,还要坚持一个学期,我真的很慌张。
毫无疑问,我是个“菜鸟教练”。熟悉体育的同学,一定知道菜鸟教练这个词。菜鸟教练很可能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新手,他匆匆上任,冒冒失失地就来了,并没有多少教学经验。好在事情都有二面,菜鸟教练的好与坏,可能我都会具备。
首先说缺点,我并不知道同学们想听什么,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同学们感到满意,不能投各位所好,这显然是不太好的一面。其次,我也有好的一面。我是一个有实践的写作者,有太多关于写作的体会和感悟,这些都可以和同学们分享。我想我会很认真、很努力地教学,绝对不偷懒,尽量把这个课上好。
事实上,在很多年前,我也曾经当过一年的大学老师,但是并没有坚持下去,原因有几个:
一是那时候我太年轻,不相信老师可以教好写作。大学生嘛,大多是很狂妄的。文科生尤其狂妄,觉得用不着去听老师讲什么写作。二是,我不想面对一群没什么写作经验的大学生。我的经验告诉我,学写作还是要靠自学,靠自己去写。写作这玩意,老师是教不了的。
当然,还有最关键的第三点,就是我接受的是非写作教育。那时,不管是哪个大学的中文系,或多或少都有着看不上写作的传统。
我自己就是中文系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算是科班出身了。可大学老师给我们的教导,都是别光想着写,别想着当什么作家,中文系不出作家,想当作家没必要上中文系。老师谆谆教导,前两年一定要泡图书馆,必须一头钻进资料堆里,千万不要急着写什么论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因此,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还真坐了三年图书馆的冷板凳。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作为一种常见的保守观点,不仅会影响学生,也影响着老师的实际教学。我所在的大学,有一个传为美谈的风气,就是述而不著。越是有名的,有一肚子学问的老先生,越是没有写过几本书。
譬如黄侃先生就不喜欢写书,不喜欢著作。他老人家指导陆宗达先生研究《说文解字》,简直就跟闹着玩一样。他拿出一本《说文解字》,让陆宗达先生去标点,并且对自己的学生提了三点要求:一、所标标点不要求全对;二、所读内容不要求都懂;三、通读之后不要求全记住。
我想中文系的学生,应该都知道《说文解字》这本书。这是一本工具书,是古代的《新华字典》,不过要比《新华字典》更博大精深。陆宗达先生开始老老实实地去标点,态度很认真,不仅标点,还要写上密密麻麻的注解。等他终于完成了,信心满满地拿去给黄侃先生看,像通常的优秀学生交作业那样。
没想到黄侃先生接过他的作业,看都不看,直接就扔进了废纸篓。然后,黄侃先生又递给陆宗达先生一本新的《说文解字》,让他回去继续标点。如此反复,连续丢进废纸篓三本《说文解字》后,黄侃先生告诉陆宗达先生,这个活你算是干完了,该学的东西差不多已经学到了。
陆宗达先生后来成为小学方面的大师,在文字训诂领域,有着非常高的地位。他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在如今的电脑时代,听起来有些古板,有些落伍,然而在学界则传为美谈。那时候,大家觉得做学问就应该这么做。
事实上,我觉得同学们在学习写作方面,可以参照黄侃先生要求学生的三个要点去做。不要求全对,不要求都懂,也不要求全记住,只要能够全身心投入就行。
我读硕士研究生时,导师是叶子铭先生。他是学古典文学的,研究方向是苏东坡。因为他大学三年级时写的学年论文《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轰动一时,他后来改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成为研究茅盾的权威。叶老师做学问的方法也是十分古典的,他经常跟我们说,对于茅盾的一生,他甚至比茅盾自己还熟悉,可以说,他比茅盾还了解茅盾。茅盾什么时候写了什么,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与谁通过信,谁骂过他,凡此种种,他无不知晓。茅盾的家人要查找什么资料,要核对什么信息,经常写信向他打听。
叶老师对我们的态度非常宽松,我们去他家里上课,先是聊天,然后他便把我们赶进图书馆,让我们去看旧刊物,查旧报纸。学期末的考核也很简单,写个象征性的读书报告就行,汇报一下自己看了什么,花了多少时间。有想法最好,没想法也可以。
叶子铭先生花了很多精力研究茅盾,用的是研究古典文学的态度。后来,他成为研究现代文学的学科带头人。我是叶老师带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在同门弟子中,我的岁数最大,算是大弟子。可惜最后我未能继承他的衣钵,属于典型的不肖子弟。在同届叶老师的五个弟子中,我是唯一没有拿到博士研究生头衔的人。
叶子铭老师是个很认真的人。他说起胡小石先生,说他老人家名士风度,改学生作业,抱起一堆作业就扔出去,摔得最远的那一份,给最高分,然后依次递减,差不多快低到及格线时,再往回调。我听叶老师说起这件事时的语气,一方面,他是赞成要死读书的,另一方面,他又十分佩服胡老先生的名士气,不太看重学生的作业。毕竟是学生,作业能好到哪里去?所以作业好不好根本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学习方法。
事实上,考试分数和作业,对于中文系的大学生来说,有时候确实不太重要——起码不像大家想得那么重要。教学,教学,首先是教会学生如何学。路要一步步地走,学霸和学问,本来就不是一个概念。学霸无非是比别人聪明一点点,更会考试而已,而学问不是靠聪明和会考试就能获得的。传统的中文系教学,更看重的是坐冷板凳的功夫。从表面上看,好像更在乎的是一种形式,就仿佛行为艺术,并不在乎内容。比如说,你怎么标点《说文解字》不重要,你怎么泡图书馆也不重要,关键是你要这么做,能这么做就好。
这样做究竟对不对呢,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心里也一直在犯嘀咕,到今天也仍然没完全弄明白。
中文系究竟能不能出作家呢?这个话题在目前还是充满了争议。不久前,广州中山大学的谢有顺教授,曾在朋友圈里发过这样一条内容:这十几年来,毕业于中山大学,在全国影响力最大的作家是文珍、王威廉和冯娜。他们分别就读于金融系、人类学系、公共传播系,没有一个是中文系的。真诚请教:这只是个案还是各大学的普遍规律?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是普遍规律,直至今天似乎依然如此,谢教授发的这条朋友圈就是证据之一。考察以往的历史,看一看今天的现状,中国的很多作家并不是中文系出身,这绝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真要掰手指算一下,大陆出作家最多的大学,相对而言,可能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了。他们有一个全是作家的硕士研究生班,这个班人才济济,不仅出了作家,而且还出了大作家。
但这种情况也禁不起仔细推敲。明眼人都知道,北师大的这个硕士研究生班里,很多人之前已经是作家了,他们能进中文系,能去攻读这个学位,首先是因为他们已有的创作成绩。像余华和莫言这样的作家,还有迟子建、刘震云,他们的加入,只是为学校锦上添花罢了。
还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当作家可以不用经过大学文学系的培养。譬如说海明威和福克纳,他们甚至没有上过大学。又譬如契诃夫和鲁迅,他们都是学医的。事实证明,不上大学也可以成为作家,学医的人也可以成为作家。
说来说去,说到现在,我几乎一直都是在打自己的脸。因为我说了半天,无非是在说中文系不一定能培养出作家,或者说中文系轻视写作。既然如此,我作为一名从中文系出来的作家,为什么还要跑到这个教室里来,给中文系的学生浪费口舌,说这些反话呢。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而最说不清楚的,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写作。应该怎么教写作,应该如何进行创作,可能注定是个说不清楚的话题。既然说不清楚,何必又要拿到课堂上来硬说呢?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说一说自己的真实想法。
首先,我当年进入大学时,中文系的传统虽然是不鼓励同学们写作,轻视写作课的,但是,在私下里,并不是所有的先生都是这么认为。
当时,南大中文系的陈瘦竹先生跟我父亲认识,他知道我进了南大中文系,便让他的学生带信给我,让我去他家。我老老实实地去了。这位陈先生不是以老师的口吻,而是以家长的语气,给我布置了功课。他让我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每周写一篇散文,每个月写一篇小说,每天学两小时古文和两小时外语。
陈瘦竹先生是学外语出身的,他的专业是西方戏剧研究,他是研究莫里哀的,可是他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位私塾先生。他说,如果是别人,我不会这么要求,对你则不一样,你应该照着我的话去做。当然,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我当作家,只是为我将来做学问打基础。他认为不管做什么学问,写作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很看重写作。
这是陈瘦竹先生与别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他的这种观点不拿到课堂上公开讲,却要向我私下传达,我觉得还是与中文系的传统有关。传统不是轻易就可以改变的,大家必须尊重传统。
时至今日,这种传统显然是禁不起推敲的。我们必须用另外一种眼光,对传统进行重新思考。毫无疑问,我能够成为作家,陈瘦竹先生私下为我开的小灶,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不敢说自己完全按照他的话去做了,但起码是很努力地这么做了。我下功夫学古文,下功夫学外语,不停地写。乱写和多写对我来说,效果确实好。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攻读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前面已经说过,我的导师是主张学生泡图书馆的,主张学生在图书馆里没完没了地看原始材料。从研究的角度说,这样的学习方法确实比较扎实,听上去也更有道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钱谷融教授。钱先生毕业于我的母校,他辅导学生的方法,却与我母校的传统很不一样。钱先生的方法在当时可以说是别具一格。他认为时间宝贵,主张要尽快投入,在一开始就要明确你准备写什么,研究哪位作家。他让自己的学生先把研究课题早早准备好,然后在读研的三年时间里,全力以赴研究你准备的作家,完成一本专题著作。
记得我的导师对钱先生的这种教学方法表示过质疑。我的导师认为,学生应该先进图书馆,先撒开网,进入要研究的时代,感受时代气氛,然后再决定自己研究什么。我的导师觉得学生一点基础都没有,冒冒失失地瞄准一个作家,就开始写书了,似乎着急了一点。
事实证明,钱先生的教育方法更有道理,更有效,也更容易出人才。他的弟子显然比我们更出色,其中一位就是岭南大学中文系的前系主任许子东老师。许老师当时研究的是郁达夫,他一门心思钻研郁达夫,很快就完成了一本书。从结果看,同样是攻读现代文学专业,许老师是我们那一批里最快出成绩的。
钱老师培养了许多优秀弟子,与许子东同届的还有一位王晓明老师,也是非常著名的学者。记得我和王老师曾一起聊过天,聊起不同学校不同的教学方法。他对我的资料功夫曾表示过赞扬。事后我想,他嘴上那样说,心里会不会觉得我们只是死读书呢。图书馆当然要泡,资料也是越多越好,但是看太多了,也可能贪多嚼不烂。
我举的这两个例子,无非是想说明动笔写作的重要性。中文系里不主张多写的传统,显然是不对的,这种传统必须改变。事实上,写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方法,很多问题都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才逐渐弄明白的。
在今天的开场白中,我唠叨了半天,其实就是想强调动笔的重要性。动笔去写,才是最重要的,比什么都重要。我在许多大学做过讲座,在要求同学们多写这方面,我是始终如一的。
接下来,我想讲讲创意写作这门课,讲讲我对创意写作这门课的看法。
创意写作这个词让我想起了“美文”,想起了“美食家”和“书法家”。这个世界上有些词本来是没有的,但大家都这么说,都这么叫,也就成立了。
坦白地说,我不太喜欢“创意写作”这几个字。写作,老老实实地叫写作多好,加上“创意”两个字,好像就加上了高大上的包装一样。这和美文的“美”一样,从一开始就是多余的。各位应该知道,美文的“文”字,本来就有美的意思。所谓文质彬彬,文和质是相对的,文就是美,就是漂亮。
后来出现了美文这个词,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文”已经不美了吗?因为不美,就要给它再美化一下,实质是多此一举,是画蛇添足。
说白了,我们要上的这个课,就是大家一起谈谈写作这件事。写作,无非是想怎么写,能怎么写,应该怎么写。“创意”两个字多少有点装神弄鬼,可有可无。我们的这个写作课,只是谈谈如何写小说,谈谈如何写散文,如何遣词造句,最后的目的,就是提高大家的写作能力。我并不指望在座有多少同学能够成为作家,这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上了这堂写作课,经过写作训练,写作水平进步了。起码在谈恋爱时,大家写情书的能力提高了,跟人吵架时,怼人的水平也提高了。
我们都知道,创意写作课程确实培养出过作家。伴随着教育的普及,未来的作家,如果没有意外,很多都应该上过创意写作课。国外有很多优秀的作家,是有创意写作学位的。譬如美国的卡佛,英国的麦克尤恩,还有既可以算是日本人,也可以说是英国人的石黑一雄,他们通过大学创意写作课的培养,在文学方面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时至今日,写作的大环境,显然已经改变。如今很多优秀的作家,都跑到大学里去了。这种例子太多,我可以说出国内一大串作家的名字。光是一个北京师范大学,就集中了好多优秀作家。莫言在那里,余华在那里,苏童在那里,还有欧阳江河和西川两位诗人也在那里。要知道,他们都不是简简单单的挂名教授,而是学校正儿八经的老师,都在带学习写作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未来的作家从大学的创意写作课中走出来的现象,将会变得非常普遍。如果海明威和福克纳还在,让他们重新活一遍,我想他们也很可能会走进创意写作的课堂。他们可以是学生,也可以是老师,这是时代的趋势决定的。
就像我们使用的写作工具一样,古人用毛笔,后来大家开始用钢笔和圆珠笔,现在绝大多数人都用电脑。以后的作家是不是都用AI了,我不知道。起码我是不会的,我已经赶不上这个时代的步伐了。一句话,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热爱写作的人,他们的内心深藏着写作的欲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生阶段,这种欲望会被安放在不同的地方。
以20世纪80年代为例,当时,有一大批热爱写作的文学青年,他们都希望可以去当文学编辑。那时,在各个文学报刊的编辑部里,聚集了一大批想当作家的年轻人。他们隐藏在那里,悄悄写作,做着美妙的文学梦,以退为进,伺机而动。在这些年轻人中,有王安忆,有池莉,有余华和苏童,还有迟子建、刘恒、刘震云,以及我本人。后来大家都告别了编辑队伍,成为作家。
这种文学现象,必定会在现在学习创意写作的学生中重现。事实上,国外已经是这样了,新一代的作家正从学习创意写作的学生中涌现。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很多重要的作家,无论中国外国,都是出身创意写作科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意写作方兴未艾,它的前途势不可挡。
迄今为止,全国已经有五百多所大学普及了创意写作课程。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创意写作课像雨后春笋一样,从各个大学里冒出来。不过,多向来不代表重视,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也应该有必要的警惕,要防止创意写作成为烂尾楼。
总之一句话,我既然已经来到这里,走进这个教室,就是在表明自己的态度:写作课是可以教的。不仅可以教,而且可以教好。写作这门学问,是不是科学不好说,但是它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有规律可循,就有道理可讲,就可以拿到课堂上来分享。我作为一名有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结合自己的经历,把自己的写作过程分享给同学们,对大家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我的愿望很简单,希望大家通过上课,通过听讲,能够更喜欢写作,能够在写作上有所进步,有所提高。
就我的课程安排而言,十三堂课中,大约会有八九堂课是谈小说,四五堂课谈散文。希望通过这十三堂课的学习,大家多多少少能提高一些写作能力。
说到底,写作能力还是可以考量,可以训练,可以提高的。我不会教大家怎么去写情书,也不会教大家怎么去怼人和打笔墨官司。但是,正像前面已经说过的,希望通过学习,同学们确确实实提高了写情书的水平,提高了怼人和打笔墨官司的能力。
第二讲:文学之路
同学们好,已经是第二堂课了,时间过得很快。记得上第一堂课时,我曾经说过,自己有些忐忑,怕忘词,怕掌握不好节奏,控制不住时间。陈曦静老师给了我一些提示,让我在第一讲中着重介绍一下自己,说一说我是谁,说说自己的文学之路,先为自己铺个路,打个广告。
没想到说着说着,词虽然没忘,节奏还是没有把握好,广告还没开始打,下课的时间已经到了。因此,今天的课,我必须亡羊补牢,先抓紧时间说一说自己是谁,说一说自己的创作经历,说一说自己的文学之路。
我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写作的。从发表第一篇作品开始算,至今已经过了四十多年,感觉就跟给你们上第一堂课一样,不经意之间,时间说过去就过去了。
每个作家的文学之路都不一样。说起来,就算是同一个作家,叙述起自己的文学之路来,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时间,说的可能都会不一样。每个人成为作家的路径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选择当作家,原因也不太可能一样。
很多年前有一次,王朔、余华、苏童还有莫言,他们共同回答了一个为什么要当作家的问题。王朔说了什么记不清了,余华的回答最机智,也是最著名的。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段子,很容易找到。
余华说,他那时候在当牙医,每天用闪亮的钳子拔掉好多颗牙齿。后来看到张开的黑乎乎的大嘴,看到血淋淋的牙肉,他心里就不太痛快。没活干的时候,他看到几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在大街上逛,就十分好奇地问身边的人,这些家伙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么潇洒。别人告诉他说,这些人是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是写东西的。余华听了,很认真地说,这个活好,我也要干这个工作。于是,余华后来就成了作家,还成了大作家。
莫言的回答也同样机智。他说他当时在部队里当兵,是普通士兵,在这期间,他稀里糊涂地开始了写作。他当时的想法并不高尚,只是为了能够提干和穿皮鞋。他大致的意思就是,只有当上了部队的干部,当上了军官,才能穿皮鞋。
接着轮到苏童回答这个问题。他开始犯难,因为苏童本来准备说自己从小就想当一名作家,因为他从小就热爱文学。因为热爱文学,所以选择了写作,选择了当作家。可在当时的气氛下,面对猎奇的听众,余华和莫言近乎戏谑的回答,效果更好,获得了满堂喝彩,反响十分强烈。苏童的回答,固然也获得了掌声,但是他觉得自己很傻,太一本正经。尽管他也说了真话,很真诚,可这样的回答,在当时的语境下,在当时的气氛中,确实有一点没趣味。
我几乎有着与苏童差不多的经历。有一次在山东,莫言、余华,还有我,三人与当地的文学青年进行座谈。那时候的莫言还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第一个讲。在演讲方面,莫言和余华,都是天才级的人物。他们滔滔不绝,口若悬河,金句频出,非常幽默。
莫言这一次说他是为了吃饺子而当兵,为了提干以后可以继续吃饺子而写作的。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写,写着写着,就成功了。余华还是说他拔牙的事,说他看到那几个游手好闲的文化馆工作人员,傻乎乎地从大街上走过。听众听了,哈哈大笑,乐不可支。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怎么说的,只记得自己开头就说,跟在莫言和余华这两个太会说话的人后面发言,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主持人表示,说什么都可以,随便说。可是我当时的心态,是什么都不想说,觉得说什么都会很无趣。
一个人的文学道路,可能会很有趣。当然,也可能就那样,没什么趣味,一点都不好玩。譬如我自己,就不太知道怎么叙述自己的文学之路。我的文学之路,既不像莫言和余华那样能说出点为什么,有一个看似有趣和明确,其实也不一定完全真实的目的;也不像苏童那样天真烂漫,是单纯因为热爱文学,从小就想当作家。
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考上了大学,进了中文系。如果不是进了中文系,我很可能会是一个与文学毫无关系的人。
我的家里有许多藏书,童年时我最初的记忆,就是自己隔着书橱玻璃窗,辨认书脊上的汉字,我就是这么开始认字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个迟钝的孩子,在未来长大后,会和书橱里的那些书的作者一样,成为一名作家。
我父亲的职业是编剧,除此之外,他还是一名作家。在今天,这个行当还不错,可是当年不一样。我父亲永远都在修改那些不太可能改好的剧本,他的工作就是成天坐在那儿写,没日没夜地写。我父亲并不喜欢他所干的工作,作为一名作家,他并不能做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反而是不想写什么,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写。
我的文学之路是个有点漫长的话题,非要说一说的话,首先,当然还是家庭的影响。事实上,与许多作家从小喜欢写作不一样,我小时候并不喜欢写作。我受到的家教,是长大了以后想干什么都可以,唯一不要干的,就是去当作家。
因此,我绝对谈不上什么从小就热爱文学,从小就想当作家,更谈不上在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文学的种子。什么书香门第,什么家学渊源,统统不存在。我童年的愿望,在今天说出来,同学们可能会觉得可笑——我长大以后想开拖拉机。这个愿望,也许与当时看的宣传画有关。宣传画上的女驾驶员很漂亮,拖拉机一个轮子特别大,一个轮子特别小,看上去很拉风,很酷。
除了想开拖拉机,我也想过要当医生,当外科医生。我的胆子很小,见了血就害怕,就哆嗦,不明白那时候自己为什么想当外科医生。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想不明白。
《红楼梦》的开头,有作者的一首小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们不妨把这首小诗,解释成曹雪芹先生在回答自己为什么要当作家的问题。它简明扼要地说了《红楼梦》这部书的缘起。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当作家,是想解决国民性的问题。他是学医的,可是他觉得医生治不了中国人的很多“病”,因此他想通过自己的笔,来为国家和民族把脉,诊断和治疗“国民性”。
巴金先生说自己之所以要写作,是因为胸中有一团火在燃烧,如果不写出来,他会觉得难受,觉得受不了。
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作家叫高晓声。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与我们家的关系非同一般。那时候,他连续获得了两届国家级的大奖,可以说是当时红得发紫的作家。他的作品都是农村题材的,因此他也被誉为最优秀的农民作家。有一次,他从北京领奖回来,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他,问他为什么要写作,为什么要为农民写作?没想到对着电视镜头,高晓声用家乡方言,很轻松地说了一句,写作嘛,不就是好玩吗?
我记得当时我母亲看了电视很生气,说老高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母亲并不是文学圈子里的人,在她的心目中,文学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高晓声这么回答记者,不是在亵渎神圣的文学吗?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朋友,平时私交很好,高晓声与我父亲可以说是患难之交,我母亲觉得,有机会自己一定要以大嫂的身份好好地说说他。
其实类似的话,作家王朔也说过。王朔也是个非常优秀的作家,他最著名的一段话,也是最遭人非议的话,就是“玩文学”。把文学看得高大上的人,一定接受不了这样的观点,他们会认为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怎么可以玩文学呢?
其实我的心里也挺矛盾的,当作家这个事,不是看你怎么说,关键是看你怎么做。不管怎么说,以上提到的几位作家,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平心而论,他们说的也都是真话。他们的起点可能不同,却殊途同归,都走上了文学的康庄大道,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因此,文学艺术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作品。首先要看作品,其次,还是要看作品。要看懂了作品再说话,要看明白了作品再讨论。不要轻易地因作家说过的一两句话,或一两个故事,就为他的作品下结论。
为什么说如果不上大学,我就不会走上写作之路呢?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上大学前,我做过四年工人,货真价实的工人,而且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钳工。感谢四年的钳工生涯,培养了我很不错的动手能力。不谦虚地说,我曾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蓝领。
在我中学毕业的那个年代,没有大学可以考。后来高考恢复,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高考。第一年没考上,然后接着考。半年以后,我考上了大学,跟你们一样,进入了中文系。我一直说,自己的人生有两件最重要的事,也是最高兴的事,就是考上大学和当了专业作家。
如果不上大学,不读中文系,我想我大约也不会走上文学之路,更不会成为作家。那时候,在做了四年工人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上大学。至于上了大学以后干什么,我没有去想。
我被中文系录取也是非常偶然的事情。后来,负责招生的老师回忆说,当时他负责中文系招生,已经录取完了,就去旁边的历史系看热闹。他在考生材料中看到了我的名字,或者说,他看到了我祖父的名字,就把我挖到中文系去了。如果我去了历史系,成了历史系的学生,很可能就会在历史上大做学问。事实上,我更喜欢历史,如果能让我重新选择,我很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历史系。
我成为作家,首先要感谢时代。我的家庭反对我从文,反对我走文学的道路,没想到我上大学时,正好赶上了文学热。那时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对文学最热情的年代,突然之间,大家都开始写小说了,都想当作家。
我父亲的好朋友作家方之,有个特别的爱好,他不仅自己喜欢写,而且只要有机会,就会千方百计地让别人写。他的两个儿子后来都成为很不错的作家。方之的小儿子是南京很有名的一位诗人兼小说家,叫韩东。如果在座有喜欢新诗的同学,可能会知道他。
方之不仅鼓励自己的儿子从事写作,而且像哄孩子一样诱惑我写小说。有一次,听我说了一个故事,他立刻用很认真的表情看着我,看了半天,鼓励说,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结果我就真的开始尝试把它写下来。那时候流行那种每天翻一张的台历,我开始在台历的背后写这个故事,想到哪就写到哪。方之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老师,不仅热情而且执着,他迫不及待地要看我的小说。我歪歪斜斜地每写完一张,他就急急忙忙地拿去看。他一页一页地看,一边看,一边说,写得好,赶快把它写完。
结果我就真的把这篇小说写完了。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写完以后,犯难的是方之。他觉得这个小说写得还可以,有些才气,可是肯定发表不了。他就跟陆文夫先生商量。陆文夫是著名的小说家,代表作是《美食家》,他跟我父亲也是好朋友。
陆文夫听方之描述完我的小说,皱着眉头说,这种小说,怎么可能发表?
方之是个很优秀的写作者,可惜他英年早逝,四十九岁就离开了人世,并没有留下多少作品。他曾去过我所在的大学给我们讲课,谈如何才能当作家。时隔多年,我只记得当时的他很紧张,反复说他没有上过大学,现在让他到大学的课堂上去讲写作,真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反正小说嘛,就是写,写就行了。
我当时听了,觉得很好笑。我已经记不得他那天具体讲了什么,只记得我坐在教室里,看见一个很熟悉的长辈,而且是自己父亲的好朋友在讲文学,讲他怎么写小说,那感觉很奇妙。那时候,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一天,自己也跑到大学的课堂上来胡说八道。
我说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隔着时间长河,我最初写的这篇叫《凶手》的小说,早已无踪无影,情节也变得非常模糊,我甚至记不清当时我究竟写了什么。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确实是一篇不可能发表的小说,因为完全不合时宜。年代久远,我只记得自己写了一个杀人的故事:一个年轻男人到警察局去自首,向警察讲述他为什么要杀人,怎么把人给杀了。故事里的主人公讲得津津有味,跟真的一样,就好像是创作故事的我亲自杀了人一样。
这显然是一篇非常出格的小说。对那时的我来说,很随意地就写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内心也不知道对不对。盲人骑瞎马,就是一阵冲动,把冲动变成了小说。
因此,如果要向同学们讲述自己写作的实战经验,我觉得写才是最重要的,写才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无所谓你写什么,也无所谓你怎么写,直接开始写才是最重要的。
同学们如果想在创意写作的课堂上得到一些启迪,得到一些在写作道路上的帮助,我的这句话,或许可以送给你们当作金句:不要犹豫,立刻开始写,随便你写什么。
除了立刻开始写,如果同学们还希望再能有些好的建议,我的建议就是,最好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找到几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组成一个文学的小团体。有了这样的文学小团体,大家可以在一起交流,互为读者,一起抱团取暖。
或许一开始,我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写的小说,可能会与文坛格格不入,注定发表不了。发表不了怎么办呢?那就自己组织起来,找几个同好,大家在一起编刊物。
当时,我们一起玩的几个年轻人,有喜欢画画的,有喜欢写作的,大家凑在一起,办了一个民间刊物。我们的刊物叫《人间》,为什么会起这两个字,我忘了,当时也没太想明白,反正就叫《人间》。我们自己刻钢板,自己用油印机印刷。我们写的那些玩意,官方的刊物发表不了,就发表在自办的刊物上。
那时候的我们,是一群很狂妄的年轻人,目空一切,玩世不恭。当时,我写的小说暂时还发表不了,不过一起玩的同伴中,已经有初入文坛的佼佼者。我们中间有一位,也就是方之的大儿子李潮,他写了一篇小说,名字叫《面对共同的世界》,发表在当时的《青春》杂志上,一炮打响,竟然收到了整整一麻袋的读者来信。
我们中间还有一位,是现今文坛上非常有名的批评家。当时上海有一位青年作家,写了一篇小说《伤痕》,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一时间洛阳纸贵。这位小说家到南京来演讲,与文学青年交流写作经验,我们的这位批评家发言,调侃他说“你那个什么伤痕,无非是小刀子在手臂上轻轻地划了一下,连血管都不一定能割破”。他的意思是说,所谓的伤痕文学都肤浅得很,算不了真正的文学。
我很怀念那一段青春岁月,年轻真好,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我们的刊物只办了一期,并没有继续办下去。原因之一,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地下刊物属于非法刊物。此外,我们当然也有些自己的问题,大家都太年轻,又都太任性。差不多同一时间,江苏有一个刊物《雨花》,发表了一期“江苏青年作家专号”,我们办民间刊物的这几个人,几乎都在上面发表了小说。这件事,对我们没有继续办民间刊物,多少也有些影响。毕竟,我们的小说在公开的文学刊物上也能发表,既然这样,似乎就没有必要再自办刊物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们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办文学刊物,确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从年龄看,当时我是里面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最稚嫩的一个。我们那些人中间,很多人都很有才华,都比我有才华,可以说是我的老大哥老大姐。可惜,他们大多没有在写作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半途而废了,而我与他们相比,只不过是年复一年地坚持下来,从没有放弃写作。
说来说去,我其实是在跟同学们回忆自己的年轻时代。年轻真好,年轻就好。我当时就跟你们今天的岁数相仿,也是在大学里读书,无忧无虑。接下来,我还会继续跟你们分享我上大学时的故事。这些故事在我的文学之路上,都是值得一提的话题。
我差不多是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写作的,因为啥也不懂,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写就写了,跟玩似的。在一开始,写作对我来说,是非常轻松的事。无知者无畏,写作有什么难的,不就是用笔往纸上写吗?那时候,我主要是利用假期写作,假期一到,便疯狂地大写特写。
我曾经在一个暑假里,一鼓作气完成了八篇短篇小说。也曾在一天之内,写了两篇小说。有一次,我上午写完一篇小说,我父亲看了,觉得不错,就是字迹太潦草,且写在了废弃的稿纸背面,就决定帮我重新抄一遍。结果他抄完了这篇小说,我的另一篇小说也写完了。
然后,我突然就交上了好运。当时南京有两家很有影响的文学杂志《青春》和《雨花》,在那一年的10月分别发表了我的两篇作品。《青春》发表的那篇短篇小说,就是我暑假的那天下午写的。那一期刊物是“处女作专号”,要求发表者必须是从未发表过作品的新人,我当然符合条件。而那天上午我写的那篇小说,也发表在《雨花》的“江苏青年作家专号”上,我顶着江苏青年的头衔,仍然是符合条件的。
好运气说来就来,那个暑假里我写的八篇小说,居然一口气发表了五篇,除了这两篇,其他三篇也发表在外省的文学刊物上。如今回想起来,我当作家好像很容易。不过,今天与大家回忆这段历史,绝不是要卖弄自己的好运气。事实上,我能够成为作家,不是因为一开始过于顺利,而是接下来的特别不顺利。
运气这玩意有时候真是说不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我依然是努力写作,疯狂写作,势不可当,可是突然就没有办法再发表作品了。整整五年,我写了长篇、中篇、短篇小说,然而却一篇也没能发表。没完没了地退稿,让我从趾高气扬变得灰头土脸。光是一个《青春》杂志,就退了我十多篇小说。我有两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和我一起创办民间刊物的铁哥们,他俩在《青春》编辑部做编辑。可人真倒霉了,有兄弟也帮不上忙,送去多少篇都是退稿。
那五年是我开始写作以来最沮丧的岁月,很多稿子被冷漠地盖了一个公章就退回来了,有些稿子甚至都没有了。我是个没有收藏习惯的人,有时候我想,如果那时候,我把这些退稿信都保留下来,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有些退稿信很长,是年轻编辑写的,表达了自己的无奈,说小说不错,强调是领导不喜欢才退稿的。那是一个文学特别热的时代,投稿都是免费的,只要写上编辑部的地址就行。
那时,我手上大约有三十万字小说,我觉得很充实,因为可以一下子寄出去十篇小说,分布东西南北各个方向,东方不亮西方亮,总会有一篇小说交上好运。然而事实却是,当你运气很糟糕的时候,那些寄出去的小说,最后都会像放飞的鸽子一样,一只接一只地又飞了回来。
曾经,我有一篇稿子在一家编辑部放了整整一年,我感觉很有发表的希望,一直关心着报纸上的预告,希望有一天突然看到它发表。整整一年,我都是抱着这样的期望在等待。然而一年多以后,稿子被退了回来,伴随它的,是一封生硬的退稿信。
差不多有五年时间,我都在这种退稿的伴随下坚持写作。我在心里骂过娘,沮丧过,但是总算坚持下来了。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是觉得最后自己一定会成功,而是因为不断地写,让我渐渐喜欢上了写作。我喜欢这种能够不断写下去的生活状态,每天能够写一些,这种日子让人感到非常满足。
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会有这样的经历,在他们心目中,这家伙不过是个文二代文三代,是一个有背景的人。直到现在,网上偶尔还会有这样的文字,认为我是依靠家庭背景才混出来的,认为我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
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说了。总之一句话,因为五年退稿,我的文学之路,终于走通了。
责任编辑""""许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