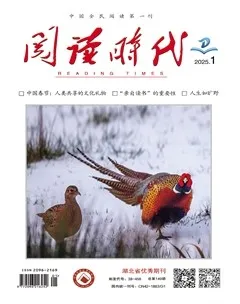怀念我的“老爸”黄永玉叔叔
黄永玉先生留给我们的,不只有他的著作、书画,还有他那赤诚的喜悦、天真的希望,以及不屈从的倔强。
一
我自小与黄叔叔一家就住在同一个院子,从帅府园的美院宿舍到北京站的罐儿胡同8号,再到顺义的东方太阳城。
黄叔叔在我眼里是一个和蔼、幽默、风趣和非常自律的人。
记得小时候在中央美院操场的高低杠玩耍时,黄叔叔提醒我小心,但我不慎摔下,左小臂骨折。他背着我跑到协和医院急诊,最终我胳膊打上了石膏。后来他跟我说当时他不认识路,是我在他的背上一直给他指路才顺利地到了急诊室。
父母早逝后,我想做手术,但经济困难。但黄叔叔得知后,给了我现金,并告诉我有事可以直接找他,他的眼神温暖如父,我感动落泪。
二
搬到东方太阳城后,黄叔叔常找我帮忙处理黑妮解决不了的事,如电视问题或购买颜料,他总信任我能帮上忙。
“黄叔叔你像一台永动机”,这是我对他说的。每每到他的家里都是看他在工作,不是画画就是写文章,好像没有停止过。
他的画,像是个谜,在我的认知里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在万和堂,我见黄叔叔画《春江花月夜》,波纹错综复杂却井然有序。我好奇他如何画出这样的波纹,他笑着说:“心静则波澜不惊,从容不迫。”
我还喜欢看他画白描中的直线,不用尺子,笔直的一条线一气呵成。

90多岁的黄叔叔眼睛不花,手不抖,他每次写特别小的字让我看时,我都会说:“等等,我得去拿眼镜,不然我看不见。”他放下笔,笑了,他一定是在想:“哈哈,小绿子你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呢。”
有一天晚上黑妮给我打电话说:“小绿,你快来,我爸找你。”什么事这么急?我赶过去了,原来他是要给我剪剪影。他让我坐下并调整我的姿势,告诉我不要动,开始了。一把剪刀,一张黑色的卡纸,他的手一点都不抖,卡纸在剪刀下游走着,他只是时不时地抬头看看我,手上的动作是那么流畅。他一边剪一边告诉我们,当年他就是凭着这个手艺,一把剪刀、一个小凳子,在街上为路人剪影求生的。没多长时间我的剪影剪好了,他拿起来看了又看:“哇,怎么像何溶(我的父亲)!”黑妮也说:“像何叔叔!”
提起我的父亲,黄叔叔经常会说:“小绿子,你的爸爸走得太早了,如果他还在该多好,我们一定是很好很好的伙伴,我们一定有好多共同的话题可以聊,还可以一起作画,太可惜了。”
有时候,黄叔叔也是一个固执的老头。他年纪大后身体出现不适,黑妮非常担心,劝他去医院看病,但经常会被他拒绝。他非常乐观地看待自己的身体,总是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可还是发生了意外。有一次他摔了一跤,把腿摔坏了,在常人看来老人家是不好恢复的,可黄叔叔特别有毅力,待到可以下地活动后,他就使用助步器,自己慢慢地练习行走,竟然恢复到自己可以正常行走了。在他骨子里,没有什么是可以难倒他的。
三
黄叔叔尽管是一个看淡生死的人,但还是会有不舍。
一次,黑妮给我打电话说:“老爸不舒服了,要去住院,你赶紧过来。”我赶过去,他正在换衣服,看我进来就伸出了手,我赶紧走过去把手递给他。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眼睛就一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不舍。我的眼泪就要涌出来了,但是我不敢让他看见。这时他跟我说:“绿子,我不舒服了,要去住院了,我不知道……”说到这儿他停下了,后面的话没说出来,我想他可能是要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吧。他把我的手握得那么紧,那个眼神让我至今都不能忘记。后来我跟黑妮说了这件事,她说老爸不愿意让她看见他这样吧,觉得给女儿添麻烦,不想女儿为他担心。
我最后一次见到黄叔叔是在2023年的4月16日,那天是他女儿黑妮的生日,约了一众朋友在太阳城的会所吃饭。那时的他身体有些虚弱,但是兴致很好,席间还在给我们讲笑话,告诉我们他在筹备百岁画展,邀请我们到时去看他的新作。
后来,我的眼睛出了问题,在协和医院住院,5月24日黑妮给我发来消息:“老爸不太好,住院了。”我的心里一紧,这次他是不是会像以往那样好起来呢?可黑妮跟我说他知道我就在他的对面住院,还让她转话给我:“愿小绿子一切顺利!”我住的病房和黄叔叔住的病房之间相隔了一条马路,我和黑妮可以隔窗相望,约好时间在窗口相对挥手,虽然我看不太清楚她,但是知道他们都在,希望黄叔叔好起来。那段日子我和黑妮每天都会互通消息,她告诉我老爸情况,我告诉她我眼睛的治疗情况。我每天下午会在楼道的窗口等她,等她去探望老爸路过这里时相互挥挥手。可忽然有一天没有了她的消息,再收到的信息竟然是:“小绿不要哭,哭坏了眼睛,老爸可就不愿意了。”
他走了……在这世上除了我自己的爸爸,他是唯一一个我还可以叫声“老爸”的人,他待我就像是自己的孩子,对我无比关爱。现在,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我这样称呼了。
“小绿子”,他叫我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呢,爱他!
(源自“夜光杯”,朵朵荐稿)
责编(见习):徐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