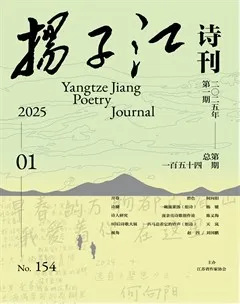“平原诗学”的实践者
妈妈,月光下喊你一声
老屋的瓦就落地一片
——庞余亮:《报母亲大人书》
近年来,庞余亮的散文、小说和儿童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住了他诗歌的光芒。其实,跟很多作家一样,在漫长的文学的隧道里,庞余亮首先点亮的,是诗歌这盏灯,诗歌应该是他文学生涯的一个确切的起点。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很多作家在小说、散文等诗歌之外的文体上成就了自己,但是,如果没有他们文学生涯早期的诗歌创作对他们想象力的启发,如果没有诗歌对他们文字敏锐性最初的锤炼,那么,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后来能在其他文体上有相应呈现。现在我们由《半个父亲在疼》《小先生》《小虫子》等散文作品回溯庞余亮的诗歌创作,无疑也是对一个作家在多个文体之间的栖居状态的一种考察。
近期出版的诗集《五种疲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是庞余亮三十多年间诗歌创作的一次最集中的呈现;该集收入的200多首诗歌,也是他所创作的约1000首诗歌作品的萃选。透过庞余亮的诗歌及它们与其散文之间的互文关系,可以看出他“以诗为经,以文为纬”的文学轨迹。他的诗是苏北平原生活的一种文化记忆,特别是对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苏北平原生活的诗性定格。同时,作为一位善于观察生活,善于从细微之处发现“大义”的作家,庞余亮善于从日常之中发现诗美,提炼哲理,并升华为他对当代生活的独特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庞余亮的诗歌是植根于现实的,尤其是植根于平原的。从诗学的维度考察,庞余亮的诗歌体现出的是一种朴素且幽深的“平原诗学”,他的全部创作体现出十分显著的“平原性”。他不作“为诗而诗”的诗学实验,他所强调的是诗歌表现现实的“效度”。庞余亮有着极强的视角意识,他善于在常人认为没有诗意的地方发掘诗美,或者,他总能从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呈现生活中常人不会感知到的方面,并由此彰显他诗歌的智性和哲性。
一、乡村:心灵平原上的“痛点”
乡村是庞余亮诗歌的“出生地”。作为父母的第十个孩子,他从生活获得的最初的奖赏是孤独和饥饿,还有如今的孩子所没有的“野蛮生长”。所以,庞余亮的很多诗歌像他的散文作品一样,是独特年代、独特地域、独特个人经历与感受的文化记忆。如果说《小先生》《半个父亲在疼》是庞余亮的乡村记忆在散文上的展开,《五种疲倦》中的许多诗篇则是这种记忆所凸显出的情感纹理与诗美浮雕。
庞余亮笔下的乡村处于苏北平原腹地,“平原性”是他全部创作最显著的特色。然而,平原相对于群山和大漠,它往往缺乏震人魂魄的异美。由于平原上的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就是在经济落后的年代,清贫当中也透着几分灵动。在人性上,平原上的子民多性情平和,做事多讲究实用和效果,且千百年来重视“耕读两行”。
庞余亮笔下的乡村书写,往往是从小处着手,动物、河流、器物、农事,是这些作品的切入点。虽然他很少从正面去表现平原,但诗中的意象与叙事的内容,无疑都烙上了区域的印记:“我总是说到麻雀,这些老家/"最卑微的鸟,便如雨点般降临/"它丑陋、瘦小,但会叽叽喳喳/"说得那么快,但我总是听不清楚……我不能说起它们,一说起/"它们就会像雨点般降临/"打湿晾衣绳上的旧衣裳”(《我总是说到麻雀》),①“麻雀”是平原上最常见的鸟类,诗人在这里虽然只是采用一种意象主义式的纯客观的表现,但地域色彩已经在诗行间清晰地显现。虽然乡村留给庞余亮的更多是贫穷和孤单的记忆,但那毕竟是他的来处,他的根;所以,逝去的一切在个人记忆中,既是温暖的火苗,也是心灵的“痛点”。从这个意义上看,《五种疲倦》也是一个平原之子的“心灵史”。诗人心灵中最温柔、最敏感的部分,在他的诗中常常是通过对过去、对“旧时光”的怀念而体现出来的。这首《老地址是安全的》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诗人的这种心态:“老地址是安全的/"那里有埋有父母亲的坟墓/"小学校里的空教室”,可是,他又写道:过去的一切“部分在死去,部分在关闭,部分在撤并”。
隔着时空距离去审视逝去的一切,是庞余亮乡村书写的一个显著特点。他常常把抒情的基点安放在十年、二十年之后;隔着时空距离,心灵上的“痛”才表现得更加深切、剧烈,但从诗学的角度看,它更具有审美价值:
十年前的秋天
母亲还在,从老家过来的秋风
有些酸楚,充满了新稻草的香味
那些从新稻草中穿越过的秋风
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
——《十年前的秋天》
“新稻草的香味”是苏北平原特别是兴化一带独特的气息,但在这里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记忆的符号,它代表着逝去的年代,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一切。毫无疑问,这种文化记忆由于创作主体的态度而呈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并因此赋予被回忆的一切以显著的诗性:“十年前,还是二十年前/"我匆匆穿过那片杂树林/"带动的风/"也带落了一些成熟的浆果/"打在我额头上的/"仿佛是一些湿乎乎的鸟粪/"但是芳香,温柔/"比舌头上的谎言更加甜蜜”(《消失的浆果》),这些诗句的蕴含所指极其丰富。隔着时空的“鸟粪”……呈现出“芬芳”“温柔”的性状,而将之与“舌头上的谎言”进行连类,于是诗人便得出“‘鸟粪’更加甜蜜”的惊人结论,在怀旧的同时,委婉地曲写了时代变迁中人性的异化。此外,我们也注意到,庞余亮特别爱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缓慢地转身》中,“九十年代在缓慢地转身”在诗中间隔反复了三次,每一次反复都隐含着诗人复杂的心态。“入窑的尘土也要安静下来/"我已看不清大风中的老家/"有几只乌鸦,有几只喜鹊/"在一九九六年的春天中乱飞”(《更多的尘土也要安静下来》)——乡村记忆、故园怀念与年代记忆,在这里交织。诗行间虽不著一“痛”,弥漫着的却是不绝的“疼痛”。
对父母亲情的表达,是庞余亮的乡村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在散文中曾写到,他“是平原两棵树的儿子”,这两棵树,“一棵叫槐”“一棵叫苦楝”,而他的母亲是槐,父亲是苦楝。②而在诗中,他更是这样表达:“我有一个致命的短板/"一旦坦露亲情/"必须立刻衰老”(《我有一个致命的短板》)。所以,在他的平原书写中,母亲和父亲是两个钻心的“痛”点:母亲的慈爱、父亲的严苛。当然,也可以说,他笔下的父母的形象,也是苏北平原上千千万万人的缩影:“小桅灯下卸草的父亲、呼呼喝着稀饭的母亲……”(《底层生活日记》)。
在庞余亮的笔下,母亲的形象是慈爱、辛劳、忍耐的化身。庞余亮在诗中刻画了各种场景中的母亲的形象。缄默的母亲、辛酸的母亲、孤独的母亲、头发白了的母亲、领着我们弯腰拾麦的母亲、被父亲打了一顿的母亲、蹲在工厂围墙外捡拾米粒的母亲、居住在乡村墓地中的母亲……母亲成为他乡村记忆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诗中这样写道:“妈妈,月光下喊你一声/"老屋的瓦就落地一片”(《"报母亲大人书》)。而在庞余亮的笔下,父亲则是另一个形象:愤怒的父亲、严峻的父亲、脾气不好的父亲、鼾声如雷的父亲、(因为中风而只有半边身体有知觉的)“半个父亲”……尽管如此,诗人对父亲的描写是他乡村表现中最为生动、真实的一个部分。如果说诗人对母亲的书写突出的是“爱”,对父亲的表现体现的则是“真”,正是通过真实的描写,给读者活化了一个平原上普通而又不一样的父亲形象。“在那个漫长而弯曲的清晨/"是刚刚浇铸好的水泥船/"驮着满船的我们/"送他去殡仪馆火化/"(请他听听哗哗的水声)/"要记住那个塞过很多父亲的大铁抽屉/"(不知他能否躲开烈焰中滚烫的铁)/"砂粒般的骨灰装进小小的木匣/"(木板的导热缓慢而持久)……”在这首题为《永恸之日》的诗中,诗人用类似小说写作中的自然主义的方式,表现与父亲的告别。这比一般意义上的抒情更真实,也更能刺痛人心。
在表现父母亲情的作品中,庞余亮的《在人间》是一首视角十分独特的作品。它通过两个镜像画面——火车车窗玻璃、出租车的反光镜——这一独特的视角,表现对亲人的刻骨怀念:“去湖南的火车上,我从清晨的车窗上/"看见了母亲那张憔悴的脸/"在北京,燕京啤酒之夜/"在出租车的反光镜上/"看见了父亲愤怒的表情/"逝去的亲人总是这样/"猛然扯出我在人间的苦根”(《在人间》)。玻璃窗里的脸、出租车反光镜里的脸,分明是作者自己的脸,但在那一瞬间,仿佛有神灵启示,诗人忽然看到的是母亲的脸和父亲的表情。于是对逝去亲人的追忆以及对蹉跎现实中的自我的反省,两种情绪便在瞬间交织在一起;他人生的四个时间节点上的四个“我”,也在这一瞬间轰然相遇。①
庞余亮的乡村记忆和平原书写一方面是他个人经历的“典型性”的体现,同时也是来自乡村但最终在都市生活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性”的共同记忆。“任何回忆都是作为从当今出发对过去的当今的追溯而完成的。只有所追溯的时代达到了超出个人经历空间以外的程度,这样的追溯才算是回忆。”②庞余亮在《五种疲倦》中的乡村记忆,既是他个人的家族记忆,也是众多的跟他有着相似经历的知识分子的共同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书写“超出了个人经历空间”。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庞余亮的乡村记忆书写体现为散文和诗歌两种文体形式,他的诗集《五种疲倦》和他的散文集《半个父亲在疼》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互文关系。
“秋风还在吹向我的故乡/"我在默默/"为背一捆草回家的妈妈祈祷/"秋风在吹,吹长了她的白发/"请不要,不要吹弯她的腰”(《秋风辞》),这是一个平原之子心灵的颤音,也是众多心灵共同的律动。
二、日常:时间与事物“缝隙”中的诗意
不管是乡村生活,还是城市主题,庞余亮绝少写大场面、大主题;相反,他的作品多从生活场景的瞬间出发,在事物和时间的缝隙中,捕捉稍纵即逝的灵感的火花,并因此演绎出对事物、对人生的哲性思索,且由此创造出具有平原底色的诗性之美。除了亲情书写、乡村记忆是相对集中的主题,庞余亮特别专注于瞬间、细节的描写,擅长在貌似没有关联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或者,赋予常见之物以新的属性,从而创造美学上的张力。在“虚”中见“实”",从“无”中生“有”,这是诗歌独有的魅力,也是想象力赋予诗人的“特权”。
庞余亮总能从最常见的事物和现象中超逸出来,由此及彼,从有限引向无限。比如,这首《草说》:“他们踩着草远去/"一些草被踩得弯下腰去/"一些草也就慢慢地挺起腰来/"默默地看着他们远去/"又有一些人踩了过来/"一些草又被踩得弯下腰去/"一会儿它们还会挺起腰来/"看着那些人走远的背影”。诗中这里所写的场景是大多数人所熟知的,诗人以一种十分平缓的语气,似乎只是对一种表层现象作冷静、客观的描述;然而,“草”在这里却不知不觉地被赋予了人格,它“被踩得弯下腰去”“挺起腰来”“又被踩得弯下腰去”“还会挺起腰来”;诗人在这里既是在写草,又不仅仅是写草;至于草在最后“看着那些人走远的背影”,更是从“无”中生出了最有意味的“有”。可以说,这首只有数行的短诗,包含了人生的无穷哲理。它让我们想起艾青《礁石》中的诗句:“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只不过,庞余亮的这首诗在表现上显得更加含而不露。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庞余亮的诗歌时常显露出“玄学派”诗人的一些特点,即善于从身边事物生发开去,由“微”见“大”,由“特殊”上升为“普遍”。同时,他的整个诗歌创作中,始终隐含着一个抒情主体的形象,他是一个孤独者,也是一个观察者和沉思者,更是一个探寻者。这个形象在他的诗歌中,又常常是一个言说者,以“我”的身份,以一种先知的视角,对“你”“你们”“他”“他们”言说着世间的种种情形,以及“我”所持有的人生姿态。“你要知道,愈高的枝头/"愈是摇晃不已,比如中年的胃总是/"在疼,但并不出声/"紧紧咬住自己的嘴唇……还有孩子,在枝头上摇晃不已/"风在吹!风吹个不停!/"对待生活,对待贫穷和幸福/"我们都应该把眼睛闭上”(《"愈高的枝头愈是摇晃不已》),在这些诗行中,从小说叙事学的角度看,包含着一个全知全能的“我”:这个“我”处于人生的制高点,向众生讲述着他的人生感悟。“你要知道”中的“你”,从语言学上讲,不是一个实指,而“我们都应该”中的“我们”同样是一种泛指。但这不只是语言学上代词表达功能的问题,它体现了庞余亮作为一个冥想诗人的语体风格。
庞余亮的诗歌的这种冥想性,应该是他在长期孤寂的写作状态中所形成。在人生的孤寂状态中,诗人对外物的敏感性会越磨越锐利,常人视而不见的事物也会成为他们诗歌的“种子”。比如,我们身体里的骨头,当我们健康正常时,我们便不会感到它们的存在,就像我们通常意识不到空气的存在那样。然而,在冥想状态中,庞余亮“尖锐地”觉得骨头的存在,并能感知到不同的骨头有如不同的乐器,奏鸣在我们的体内:
我听见了骨头,206块骨头/"在我身体里沉闷的合奏//"我听见了肋骨的手风琴穿过了我的胸膛/"我听见了指骨的笙抚摸了我的双手/"我听见了髋骨与脊柱的吉他指挥着我的步伐/"我还听见肱骨的笛声/"穿越我的隧道和铁轨,一直抵达/"我的头颅里和耳骨边
——《我听见了骨头》
骨头虽然是有形的,但只有通过心灵的内视,才会发现并建立它们与乐器之间的这种关系。“肋骨的手风琴”“髋骨与脊柱的吉他”“肱骨的笛声”,在给事物这些名称的同时,也赋予了它们以新的生命,并让寻常之物陌生起来,诗歌的兴味也由此生出。
从日常出发通向诗性表达,除了要发现常人不能发现的一切,还要在常人虽已看到却未能表达的事物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书写方式。下面这首诗中所包含的生活场景,凡是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都有,但庞余亮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书写角度:
结在高处的柿子/在风中晃荡着/"是不是在嘲笑摘柿人的个子//"这个问题已无法考证//"反正柿子是红的/"竹竿是愤怒的//"受伤的枝条/"白生生的,像必要的修辞//"哦,修辞,修辞/"修辞就是/"掉在地上的柿子/"吐出了厌恶的舌头
——《结在高处的柿子》
在这里,诗人“移情”于表现对象,让柿子、竹竿作为主体来审视摘柿子的人。于是,柿子会“嘲笑”,竹竿会“愤怒”,枝条会“受伤”;而“修辞”的参与,是一种反讽,也是一种幽默。乡村常见的生活场景,经过这番书写后便成为一个不可复制的诗性定格。
这种对事物的创造性的重新“发现”,源自诗人对生活深入、细致的体察。这是庞余亮诗歌的特点,同时也是他散文的一个显著特色。他诗中的很多生活场景都是来自“旧时光”,所以,当他将那些童年时期的场景和意象嵌入他的作品时,也是一种文化记忆的唤醒。“当诗人回到曾经的故乡,故乡发生的变化让诗人的记忆机能受到强烈的刺激,于是发出剧烈的怀旧和惋惜之情,同时激起漂泊者的强烈共鸣。”①比如,在《荒凉图》中,诗人对馒头的记忆以及对这种记忆的延伸性演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由村庄到麦地再到馒头的正向联想,以及由馒头到面粉到麦子到割麦老人的逆向联想,勾画了一幅以馒头为中心词的乡村图。在诗的末尾处,则由馒头回归田野:“一个弯腰割麦的瘦老人/"和来自安徽的收割机主/nbsp;并坐在田埂上/"咳嗽声此起彼伏/"既像是在咳嗽接力/"像是和沉默的田野拔河”,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生动的夏收图。而全诗的最后一句“此刻,世界就是一枚破铜钱”,通过“破铜钱”这一惊人的意象,为这首《荒凉图》画上了最后一笔。
庞余亮诗歌的这种日常性和及物性,也从一个方面折射出“平原诗学”的“物性特征”。平原的四季,“旧时代”的劳作,以及如“老韭菜”“铝钥匙”“‘永固’牌铁锁”“榆树”“榆钱”等时代性、地域性标签,都间接地表明,他是苏北平原上的一个歌者。
三、诗学:有节制的现代主义
庞余亮走上诗坛的年代,正是中国新诗五四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期。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诗歌狂潮中,庞余亮达到他诗歌创作的高峰期。他像一个圣徒一样,为诗歌献出一切,“我既是狱卒,又是死囚/"我唯一的罪行就是写诗”(《所谓诗人》)。他背负着诗歌之重,行走在平原腹地的旷野上。在那寂寞、清贫而又精神崇高的年代,他相信雪莱所说的“诗人是世界未公认的立法者”①;所以,在他看来,尽管平原上万物生长,但是“不读诗的人,连那些不规则的树枝的影子/"也得不到”(《投影》)。
在诗学追求上,庞余亮的诗歌风格总体上讲是“现代的”,但他绝不是现代主义诗学的狂热追求者,更不属于先锋派的实验主义者,虽然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尝试着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应该说,庞余亮的诗学追求在继承五四传统的同时是根植于20世纪80年代主流诗学的土壤中的。他既吸收了“朦胧派”一系的“英雄”诗学,同时,“第三代”诗人的解构性在他的诗中也有着显著的印迹。换言之,庞余亮的总体诗风呈现出“现实性”与“现代性”并存的情况。所以,在他的诗中,真实与想象兼备,纪实与虚构并置,写真与变形共存,从而形成了他特有的总体风格,即有节制的现代主义和实用的现代主义。也就是说,他的创新是以表达为中心的创新,而不是沉迷于形式的实验。于是,口语化的表达与致密的意象组合、强烈的陌生化与有节制的幽默感、巧妙的设计感与如水的铺陈,有机地交融于一体。
陌生化原则是现代诗学的基本属性,只是在不同的诗人那里,实现陌生化的方式各有不同。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说,陌生化就是要打破惯性思维,就是要在诗行间制造“诧异”,而这种诧异性往往是通过意象的奇崛性来实现的,而意象的选择则受到诗人生活经历与环境以及他的教育和阅读背景的影响。然而,不少诗人在追求陌生化时,常常会“为陌生而陌生”,最终造成的是语言上的“消化不良”。庞余亮在追求意象的新颖性的同时,十分注重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妥帖性,努力实现“有意味的陌生化”“就地取材的陌生化”。“铁轨是蘸满扬子江水的/"两根鹤骨笛”(《必须有一副热心肠》),在表现主体“铁轨”时,长江被巧妙地衬托出来了;因为“鹤骨笛”是有声的,所以涛涛的江水声便被暗含进了诗行。随着时代的变迁,老地图上的很多水体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已经变异。于是,诗人便把这些老地图上的水体比作“失宠的蓝黑墨水瓶”,这是一个具有时代特点的意象。于是,他接着写道:“还是用蓝墨水瓶做一盏小油灯吧//"它怀旧的关节炎/"等于思乡的芬必得/"等于气喘吁吁的虚胖/"等于它的心脏病”(《旧地图的顽症》)。在这里,他巧妙地将“关节炎”“芬必得”等医药术语嵌入,含而不露地写出了时代变迁中的病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庞余亮十分注重意象与意象派生技巧的运用,以及意象与直陈式表达的有机结合。比如,在《活着并倾听——》中,他把落叶比作男人和女人:“活着并倾听——/"阔叶林的落叶就像男人坠地/"细叶林的落叶就像女人坠地”,“阔叶”为“男”,“细叶”为“女”,在形似方面体现了意象营造的妥帖性。而接下来的“整整一夜,无数个男人和女人/"不停地坠地”,则是前面落叶的意象派生,诗人不写叶子落下,而写男人和女人“坠地”,在“偷换概念”之后,诗句的趣味性便立刻显现。这首诗的结尾处的“一场生活结束了/"必须用死来纪念”,是一种直陈式表达,它与上述的意象之间形成了映照关系,是从意象及意象派生中抽取出来的格言式判断。可见,庞余亮是属于那种务实的、清醒的、有节制的、在荒诞中讲究诗行间逻辑理路的现代主义诗人。
陌生化原则的恰当体现,为诗集《五种疲倦》带来许多精彩的诗句:“他疼痛不已/"生下一辆自行车”(《杂技》),是令人诧异的表述;“我爱你,像麻雀一样/"在青草丛中出没/"像逗号一样,在诗歌中出没”(《耕耘之疼》),这是带着平原气息的陌生化;“修辞的水藻/"象征的乌贼,还有破折号的带鱼——”(《章鱼的御敌术》),充分体现了虽然“太阳下面无新鲜事”,但事物之间的重新组合则会生出无穷的“新鲜”;“在失火的麦地面前/"你必须要/"掷出/"一把生锈的镰刀”(《苦月亮,白眼狼》),这是天才性的诗句,类似中国画的大写意:不是“抡起”,也不是“挥动”,而是“掷出”,符合“失火”的情势,而“生锈”二字是有特别考量的,它隐藏着很多时代的符码。
庞余亮虽然没有声称自己是个文学上的什么“主义者”,也很少谈论他的诗学主张,但从他近三十年来的作品看,他是一个诗艺的探索者、沉思者、淬炼者。应该说,庞余亮并不为某种主义所动,他在诗学上的追求跟他全部的文学创作一样,在务实地吸收前人理论与技法的同时,追求的是自我的价值判断,追求的是“我”所认为合宜的美学原则。比如,他在《就像你不认识的王二……》《聋子说》《不一定是头疼》《间隙》等作品十分追求某种“设计感”,通过整一的、明快的形式,去表现事物或生活中普遍的、复杂的本质。在这种“设计”中,他把民歌中的间隔反复巧妙地运用到诗行的排列、组合中:
我刚打了一个盹/米饭未熟,我带着我醒来——/"一堆篝火年纪轻轻//"我刚打了一个盹/"米饭已熟,我带着我醒来——/"面前是一堆黑色的灰烬//"我刚打了一个盹/"米饭已凉,我带着我醒来——/"米饭里爬满了黑字的蚂蚁//"我刚打了一个盹/"米饭所剩无已,我带着我醒来——/"已被谁搬到了空碗中
——《间隙》
这首诗从形式上看是“简单的”,但它又可以“装下”多种寓意。可以说,它是一首关于苏北平原上世纪90年代记忆的一首诗,也可以说,它是一首关于时间的相对性的诗,还可以说,它所言说的是“存在”与“时间”的关系问题。“我带着我醒来”,这可以是同一个“我”,也可以是两个不同的“我”;而“我”被“搬到了空碗”中,则透出极其强烈的超现实的荒诞感,以及某种令人不安的神秘感。而下面这首《聋子说》,全诗同样是四节,“设计”的理路同上,但其视角却又不同:
我看见的人群寂静/"他们挥舞着手,张合着嘴巴,像一条条鱼。//我看见的人群寂静/他们聚集,他们分开,他们奔走,像一棵棵树。//"我看见的人群寂静/"他们吃饭,他们流泪,像一个个哑巴。//"我看见的人群寂静/"他们追赶他们,他们殴打他们,他们生下他们,像一只只老鼠。//"我看见的人群寂静/"我杀死他们,他们躺下,我也躺下,一片寂静。
——《聋子说》
这首诗借助于“聋子”的视角看喧嚣的世界,为我们呈现出一个陌生的、令人惊讶的现实。从“聋子”的视角看世界,世界一片寂静;寂静后的世界,人群的动作自然就显得突兀、夸张、荒诞;在这个寂静的世界里,人群成了寂静的影子,如无声电影——常人视角不便言说的一切,诗人在这里全部交给了“聋子”。朱光潜在谈到“实质”与“形式”、“形式”与“表现”时说过:“所谓表现就是把在内的‘现’出‘表’面来,成为形状可以使人看见。”①而庞余亮诗中的这种独特的设计,就是一种“形”,通过它将某种看不见的“质”表现出来。
诗歌的语言方式,就是一个诗人的符号标签,也是一个诗人的全部个人经历与全部内在素养的综合体现。优秀诗人的语言是不可复制也是难以模仿的,因为每个成熟诗人的语言中都包含着他的“秘符”。庞余亮的诗歌语言是多姿的,是根据他所抒写的主题而不断变化的。他的语言体现了一个平原诗人特有的灵性。在具体的呈现上,他的语言虽然未必险峻、奇崛,但强调妥帖、机智,所谓“是有真迹,如不可知”(钟嵘《诗品》)。比如,他的诗中多处嵌入语言学术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表现效果。“黑狗在奔跑,它被打狗队打断了一条腿/"像一个不规则动词/"在雪地上奔跑”(《真相》),“动词”的属性,“不规则”的限定性,把一条雪地上瘸腿的狗写得栩栩如生;“有多少生存,就有多少死亡/"就像有多少实词/"就得用多少虚词/"从我们的嘴唇边长出来”(《捕蛙人》),“生存”与“实词”的对位,“死亡”与“虚词”的连类,真正体现了优秀诗歌就是一种“发明”的诗学基本法则;“如果词语能够控告修辞/如果水果店那只关了一夜的狸猫/"能够控告那些水果们”(《芳香也是罪过》),这种无法求证的因果关系,无疑在诗行间增添了非理性的迷人色彩。此外,庞余亮在追求风格化的语言时,强调情与景的交融,强调意象与叙事场景的贴合性。“天井里晃来晃去的的晾衣绳啊/"请告诉我这一切的真实性”(《往日》),这样的诗句,与其说是奇崛得让人惊奇,不如说是妥帖得让人惊讶。
此外,庞余亮是诗人,也是散文家和小说家,小说的笔法在他的诗中得到了恰当的体现。他的很多诗作,具备很强的情节性、现场感,并在叙述上显示出了超强的语感。在下面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小说笔法在诗歌上的运用:
哑巴的推销术
就是手拿一把菜刀
快速地剁着一根钢筋
这是在黄昏,我们目睹下
他剁着一根钢筋,像剁着一根草绳
钢筋的崭新切口
婴儿一样睁开眼睛
深夜里我们不说话
深夜里我们高举着哑巴的菜刀
在人群中乱窜──
——《哑巴的推销术》
诗的前两节从表现方式看,是小说笔法和诗歌艺术的完美融合,既有动作的精准描写,又有诗歌的形象生动。而诗的末段则是上升到一种超现实,借助于荒诞来表现生活的真实。
以上对庞余亮的诗歌创作在本体和艺术上作了一个粗略的勾勒。然而,近年来人们对庞余亮在散文创作上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似乎遮蔽了他诗歌的光芒,但他的诗歌强烈的地域性、时代性特征,以及鲜明的个性化语言,都表明他已经形成了独属于他自己的风格。在平原乡村书写与城市生活表现之间,在先锋与传统之间,在晦涩与清新之间,他一直追求着某种平衡。他的语言经过长期的磨炼,也显示出极高的辨识度。可以说,庞余亮用他独有的诗歌文本丰富了江苏新诗的版图。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
①本文所引用的庞余亮诗歌均出自庞余亮诗集《五种疲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下文不再另注。
②庞余亮:《我是平原两棵树的儿子》,见庞余亮著《半个父亲在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8-109页。
①庞余亮:《四个“我”都在证明》,同上,第3-5页。
②[德国]安格拉·开普勒:《个人回忆的社会形式——(家庭)历史的沟通传承》,见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①鄢冬:《当代诗歌文化记忆的三种图式》,《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①[英国]雪莱:《为诗辩护》,缪灵珠译,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①朱光潜:《诗论》,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