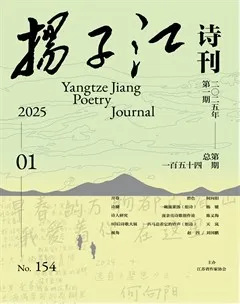火车(组诗)
大雪日
缥缈是雪的灵性,也是你恣意时的眉骨,
你看,你的睫毛也在闪着雪,你
理想的眼里这时有一个辽阔或叫雪野,
而不是围城——我不愿说到围城,
身体里还有不少酒能燃出恣意或醉欲。
那就醉一把——很久了,每个人仅在
露台上辗转,下雪即是要一个飘逸——
听起来虚妄吧?那我就站在虚妄一边。
雪下着,翩然于野性而不拘泥什么,
雪下着,它似乎在倾覆着时间里的不安……
汝瓷小镇
雪后的上午有爽目的清凉,
汝河湿地在冰凌的镜下找天青。
走进汝瓷小镇,
——镇子亦如瓷的色泽。
我想起了手艺。有用或无用的
手艺,绮梦般幻化出时间——
我们看着那些植物石、铝矾土、泥坯,
以至于瓷器——时间就是手中器皿,
就像我们的词,即便虚妄,
也有一个时间的真身,这就够了吧。
河流在朗诵,抑或给时间以血脉,
却不再是秩序、速度、晦暗……
几只白鹭划开水面,一个女人手挽桃枝,
瓷的光泽蔓延出更多的妄想——
我就想,那就站在虚妄的一边,
我就想,有生之年就住在这样的小镇
甚或山涧,荷尔德林的正午也是我们的。
黄栌
越过山的陡峭,葱茏里渺望幽谷,
没有另外路径除了黄栌生出黄栌,
每一个叶片都像是词的派生,
薄羽飘摇自有其飘摇于天地的野性。
为了那一束灵光在风景深处
抑或说在你的身体里有一种嘶鸣。
越过时间的陡峭还会有时间的火焰。
或者因爱的创伤也未可知,在我的
履历里,自个儿给出一个染色,
好让群山或众树之中的我拥有一道
闪电,便不再与平庸达成共识。
这是黄栌在秋天的一个骄傲——
颓荡的世界、生茧的谎言……
让霜天无情地落下来吧,在时间的
慌乱处生火,给自然另一个自然。
诗像一个旅行家给过往装上它的词。
在郑州,寻找贾鲁河
想到舟楫之行。在速度碾压夜色的
晚上,我坐在贾鲁河岸,想到
一条河就是一种历史赋形。
我是多年前的我,也是多年后的我。
——话说得如此肯定,在于挑衅过
我们的桅杆之后,水清澈到照见
月亮的真身;在于我依然拥有我的词,
为了一个远方,或叫时间之鱼……
太多恍然的人,唯有王维《宿郑州》
那句明天将要渡过京水,像是点醒了
情到深处更孤独的人……
还是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多坐一会儿吧。
十几米外是街道、飞驰的车子以及
匆匆的人、夜晚的沸腾与繁华,
这时一条河停在这里,或说穿过我们,
我想,我的词就该给时间一些虚无。
野燕麦,或饮马河往事
饮马河,不再有马,
野燕麦长成它应有的模样。
这因果,用什么来诠释
都不如蹲下来的裙裾——
一时间还原我们的景致。
“经历的过往依然鲜活。”
每一次都要过这一座桥,
一座什么样的桥,通向
梦境抑或永远?我n次
越黑暗而来——我是我的
火炬,你是你铺开的燕麦。
这么多年,一条河几乎
越来越懂得了我们的
呼吸、行为、忽隐忽现的
浪与帆船。野燕麦随着
风的意思摇摆出河的生动
以及相拥的人,暗夜里
隐秘闪烁的辰星。我像梦
一样述说燕麦绵延不息的
波涛,更深的梦境潜着
朱丽叶的泪:尖锐的痛感
来自爱在爱又不在。如水。
葛花,或醒酒论
“因酒已成弱者,禁用。”
酒醒后读草经,惊讶于葛花的
两面性:解酒又怯弱。
我不安于我是不是一个弱者,
酒还在继续进行,三五人或偶尔独饮。
时间在寤寐间有一个沉醉与清醒的真身。
幼时食葛花后三日而味犹在,
今沏之以醒酒实属不得已。
尤其在酒劲儿过后的深夜悠然醒来,
有一种空夜更空的空惘感。
葛花呀,杯子里是它宛在水中央之姿。
寂寞的人长久地沉浸于酒——
酒在欢愉,还是醉眼里的人无可觅?
不羁的风吹过窗台。我在无眠中
给你,多数时候算是给自己写信——
确切地说是写下长长的诗句。
别问我,解我酒毒的人在不在诗中。
明明如月,葛花卓卓。
鸟归林
——在筎园,为王谦而作
黄昏,也即世界的柔情部分。
森子说:鸟归林。
我们在竹园深处干净的夕光下听
无边鸟鸣,一天的不安随着《不安之书》的
合上而变得安宁。我们
不再谈及……一个不再可疑的
时间是醒着的时间。
诗思也即我们的酒器,这时
归于饮,当然也可以理解为隐。
“竹子,是苏东坡的偏爱,
也指定是我们的胸襟。”
说到这里,忍不住碰了一下杯子。
身后画框里的辘轳吱了一声,
河岸的布谷也似叫了一声,
……我们便不再说话,偌大的竹林
以自然的嗓音,在召唤着词。
火车
你不会回到你。
——保罗·策兰
这一列还是另外的一列,带我去哪里?
或始终在一个原点?瞬间的过往,
隐约的面孔,火车过后的空荡、空茫。
我飞驰,我的变形记,我离开的内心,
我像一个盲者。如梦般的缥缈之神……
活着即奔走?我的列车就在眼前,
在我身体里一定有个站点,别告诉我——
火车载着大时代让我不再是我,
我注定要完成一个自我。自我之神,
时间的真身,即是说我的火车驰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