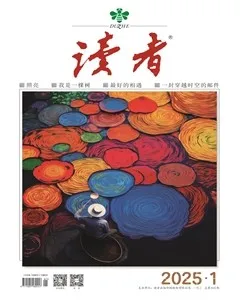女骑手

如果说外卖骑手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么女骑手就是配送行业中“显而易见的不可见”人群。送外卖是一项具有强烈男性气质的工作,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对体力要求高,因此常常被认为是“男人的活”。女骑手由此变成配送行业里的“性别少数”人群。她们穿着略显肥大的工作服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只有走近时,我们才能从长发和头盔下的轮廓中发现她们是女性。
送外卖的女性,不是媒体经常讨论的受过高等教育并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精英中产女性。相反,她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农村、乡镇,日常生活以家务劳动、照料丈夫和孩子、干农活为主。从性别内部的差序格局来看,她们中的很多人属于弱势和边缘人群。作为从农村传统家庭成长和走出来的女性,她们继承了传统的性别分工认知,默认自己应该承担更多的照料工作和家务劳动;在配送行业中,她们是遵守规则的典范,兢兢业业,配合度高。对这样一群女性来说,家庭的责任与重担并没有因为她们加入骑手行列而消失,这意味着她们不得不面临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拉扯,并在这种拉扯之中寻找解决之策。
破碎家庭的阵痛
在我做田野调查时,女性受访者中因为离异、家庭变故、破产等原因不得已外出送外卖的,占到近三成。因为离异而送外卖的女性多是家庭主妇,与丈夫离婚后发现自己没有工作经验,很难找到工作,无奈之下,只好先送外卖以求过渡。
40多岁的雪花就是一个例子。30岁时她在东北老家认识了现任丈夫,家人觉得她年纪大,催她结婚。她受不了催促,与对象认识不到3个月就匆匆领了结婚证。婚后,雪花发现丈夫有家暴倾向。儿子两三岁时,她发现丈夫有了外遇,夫妻俩关系更加冷淡,因为儿子才没有离婚。在过去的几年间,“凑合过”一直是她家庭生活的常态。2020年,儿子上小学六年级。雪花所在的公司倒闭了,她待在家里,与丈夫三天两头吵架。没有收入让她变得忧心忡忡。
2020年秋天,犹豫再三,雪花决定送外卖。周末的时候,把儿子一个人放在家里雪花不放心,既怕他无聊,也怕他管不住自己,一直打游戏。所以她带着儿子一起出来跑“闪送”,戏称是“上阵母子兵”。
有一次,北京天气突变,噼里啪啦地下起了冰雹。小石子一般大的冰疙瘩打在雪花的送餐箱上,砰砰作响。雪花急忙骑着电动车带着孩子跑到一座桥下,挤在一起躲避冰雹。雪花只带了一件雨衣,两个人钻进去取暖。儿子跟雪花说:“妈妈,我太冷了。”雪花低头看见儿子的裤子和鞋子全湿了。于是,雪花带儿子去公共卫生间,用干手器把他的衣服吹干,但两个人的鞋子还是湿的。天气不算冷,雪花索性光着脚骑了半天车。
2021年,儿子上初中,能管住自己了。因为作业多,雪花让他独自在家,周末不再带着他送外卖。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雪花就这样一直送外卖。把孩子安顿好之后,她放下心来,更愿意走出家门。单子多的时候,她会干到半夜甚至凌晨。生活艰难,雪花对于自己无法兼顾孩子和工作还是耿耿于怀。
对家庭主妇来说,家庭破碎是可怕的。失去了经济来源,她们需要面对无法实现经济独立的阵痛,得想办法养活自己,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阵痛不会轻易消失。
小城母职
在女性选择送外卖的诸多原因中,有一类最为大家所熟知,那就是为了照顾孩子和家庭选择做兼职骑手。在我的调查中,这类女骑手占到两成左右。她们不像一些离异妈妈那样干全职,而是奔走于家庭和工作之间,希望靠“打零工”赚取一些零花钱。她们一般选择跑“众包”,因为还需要接孩子上下学、准备晚饭、辅导孩子写作业等。这样的女骑手年龄多在30岁上下,处于育儿任务繁重的阶段。她们的身影一般出现在小城市或者乡镇上,大城市中鲜有。
根据观察,这类女性属于典型的“城乡两栖人”。一方面,她们有一定的教育背景,其中大部分有中专、大专学历,作为年轻一代,她们对于现代化的育儿知识、家庭认知并不排斥,甚至喜欢追随;另一方面,她们又因为“在地化”就业,身处小城或乡镇之中,被沿袭自传统女性角色的诸多期待包围。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当这群女性受到城乡文化的双重影响时,其认知出现了有趣的“文化调试”:一方面,她们变得更加在意自身的母职实践,注重对于孩子的陪伴、辅导等精细化养育;另一方面,她们也十分在意自己作为传统家庭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定位和预期,例如要按时做饭、照顾好家庭,尽到自己的责任。她们的母职实践虽然不属于大城市中精英妈妈们所展现出来的“密集母职”,但也确实受到了这类主流话语的影响和冲击。
芳利是湖南湘阴的一名兼职骑手。她的丈夫在老家经营着一家彩票店,不怎么赚钱。两个人有一个上初中的儿子。为了给孩子攒够以后的学费,芳利从2021年开始送外卖。为了多挣点儿钱,芳利的工作时间与全职骑手的并无两样,每天都在10小时以上。
芳利读过大专,毕业后结婚,很快有了孩子。但生活并没有朝着她期望的方向发展,相反,养育任务和家务劳动繁重,丈夫赌博、开店赔钱都让她无可奈何。芳利同时面临“丧偶式育儿”和干工作的双重压力。孩子与工作成了她心头的两座大山,二者都难以割舍,却又找不到解决办法。芳利到了晚上经常难以入睡。她说:“我也快40岁的人了,干这行并没有给自己带来特别多的收入,也就是能保障基本生活。工作经验没有增加,我也没有时间陪孩子。我干这一行,受影响最大的就是自己的小孩。我想多挣点儿,就不能过周末,必须每天都跑。孩子的作业,我不会很有耐心地去管,只能潦草地看一眼。”
在城镇化不断加速发展的今天,现代与传统同时影响着县城、乡镇里的诸多母亲,履行母职责任的认知一方面变得更加牢不可破,另一方面,母职不断加剧的精细化程度又让诸多女性感到疲惫。其中一个核心原因依旧是家务劳动的不可见性。女性在母职、家务劳动层面的付出无法得到认可,便会出现奔波于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第二轮班”母亲。对小城的女骑手而言,家庭的藩篱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他家庭成员对家务劳动的无视或忽视。
外卖娘子军
在深圳市龙岗区的一个外卖站点里,顾大娟用两年时间组建了一支“外卖娘子军”。这支配送队伍由十几名女骑手组成,并且拥有自己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可以随时随地为女骑手发声。
顾大娟的短视频账号里发布的内容几乎都跟女骑手相关,其中大部分是分享跑单的策略和送单过程。例如,她会根据自己的跑单经验,教新入行的骑手如何看导航、如何抢单、如何与顾客交流等。随着粉丝量和观看次数的增多,这些视频慢慢地被周边的一些女性看到,她们萌生了送外卖的想法。一些女性从周边赶来找她,有的甚至坐火车、长途汽车来到龙岗,表示自己想在此地送外卖。顾大娟都热情地帮助她们。从买电动车、电池,到租房子,再到将她们介绍给站点,带她们送外卖,几乎提供了“一条龙服务”。
随着女骑手在这个站点越聚越多,可拍摄的素材变多了,顾大娟可以更频繁地制作和发布短视频。除了讲述日常的送单生活,顾大娟和姐妹们开始尝试拍摄一些带有表演性质的内容。例如,顾大娟会和大家一起策划出整齐的动作,认真排练、表演,拍好后配上精心挑选的音乐,以此展现女性骑手这一群体的不易和坚强。她们在视频里自称“外卖娘子军”。这些视频的发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进一步鼓励了很多想要尝试当骑手但又有些犹豫的女性。
“外卖娘子军”形塑了超越传统家庭再生产的性别话语。在这个小社群的集体展演中,女性传统的勤劳、顾家、隐忍等性别规范不再被强调。相反,独立自主、敢于挑战、团结一致的女性形象开始出现。正如顾大娟所说,她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她相信“爱拼才会赢”。
身份的桥接
我尝试对女骑手做一个超越其职业劳动本身的定义。这个定义的一端连着劳动,另一端连着家庭。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与女骑手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是一群无法用单一的场景去解释的人。横跨在天平两端的,是无比丰富、细致却又充满张力的性别化阐释与行为。她们并不是被限定在数字劳动框架内的劳动者,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背负着生产与再生产、市场与资本多重结构的性别化个体。
换句话说,女外卖员是具有理性和主体性的个体。她们进入外卖行业有着自己具体的、个人的原因,包括赚取收入、照顾家庭、争取经济独立等。
平台经济的低端数字红利给予了她们一定的机会,女骑手利用这一机会来获取自我收益。平台劳动可以作为其临时性的过渡工作。在这一过渡工作中,零工劳动的市场化正在对家庭领域形成虹吸效应,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市场化生产领域。外卖平台承载了劳动赋权和性别隔离的双重职能。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平台为女性提供了争取平等权益的渠道;作为一种组织管理形态,平台复制了不平等的性别劳动关系。但女骑手并没有被束缚于平台既有的性别规范之中,而是在送餐实践中展现了一种“桥接式”的性别展演。这种展演从家庭再生产领域进入市场生产领域,并最终产出了基于女骑手社群文化和女性独立的性别身份认知。
这些女骑手,牵连着她们的家庭,每个人背后都有具体的情形和生活意义。对女骑手而言,家庭既给予她们温暖和力量,也给予她们悲伤和苦楚。生产和再生产同时压在她们的肩上,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极其复杂。对大多数女骑手来说,家庭和工作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时而需要她们做出选择,时而需要她们全部扛起。
(含 烟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一书,本刊节选,贺志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