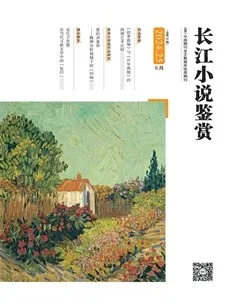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生态美学思想比较研究
[摘要] 陶渊明与华兹华斯是中西诗坛吟咏自然的典范,二者跨越时空和文化的界限,建构出在内涵上惊人相似的生态书写,诗作中均洋溢着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思想,向往乌托邦式的社会生态思想,以及真善美并存的精神生态思想。从生态诗学视角出发,将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生态美学思想进行平行比较研究,挖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关系,为当下身处“工具理性”统治下的人们带来一股思想上的清风,或可消减社会发展带给人的异化现象和心灵矛盾。
[关键词]陶渊明" "华兹华斯" "生态诗学" "自然和谐
[中图分类号] I06" "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25-0125-04
一、引言
我国东晋时期山水田园诗人陶渊明和英国“湖畔派”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歌皆以吟咏自然著称,陶渊明的诗歌生态深受其所处时代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流传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表述。华兹华斯则受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生态文学家卢梭“返归自然”与“追求真我”主张的影响,他久居湖畔,具有超越其时代的生态意识及对自然的伦理关怀。两位诗人都以抒情化的诗句彰显出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崇拜,作品中所蕴含的生态美学思想为当下身处“工具理性”统治下的人们带来一股思想上的清风,也为人们增添了一份应对精神生态危机的勇气。
生态文学是20世纪生态思潮中极其重要的支流,它通过文学来重视人类文化。本文从生态诗学视角出发,根据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中提出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三分法,对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生态美学思想进行平行比较研究,挖掘诗作中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思想,向往乌托邦式的社会生态思想和真善美并存的精神生态思想,促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达到和谐平衡的状态,“让人类告别冷战、战争、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让人性更具有生命的绿色”[1],对于冲破理性的泛化、资本的扩张以及人类主体地位的高扬也具有一定的启发。
二、田园与水仙: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
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古以来即为一种根本性存在,因而鲁枢元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看作一个“元问题”,它会“伴随着其他问题的存在而一直存在,但它的解决也将自然而然地促成其他问题的有效解决”[2]。“天人合一”是生态诗学的一大重要思想元素,强调人类作为生命的存在体,与自然界始终保持着一种生命共同体的关系。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笔下的田园、水仙等自然之物纷纷呈现出人与自然相互适应、和谐统一之感。他们以自然为诗,将自由闲适与物我交融的生生之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中国田园诗歌的创始人,陶渊明在其作品中书写花鸟草木之趣和躬耕田园之乐,用空灵的心境享受归隐后惬意的田园乡村生活。在他的生态意识里,对自由的追求可以说是在寻找一种能容纳自我的外在生存空间,并在此契合大自然的秀丽景象和千变万化。正因为摆脱了羁人的官场和“心为形役”的人生困境,陶渊明归田参加劳动后体会到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并创作了《归园田居》组诗六首。“复得返自然”指向标题中的“归”,作者逃离世俗的樊笼,所归之处不仅仅是自然界,也是个体与天道合二为一的自然状态。“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3]诗歌在描绘耕种生活的同时,也隐含了自然规律,荒草茂盛而豆苗稀少的自然之变是耕种者需要面对的,因而作者选择早出晚归躬耕田园来顺应自然。人与山、人与月、人与身边的一切和谐共存,诗人将其清新自然的心灵净化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美,诗中所蕴含的返璞归真、融入自然的生态思想在冲破陈旧的精神枷锁的同时,赢得了后世的钦佩和效仿。陶渊明以描写田园风光闻名,笔下的自然充满诗情画意,他在诗中所传达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生态思想是“指导陶渊明生活和创作的最高准则”[4]。个体与自然界的互动,当是后人需要不断传承的生态理念。
现代工业文明高速发展的同时,人类与自然界原本的和谐关系也被无情打破,人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自然的对立面。华兹华斯的生态思想最初体现在1802年版《抒情歌谣集》的序言中,他将其诗歌体裁归纳为一种“微贱的田园生活”,“任何来自内心的强烈情感都能在此找到适合的土壤,能够臻于完熟,少受一些约束,表达出更为质朴有力的语言。在这里,人们的热情也恰能与自然的美和永恒的形式融为一体”[5]。诗人不仅以现实主义笔调描绘英伦三岛独特的田园风光,以追忆的方式再现已逝的田园生活画卷,而且还营造了许多山水田园意象,包括落日的光辉、辽阔的碧海、鲜活的空气以及湛蓝的天空等一切自然之物。《丁登寺旁》将孩提到成人历经的时光变化与诗人对自然的崇高敬意完美地糅合在一起,流露出诗人恬然自适的生活态度和对自然的独特感悟。不管肉体是否存在,只有当人的灵魂真正融入自然,才能“永远与岩石,石头和树木朝夕相伴”[6]。在《咏水仙》中,诗人以孤独的流云自喻,“我独自漫游,像山谷上空 / 悠然飘过的一朵云霓,/ 蓦然举目,我望见一丛 / 金黄的水仙,缤纷茂密”[5]。此处,水仙已然超越了植物学意义,是一种灵性的存在。作者托物言志,从言外之意与象外之境中把握住与大自然息息相通的契机;在物我交融的和谐中将心胸升华到崇高的境界。华兹华斯的诸多诗歌表现出天人合一之美,暗示作者孤独迷惘,渴望在自然中找到内心所归。
三、桃花源与割麦女:乌托邦式的社会生态
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同时,生态系统也遭受严重破坏,人类开始构建一种愿景化的理想状态。陶渊明和华兹华斯均非逍遥于世之人,他们深谙社会的黑暗和百姓的疾苦。陶渊明在愤懑之余用桃花源建构出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表达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而华兹华斯塑造了割麦女等简单淳朴的形象来消除资本对人和自然的异化。
陶渊明从小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然而其生活的六朝时期是一个佛学和玄学盛行的时代,社会动荡,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出身庶族的陶渊明遭人轻视。混乱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下,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显露无遗。在陶渊明辞官归田的第三年,诗人所居陋巷的草房“遇火”,全家人只好在门前的船上暂住。虽然诗中所写乃诗人一家的遭遇,但客观上反映了六朝百姓共同遭受的苦难,这种贫困潦倒的生活是当时社会黑暗的一个缩影,百姓的朴素愿望就是社会安定、天下太平。陶渊明遂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采用写实的手法将黑暗的现实和虚构的世外仙境联系起来,通过对桃花源安宁和乐环境的描写,以及对桃林山水阻隔战火的巧妙设计,呈现出自己心中理想的社会,表现出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桃花源记(并诗)》描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和谐社会,呈现出人人平等、人人劳作、人人自足的理想生活模式。“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3]桃花源中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各遂其性的恬静安详之感是陶渊明恬澹自守的再现,政治上没有君权压制,经济上没有剥削压迫,这一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桃花源深度契合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理想之态。
华兹华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历了圈地运动等漫长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进而步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无政府干预的市场自由竞争使得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对劳动人民的压榨到了极限,原本是自然之子的人类成为卢梭鄙夷的“最堕落的动物”,且必须面临机器工业取代手工劳动的威胁,“人们的思维方式变得机械、狭隘、浅显”[7]。在此背景下,诗人华兹华斯内心充斥着对工业革命的厌恶和对上层社会浮华虚幻的憎恨,渴望通过自己的诗歌去恢复那些被资本减损的自然感召力,化解现实社会暗藏的重重危机。他向夜空中的月亮求助,“请让我在自己的想象中 / 追随着你的航迹,/ 天上的光明之船哪,请原谅 / 我以你的榜样对抗”[8],并且塑造了一群过着简单淳朴生活的自然人。《孤独的割麦女》通过角色自传的方式传达出对未受工业文明破坏和大机器生产影响的质朴田园生活的向往。“夜莺也没有更美的歌喉 / 来安慰那些困乏的旅客—— / 当他们找到了栖宿的绿洲,在那阿拉伯大漠; / 在赫布里底——天边的海岛,/ 春光里,听得见杜鹃啼叫,/ 一声声叫破海上的沉静,/ 也不及她的歌这样动情。”[9]诗行中蕴含着冬去春来的和谐乌托邦景象,英格兰西北边疆区域的赫布里底群岛在冬季沉睡,杜鹃嘹亮清澈的叫声将群岛从沉睡中唤醒,原本寂静的海岛又充满勃勃生机。少女的歌是“一支被征服民族之歌”,深刻揭露了“殖民历史的创伤和暴力”[10],反映了苏格兰生态农耕被破坏的社会现实,作者借少女之口表达出对生态灾难的控诉。
四、安贫者与老乞丐:真善美并存的精神生态
精神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彰显出主体内在的、意向的、自由的生命活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生态领域的危机此起彼伏,“精神生态属于地球生态循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的精神因素也属于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变量”[11]。跳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是正确处理人与自我关系的关键一步,当个人将生命与生态融为一体,心理达到平稳状态,便能达到人类自我存在的最高境界。陶渊明安贫乐道、维持真我的超然精神以及华兹华斯化悲苦为审美的慰藉感诠释了生态系统健康“精神圈”的真正内涵。
正值政局动荡不安与思想自由开放相混杂的魏晋时期,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影响深远。陶渊明诗歌中暗含的种种生态意识和生态境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人异化心灵中的绿色期待。诗人既怀有“有志不获骋”的志向,又有着“性本爱山丘”的志趣,生性洒脱的他注定与纷扰的尘世格格不入,常有“误入尘网”和“身居樊笼”的压抑之感。在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之间,陶渊明更看重后者,尽管深受贫苦困扰,诗人始终保持着高尚的品德和高洁的情操。“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3],“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而辞荣”(《感士不遇赋》)[3],“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3]等诗句体现了他安贫乐道、不改本性的铮铮铁骨。诗人始终保持着淡泊名利的心境,将躬耕之苦与收成之衰抛于脑后,摆脱“身在江海,心居魏阙”的矛盾心态,完全寄情山水、追求纯真,化“‘小我’为‘大我’,渴望进入一个超脱的精神境界”[12]。人与自我的生态之美体现在人类身心和谐与真实的生存之态上,遵循本性,掀去生活的伪饰,才能实现诗意的栖居。陶渊明对“真我”的永恒之追,给予深受精神问题困扰的当代人一定的启发。
法国大革命后,受启蒙运动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随着基督教信仰的动摇变得混乱迷茫。诗人华兹华斯以诗歌为载体抒发内心的情感,以此促使精神生活复活重生。他以敏锐的眼光去发现普通人身上的闪光点,并借助诗歌颂扬其高贵品德。农夫、乞丐、猎人、老妪等一批乡村生活的苦难者形象在华兹华斯笔下被赋予特殊的含义,成为在精神迷茫时代中的一股淳朴之风。《坎伯兰的老乞丐》中,老乞丐行走在自然中,并随着诗的推进渐渐从一位有血肉之躯的社会边缘人,获得了与自然的同一性。18世纪90年代,湖区乞讨现象十分普遍,华兹华斯将个体生命的悲凉感融合进诗中,给人“形而上学的慰藉”。诗歌真切地描绘了老乞丐啃食面饼的场景,一种真实的孤独感跃然于纸上,“他坐在大路旁边一个不高的 / 石墩上……独自吃着他的食粮——/ 周围是渺无人烟的野岭荒山。/ 他风瘫的手虽然避免浪费,/ 但是毫无办法,事物的碎屑 / 依然像是小阵雨洒落在地上”[13]。华兹华斯将孤单的老人融进群山,栩栩如生而又超凡脱俗,他们虽然命运悲苦,但仍保持着人性的尊严。诗人的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在此处达到高度的融合,揭示出世界上每一个孤独脆弱的个体都是踽踽独行的悲苦乞丐。这些具有独创性的诗歌被注入善良智慧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来自诗人自己的精神,“是一种在宁静的回忆中唤起的慰藉感——这是一种希腊雕塑式的静穆和悦感”[14]。
五、结语
诗歌本身有着独立的内在美学价值和目的,虽然陶渊明与华兹华斯所处的时代,所接受的思想熏陶,以及人生经历都有差异,但二者诗作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却极其相似,字里行间无不传达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强调宇宙间万事万物应通过“调适”和“协同”达成统一。他们从自然的范式中不断探索人类的发展动向,扭转被羁人的官场和现代工业歪曲的人与自然关系,被战争与资本积累疏离的人与社会关系,被人类中心主义囚禁的人与自我关系。在文化重构进程中,生态文学的研究发出响亮的声音,以建立生态文学观念和审美观念,寻找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为目的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生态书写是对自然、社会、人性的思考,可为当代生态诗学的建构和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一条借鉴思路,鼓励人们走出狭隘的自我意识(ego-consciousness),走向更为包容的生态意识(eco-consciousness),用“精神”超越“物质”,用“诗意的栖居”打败“科技的栖居”,消减社会发展带给人的异化现象和心灵矛盾,为饱受工具理性和身处精神危机下的人类开辟了一条复返自然之路。
参考文献
[1] 王岳川.生态文化启示与精神价值整体创新[J].江西社会科学,2008(4).
[2] 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3]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9.
[4]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 Wordsworth W.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Lyrical Ballads 1798 and 1802[M].Fiona Stafford,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6]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 李丽娜.华兹华斯:心灵生态的守护者[D].北京:北京大学,2005.
[8] 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M].黄杲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9] 华兹华斯.华兹华斯诗选:英汉对照[M].杨德豫,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10] Carruthers G.Scottish Literature[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
[11]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的原则[J].新东方,2001(1).
[12] 易春.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田园诗歌的自然观比较分析[J].文化产业,2018(18).
[13] Wordsworth W.Lyrical Ballads,and Other Poems,1797-1800[M].James Butler and Karen Green, ed.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
[14] 张旭春.“以诗证史”与“形而上学的慰藉”——以华兹华斯《康伯兰的老乞丐》为例[J].外国文学研究,2020(2).
(特约编辑" 张"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