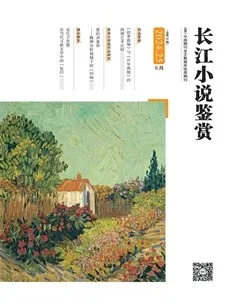弥赛亚时间与日常生活颂歌
[摘要]《我们的小镇》是美国剧作家桑顿·怀尔德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剧本,从生活、爱情、死亡等方面展开格洛弗镇平淡的日常生活画面。然而,剧作绝不意在展现田园牧歌般的小镇生活,其真正的主题深埋在对日常生活事无巨细的表现之下:作为一部叙述体戏剧,其中时间和空间随意切换的叙述话语并不止于一种戏剧表现方式的革新,更是一种全新的解读生命时间的共时性视角,引领我们走向生命的内在时间,看到弥赛亚时刻降临的可能性。怀尔德取消情节,淡化戏剧性,采取种种“间离”手段,制造陌生化效果,力图使读者的注意力从表层的故事情节转向深层的日常生活内核。《我们的小镇》实质上是一首对日常生活的颂歌——千篇一律、平淡无奇的当下生活里才真正埋藏着救赎之地。
[关键词]《我们的小镇》" 日常生活" "弥赛亚时间" "共时性
[中图分类号] I06" "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25-0112-04
一、引入叙述元素 发现共时性状态
《我们的小镇》是一部戏剧式的现代寓言[1]。作为20世纪富有代表性的新文本,其最大的创新在于引入大量的叙述元素,以表演组织者(舞台经理)承担叙述性话语,从而对时空进行任意切换;以叙述代替动作,从戏剧性戏剧转向非戏剧性戏剧。
舞台经理在开篇介绍小镇概况时,用了一个奇妙的时态:“大概五年之后这里才会有第一辆汽车。”[2]一句话便将三个时间点杂糅起来:处于过去的当下(舞台经理说话的时刻),处于未来的过去(第一辆汽车出现的时刻),处于未来的更远的未来(隐含的信息:更远的以后出现了越来越多汽车),以时空的并置取消时间的历时性状态,引入共时性视角。这种共时性视角打破线性时间观,取消因果关系,在传统戏剧中按先后顺序接连发生的情节变成日常生活画面的片段式呈现。对此,斯丛狄在《现代戏剧理论》中评论道:《我们的小镇》是“拒绝戏剧”的“叙事性戏剧”。其中舞台经理的作用是解除“戏剧性的任务”,使“舞台叙述替代戏剧情节”,“情节的各个部分不再像在戏剧中相互产生,而是根据一个超越单个时间的普遍性计划,由叙事性自我来组合成一个整体”[1]。舞台经理运用叙述元素,通过“面对观众介绍环境”和“面对角色进行互动”这两大作用,传递出一种共时性的时空观念。
首先是舞台经理引出小镇背景环境的介绍。对小镇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文化氛围等的叙述,有时以旁白形式穿插在对话与动作中间,但更多是以对话的方式占据主要内容。在历史学家和报社编辑的介绍中,格洛弗镇是沉闷无聊的——这是一座没有任何新意和特色的小镇。格洛弗镇以最极致的普遍性成为所有小镇的代表,这种代表所体现的是一种具体的个性,格洛弗小镇中发生的一切在其他所有的小镇发生过;也是一种抽象的共性,一种拆除时间和空间后的共性,这就赋予了小镇和小镇中的人和事一种寓言性质,同时也暗示观众,这些表层的信息并不是剧作家希望我们关注的重点。除了对话传递出的信息,对话的发生方式也十分值得关注:编辑韦伯先生在上台之前被苹果割到手、观众席的男子在询问问题时被经理打断——这两出插曲目的在于塑造一种真实的日常生活细节,再加上舞台经理拖沓的话语和对极端真实性不遗余力的渲染,实际是对极端形式的现实主义的一种反讽和解构[1]。观众对现实主义戏剧极端真实性的要求,根本目的是更好地沉浸于剧情的体验之中,相信舞台上的不是幻觉而是真相。然而怀尔德的这种解构态度意在对这种故事注意力进行拆解,将个性事件化为普遍的共时性视角下的时空。斯丛狄认为,剧作家对格洛弗镇的介绍,是以“自然主义的意图”,将“环境作为决定单个人存在的要素”在舞台上展示,目的在于去除对白的客观性[3]。尽管斯丛狄对怀尔德是否达到目的持一种否定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剧中对小镇的描述绝非作为纯粹的客观背景进行介绍,而是试图将格洛弗小镇塑造成一个携带人迹的主体空间。小镇不单单提供了事件发生的客观场所,更是一个富有主体性的生命角色。
舞台经理的另一个作用是与角色进行互动。舞台经理可以肆意调度时空,他不仅可以控制整个舞台的时空位置,还可以将死者带回过去的空间。舞台经理这一角色并不具有任何宗教因素——这种能力并不是神性所赋予的,而是一种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的全新视角的折射:共时性。舞台经理将生与死,过去、现在、未来并时而置,这种处理之下,生命已然不是因果相连、环环相扣的线性时间,而是以生命冲动和生命直觉构成的绵延。舞台经理揭示出,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种外在于人自身的客观对应物,而生命的真实状态,是在混沌的共时性中完成的。在这种共时性中,线性时间没有了意义,空间也不再区分主体和客体,呈现一种交融的状态——小镇与人们彼此相互构成,密不可分。
二、淡化戏剧性情节 重返日常生活现场
怀尔德对故事本身丧失兴趣,是《我们的小镇》淡化戏剧性情节的根本原因。剧中的一切情节仅仅是情节,而不传递任何主旨。
为了使得情节作为前景而不指涉真正的主题,怀尔德以这样的方式消解戏剧性:在最开始就宣布一切人物的未来结局,通过“间离”破坏观演的沉浸性,让观众把注意力集中在情节背后的主题而不是情节本身上。例如介绍人物时,引出吉布斯医生和太太后便紧接着宣布他们逝世的日期;报童乔·克罗威尔甫一出场,就立刻告知观众他最终的悲剧性结局:年轻有为的生命被战争无情地毁灭了。在“高悬的死亡幽灵下,格洛佛小镇居民的日常生活获得了一种庄严感”[2],如前所述,剧中的共时性视角为平面的日常生活增加了厚度,使其不陷落在感伤剧情的窠臼中。
弃绝故事情节表明怀尔德厌弃以大人物、大事件的古典式戏剧为代表的线性历史观下的美学,进而转向现代主义范式下的日常生活美学——从日常生活中得到救赎。托多罗夫《日常生活的颂歌》中一段对日常生活的表述可进一步阐述这种转向:
日常生活并不一定是愉悦的——这个道理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呢?而且,他经常是折磨人的:重复某些机械的动作,被不得不面对的烦恼压得抬不起头,仅仅为了维系生存——自己或亲人的生存——就已精疲力竭。正是因此,我们才会那么向往梦想、逃避,才想要沉迷于英雄主义神秘主义,而所有这些支柱实际上都不是真实的。不应该抛弃日常生活(蔑视它,或将它扔给别人),而是从内部改变它,令它在意义和美的光照之下获得重生。[4]
源起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经历了“异化”和“抵抗”两个转变。“异化”阶段的日常生活理论将日常生活视作一种“对象化”“类本质”的生活状态。以异化为支点,试图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使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从而克服或超越、消除异化的日常生活理论,“将日常生活看作主体和客体辩证的同一场所,批判目的是要恢复日常生活的主体性”。20世纪70年代以后,研究“抵抗”的日常生活理论逐渐兴起,取代异化论成为主导范式。以“抵抗”为特征的日常生活理论主张不抛弃日常生活,而是以审美手段超越异化,如托多罗夫所说,“令它在意义和美的光照之下获得重生”,从而救赎日常生活[5]。作为沉闷乏味日常生活的反面,英雄主义和神秘主义固然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心生向往,但这绝不是救赎之地——这显然不是生活的本真面目。只有直面真实,救赎才可能发生。实际上,对日常生活的兴趣是一种伦理态度:承认最微不足道的甚至受谴责的行动也具有价值。看到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我们的小镇》真正的可贵之处——让故事浮到表层,摒除道德训诫,不从情节中寻找人为附加的教化意义,而是直面生活本身,还原生活本相。
因此,剧中的一切情节与道具没有区别,仅仅起到一种工具性的作用,如几张桌椅构成的布景一样,作为背景存在着。真正作为主角在其间活动的是连绵不断的日常生活细节,所贯穿的无意义的时间就是生命的救赎时刻——弥赛亚时间,但剧中人物无一例外地错过了。这就是怀尔德真正想要向我们传递的日常生活美学。在日常生活的反复折叠中,《我们的小镇》揭示出生命真正的美好存在于一种奇妙的共时性之中。
三、深埋的弥赛亚时间:作为内核和救赎之地
将情节的表层遮蔽去除后,我们将看到文本言说的真正主题——生活。“这部剧所讲述的其实是一件大事:那就是生活本身。”[2]舞台经理曾经点出了题旨:“你知道——巴比伦曾经有两百万人口,而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只是那些过往的名字,还有几份关于小麦的契约……可是,每个晚上,那些家庭都会坐下来吃晚饭,父亲会干完活回到家里,烟囱里会升起炊烟——就像这里一样。甚至在希腊和罗马,我们对那些居民的真实生活的了解,无外乎那些搜集到的打油诗和为当时剧场写的喜剧。”“所以,我打算把这个剧的剧本放在一份奠基石里,千年以后的人们就会了解一些关于我们的基本情况……这就是当年我们的方式:我们就这样成长、结婚和死亡。”[2]
《我们的小镇》一共分为三幕:第一幕的主题是日常生活,第二幕的主题是爱情与婚姻,第三幕的主题是生与死。这部剧的高潮看似是在第三幕发生的,艾米丽穿越生死,回到过去,却发现所有人对日常生活的真正美好之处无动于衷,直到得出一个悲剧性的宿命结论:我们对生活的美好感受永远不能和真正生活的时刻同时存在。然而,《我们的小镇》的核心其实在第一幕,对非对象化、类本质的日常生活的展开。送牛奶的男孩与医生的交谈、妈妈与孩子在早餐时分的对话,都是生活中不能再普通、不能再常见的场景。日常生活现身后,问题就在于:如何从日常生活中看到美呢?托多罗夫在《日常生活的颂歌》中给出了提示。
在托多罗夫看来,日常生活之所以被遮蔽,是因为对于效率的盲目追求。结果导向的生活使一切成为手段,因而我们眼中看到的只是最终目的,而没有行进的过程本身,自然也就远离了日常生活:我们的人生被机械的时间切割成段落,以重要的人生节点来标记生命时刻,正如艾米丽一开始选择回到的场景是婚礼、生育等重要的记忆,其实是一种对人生重要坐标的选择。随后在众亡魂的劝诫下,艾米丽选择了一个相对而言没有那么重要的时间点:12岁生日。重返过去后,她惊喜于小镇旧日的模样,惊喜于过去记忆的重新体验,然而,艾米丽的欣喜若狂却逐渐被失望和悲哀取代。时间不停歇地流逝着,母亲专注于种种琐事,这使艾米丽发现自己没有办法与母亲完成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我们甚至没有真正看一眼对方”。在失望之后,艾米丽动情地说:“再见,再见,世界。再见,格洛弗镇……妈妈,爸爸。再见,我的闹钟……妈妈的太阳花。食物和咖啡。新熨好的衣服,还有热水澡……睡觉和起床。哦,地球,你太美妙了,以至于无人能认识到你的好。”艾米丽终于意识到,原来生活真正使我们留恋的不是重大事件,而是重复又无聊的日常生活。
艾米丽的觉醒,实则是弥赛亚时刻的降临。弥赛亚时间观是本雅明针对线性时间观提出来的另一种时间概念。在线性时间观中,时间是断裂的,记忆和经验是本质组成部分。但这种历史主义下的时间,其实并不与我们本真的生命经验相联系。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对历史主义的线性时间观进行了批判和重构。历史主义的时间观发源于早期基督教,在工业革命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建立,历史主义者基于线性的时间观念,构建出一套在客观上连续不断进步的历史进步论。这种进步史观一方面埋葬过去的苦难,一方面对未来盲目乐观,并且把救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后来者上。然而,这种线性的时间观只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谎言。线性时间是同质的、空洞的、理性的,是外在于人自身的,并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状态。基于对线性时间的否定,本雅明提出了弥赛亚时间。本雅明认识到,世界在本质上是一种整体性存在,人类所追寻的无限的永恒性存在就蕴含在现世和当下的时间中,是一种非断裂性的救赎时间[6]。
但这种救赎时刻深埋在日常中,它埋得太深以至于无人能够察觉。生者是如此盲目,在线性时间观的支配下,我们不是回首过去就是仰望未来,殊不知最珍贵的东西就在当下的此间。吉布斯太太一直有去法国巴黎的心愿,“人这辈子应该在死前有此机会,去个不说英语,也不爱说英语的国家瞧瞧”,但始终没有实现[2]。然而,这个心愿的真实面目不过是一个不需抵达的路标,而非吉布斯太太切身的渴望。巴黎就这样作为一个远方的目的地存在着,但不必向那里行走。吉布斯太太未完成的心愿是一出日常生活中随处发生的浅淡的悲剧。吉布斯太太这种渴望远离日常生活、向往异乡生活经验的心理,呈现出一种矛盾感:一方面她倦怠了现有的生活,不能从日常生活中得到在世的救赎,然而一方面也没有充分的动力去远方寻找救赎。巴黎只需要虚无缥缈地存在着——这就是它的全部意义。但是,在这种线性时间观念的支配下,人生变成了一串点线相连的高速公路,从一个目的地到另一个目的地,从而使得真正的弥赛亚时间永远无法降临。因为生者永远不曾知晓“人类苦心孤诣找寻的无限的永恒性存在就蕴藏在现实经验世界和世俗历史中”[6]。
那么,其中有谁得到救赎了?只有死去的人。艾米丽与舞台经理的最终对话意味深长。“有没有人在活着的时候,意识到生命的意义——每一分,每一秒?”“没有。也许圣人和诗人会——他们能有一些认识。”[2]弥赛亚时刻的降临,必须深耕于日常生活美学,从最平常的生活中发现偶然性,注意到“立即的、无诗意的、自身缺乏美的存在”。生命的真正意义就在这些平日里不被注意的细节之中。
四、结语
《我们的小镇》毫无疑问是一首对于日常生活的颂歌。这种歌颂并不停留在表层的情节里,而是深入生活本身,对人的感知能力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做出全新的思考。在带有间离目的的叙事化改造下,情节成为不承载任何意义和目的的动作本身,只是单纯作为画面进行展示。在对线性时间的解构中,怀尔德试图破坏一切在感性层面带来的刻奇倾向,不遗余力地运用间离效果,希望观众的注意力能够转入更深的层面:对日常生活进行重新思考。怀尔德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任何一个不被注意的日常生活时刻都是弥赛亚时间降临的时刻。然而,正如艾米丽悲哀地发现,这个道理生者无法知晓,死者知晓但无可奈何。生活在当下的时刻,意识到此刻的每一瞬间都有救赎可能性的产生。在悖谬带来的淡淡的悲剧感中,《我们的小镇》深切地呼吁着人们对当下生活进行观照,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美好和动人之处,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救赎。
参考文献
[1] 但汉松,刘海平.现代寓言的舞台呈现:重解桑顿·怀尔德的《我们的小镇》[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1(1).
[2] 怀尔德.我们的小镇[M].但汉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3] 斯丛狄.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M].王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 托多罗夫.日常生活颂歌:论十七世纪荷兰绘画轻与重文丛[M].曹丹红,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 张道建.异化与抵抗:西方“日常生活理论”的两种路径[J].湖北社会科学,2018(7).
[6] 郭广.本雅明对历史主义线性时间观的批判与重构[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9(1).
[7] 本雅明.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
(特约编辑" 张"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