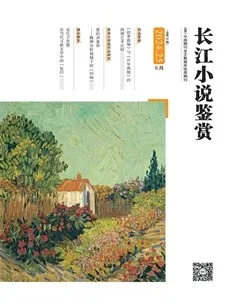寻找“自我”之途:空间批评下的《莫失莫忘》
[摘要]石黑一雄的《莫失莫忘》以克隆人为主角,讲述了克隆人为人类捐献器官直至死亡的悲剧故事。本文旨在运用福柯和列斐伏尔的空间批评理论,特别是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三元一体”概念以及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理论,深入剖析克隆人终其一生追寻自我身份的复杂历程,以此揭示克隆人在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小说描述了凯西、露丝和汤米三位主人公成长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学校、村舍以及画廊。通过描绘这些空间的地理特征及其对人物成长的影响,展现了三者对自我身份认知的持续变化过程。本文强调了空间批评理论在解析《莫失莫忘》中主人公寻找自我意义之旅中的重要性,综合分析了克隆人的自我认知过程,同时揭示了空间与人物身份意识构建之间更深层次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石黑一雄" "《莫失莫忘》" "空间批评" "身份意识
[中图分类号] I06" "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25-0079-06
一、引言
作为英国当代最成功的小说作家之一,石黑一雄近年来收获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与赞誉,其作品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他的《莫失莫忘》(2005)讲述了克隆人被设计为器官捐赠者的故事,小说入围了布克奖,并于2010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读者通过主人公凯西·H的视角,回溯了她和朋友露丝、汤米在黑尔舍姆、农舍和康复中心的经历。黑尔舍姆是一所寄宿学校,在这里,克隆孩子像普通学生一样接受教育。毕业后,他们被集体转移至农舍度过近两年的时光,待到成年之日,他们将在康复中心通过捐赠器官完成自己的“使命”。小说开篇即隐匿了这一残酷真相,随着故事的发展,越来越多关于学校的真相和他们的真实身份被揭示出来。
在《莫失莫忘》中,石黑一雄还通过人物角色探讨了社会层面的问题。对于这些克隆孩子来说,器官捐赠是他们未来唯一被允许和应该做的事情。像其他孩子一样,他们享受童年,接受教育。他们仿效人类行为模式,试图像人类一样生活。他们渴望身份的认同。但对人类来说,他们只是用来追求健康和长寿的工具。这一残酷的现实,构筑了小说的悲剧基调。为什么克隆人不能被称为人类,或者确切的人类是什么,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在科学技术的世界里,人类和非人类的问题必须被讨论。这部小说是科幻小说和文学作品的结合,反映了未来生活可能的一部分,并提出了基因实验和人类身份的道德问题。此外,强烈的存在主义主题对社会的激进变革提供了一个值得反思的研究领域。
在理论层面上,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为解读《莫失莫忘》提供了新的视角。他提出的“空间的生产”概念,涵盖了两种含义:“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和“空间本身的生产”。列斐伏尔认为,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人类的生产方式已经从“生产空间中的物”转向“生产空间本身”[1]。他批判了传统空间观的静态性,强调空间能影响并塑造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而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则进一步补充了空间如何对个体实施控制。这两者的理论贡献,为分析《莫失莫忘》中人物身份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不同空间中的身份问题
根据列斐伏尔的说法,“空间从来不是空的:它总是体现着一种意义”[1],因此,对物理空间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地理空间的表面描述,还要关注其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小说中有三个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空间:学校、农舍和画廊。这三个空间对几位克隆人的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节将运用空间批评理论,特别是列斐伏尔的“三位一体”理论,探讨人物从迷失到自我觉醒,再到最终身份确立的复杂过程。
1.学校
黑尔舍姆是一所寄宿学校,坐落在风景优美但相对与世隔绝的英国乡村。凯西和她的朋友们在这里度过了看似愉快且与普通人无异的童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黑尔舍姆这所“学校”实则是克隆人的摇篮,看护者们用纪律来营造出乌托邦式的幻觉,让学生们难以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真实身份与来源,更无法解答“自己来自哪里以及自己到底是谁”的根本性问题。
1.1 作为空间表征的“监狱”式黑尔舍姆
为了将这些克隆人变成“驯服而有用的身体”,“学校”采用了三种方法:监视、检查和评价。规训是福柯权力理论的一个重要术语。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阐述,许多现代机构都是为了规范人类,将人类塑造为“驯服的身体”而设计的[2]。这与列斐伏尔的“空间表征”理念相吻合,即概念化空间的输出,因为黑尔舍姆作为一所“学校”,人类可以在身体和心理上控制克隆孩子。规训首先是通过严格的监督来实现。黑尔舍姆的布局设计借鉴了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所提出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概念,其核心是一座中心控制塔,即学校的主要建筑物。此塔被呈环形排列的监舍所环绕,使得居于中心控制塔内的管理人员能够轻松观察到监舍内的所有活动,有效防止了任何逃脱行为。这一设计理念解释了为何在黑尔舍姆,尽管存在众多隐蔽角落,克隆孩子却总是难以逃脱监护人的监视,他们甚至错误地认为监护人拥有某种心灵感应的能力。他们由于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处于被监控状态,以及何时会受到监控,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他们心理上始终处于被监视的紧张状态,从而不敢随意行事,达到了一种“自我禁锢”的效果。
规训的第二种手段是检查,它“整合了权力的仪式、实验的形式、武力的部署、真理的确立,并显示了被视为对象的人的征服和客观化”[2]。为了确保未来器官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克隆孩子的健康状况被视为优先关注的重点。因此,他们需要定期进行体检,频率达到每周一次。此外,监护人对于吸烟行为持有极为严格的态度。图书馆的藏书中,并未收录诸如《夏洛克·福尔摩斯》等经典小说,其主要原因是这些作品中的主角频繁吸烟,而且书籍和杂志中含有的吸烟图片与插图已被系统性地清除,以减少不良示范效应[3]。与此同时,“创造力”受到了极度重视,原因在于它成为学校检验克隆人是否具有“灵魂”的关键途径。若个人的绘画、素描、陶艺或诗歌作品得到了认可,甚至荣登“画廊”,这将被视作极高的荣誉[3]。这种蕴含奖惩机制的审查过程,实则是对他们进行重新塑造与训练的过程,旨在实现思想和行为上的引导与规范[4]。
第三种规训手段是评价。首席监护人往往不会采取过于严苛的措施,然而,她的每一个举止都足以令学生们心生畏惧。如果不慎触怒了她,或是得知她对你的评价有所降低,你会感到深深的失落,并急于寻求改正。这种惩罚方式虽非直接的肉体惩罚,却能在他们的心灵层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1.2 空间表征中的身份意识丧失
克隆人的身份丧失,首先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命名上,如Graham K、Reggie D、Arthur H、Alexander J等。这些名字如同流水线产品上的序列号,字母组合成了他们的标识,更有甚者,有些人甚至拥有相同的姓氏,这不禁让人揣测他们是否属于同一批“制造”的克隆人。然而,这些孩子从未像正常小孩那样对自己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而感到好奇。在黑尔舍姆的权力结构影响下,他们似乎彻底丧失了自我认知。
此外,黑尔舍姆还会模仿外部社会开展一系列活动,但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巩固克隆人的附属地位。举例来说,学校设立了一个特殊班级,要求学生扮演各种职业角色,比如服务员、警察等,以便让他们体验和学习。然而,这些角色只限于服务行业或维护社会秩序的领域,这种安排无形中强化了他们为社会服务的观念。学校也会定期进行拍卖活动,但讽刺的是,学生们视为珍宝的藏品不过是外界普通人丢弃的垃圾[3]。按照列斐伏尔的说法,空间“……不仅是权威的控制机器,也是没有特权的人的防御工具”[1]。在业余时间,他们受到监护者和在这个空间内制定的无形规则的控制。克隆人经常“被告知或不被告知”,因此他们过着一种看似无忧无虑,从不考虑自己身份的生活。正如凯西所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对自己有一点了解的年龄,我们是谁,我们与我们的监护人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但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3]
2.农舍
农舍,作为学生们离开黑尔舍姆后首个抵达的地方,它不仅承载了他们从学校到外界的过渡,更成为连接黑尔舍姆与外部社会的纽带。这里汇聚了来自黑尔舍姆的毕业生以及其他地方的年轻人,凯西与几位密友便是在此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岁月。对他们而言,这里宛如一个缩影,映射出外部世界的轮廓。正是在这个空间中的实践经历,让几个主人公开始敏锐地意识自己的身份问题。在这个共同生活的空间里,他们通过日常的点滴交流,逐渐感知到与他人的不同之处,并由此激发了探索“自己是谁”的强烈愿望。
2.1作为空间实践的半开放性农舍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为空间的实践想象了各种新的意义和可能性。”[1]精神空间,作为心理与话语的交互场域,承载着逻辑性和形式化的抽象概念。文学作品通过具象化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意识形态,使得这些概念得以具象表达。起初,克隆孩子受限于黑尔舍姆灌输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但在农舍里接触到更多人后,他们逐渐开始“发现”自己。
克隆孩子被人类刻意安置在远离人类社会、近乎与世隔绝的农舍里。从凯西的叙述来看,这些小屋“(看起来)美丽而舒适,到处都是杂草丛生的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奇的东西”[5]。随处可见的杂草表明这些小屋离人类居住区很远。因为农舍位置偏远,所以农舍的主人每周只来这里两到三次[3]。他驾驶的那辆满是泥泞的货车也进一步印证了农舍坐落在一个偏远而崎岖的地区。更重要的是,除凯弗斯外,再无人类出现在这里,这一点凸显了农舍的隔离状态。不同于黑尔舍姆对克隆孩子的严格管控,在农舍,他们体验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可以走出小屋,与外界接触。然而,由于农舍地处偏僻,与人类社区相距甚远,克隆孩子若欲外出,必须一大早就离开他们的生活场所,以确保有充足的时间在外逗留。有一次,露丝、凯西、汤米和两个老兵去诺福克寻找露丝所谓的“可能”,五人于黎明前出发,直至午餐时分才到达目的地。由此可见,克隆孩子是被人类有意安排在远离人类居住区的农舍。
在农舍中,克隆孩子也被无形地监视着。对他们来说,大部分时间都被束缚在农舍内,鲜少外出。即便他们离开,也必须确保在凯弗斯的登记册指定的日期和时间前返回[3]。因此,当克隆孩子前往诺福克时,他们必须早早出门,以确保能在日落前归来,并及时在登记册上签到。登记册记录了他们出入农舍的时间,这反映出即使身处半开放环境,克隆孩子仍处于某种隐蔽力量的监视之下。不仅如此,克隆孩子之间也会互相监视。凯西的新朋友克丽丝指出,“在农舍后面”不可能进行秘密谈话,因为“(每个人)总是在偷听”[3]。农舍的存在,实质上延伸了黑尔舍姆学校所构建的“圆形监狱”体系。克隆孩子不仅要面对隐形的监控,还要承受同伴的监视。所有的监视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不断提醒着克隆孩子所肩负的人类安排下的义务。他们理应留守此地,静候成为照顾者或捐赠者的召唤。因此,农舍的隐形监控机制也推动了捐赠计划的实施。
此外,这些简陋的农舍也迫使克隆孩子不得不服从人类的意志。这些小屋是数年前一个废弃农场遗留下来的建筑,其中包含一座年代久远的主屋,以及周边的谷仓、外屋、马厩等,共同构成了克隆孩子的居住空间。克隆孩子在农舍中的居住条件非常简陋。更糟糕的是,除了夏季,整座农舍都非常寒冷。根据凯西的叙述,他们出门的时候即使穿上两三条牛仔裤,还是觉得很冷。由于这种严寒的环境,他们不得不蜷缩在老旧的窗帘下,甚至是地毯下进行取暖。有时天气过于寒冷,他们只得将所有可用之物堆叠其上以御寒。“虽然农舍里有大型的加热器,但克隆人必须依靠能带来煤气罐的凯弗斯来使加热器运转起来。”根据凯西的回忆,“我们一直要求他给我们留下大量的供应,但他总是沮丧地摇着头,好像我们一定会轻率地用完它们。”[3]只有当天气变得越来越冷的时候,凯弗斯才会同意给克隆孩子一个装钱的信封。于是,克隆孩子可以用这笔钱购买煤气罐,确保加热器正常工作。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克隆人在农舍中的生活条件恶劣。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因而只能仰赖人类援助维生。为了继续生存,他们必须顺从人类的意志。
2.2 空间实践中的身份意识觉醒
在这个半开放的空间内,阶级的划分并非基于权力地位,而是依据群体间生活方式的差异。当凯西与朋友们初抵农舍时,很快便察觉到他们的习惯与其他人非常不同。为了融入这个群体,克隆孩子便有意识地效仿这些人的行为。露丝观察到,“这些夫妇在公共场合从不做任何让人觉得炫耀的事情,而是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就像正常家庭中的父母一样”[3],因此,她改“用指关节的背面轻轻地拍一下伴侣的胳膊,靠近肘部”[6]的亲昵方式,代替了在黑尔舍姆习得的亲密表达。然而,凯西观察到,这些人也会通过电视节目学习和复制一些行为模式,他们频繁引用的口头禅“上帝帮助我们”源自一部美国电视剧。此外,从夫妻间的非语言交流、同坐沙发的姿势,到他们争执与离开房间的方式,无不体现出他们对电视或电影场景的模仿。
凯西逐步意识到她与其他人之间的不同,并开始认识到她的独特存在意义。她认为露西的行为转变,是后者试图挣脱在黑尔舍姆形成的自我形象的尝试。在经历了身份认同的危机后,克隆孩子展现出他们正在建立身份认同,并试图通过放弃过去的身份标识来更好地适应新环境。他们通过模仿他人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归属,这反映出他们渴望融入外部世界的强烈愿望。在缺乏外部参照的情况下,自我认知难以自发形成,因为自我身份的构建是在与外界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尽管农舍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觉醒自我意识的环境,但他们在不经意间模仿他人的行为,暴露出他们在自主思考和内在行为模式上的欠缺。他们的语言、动作和交流方式均是通过间接学习获得的。自我认知的缺失驱使克隆孩子踏上了探索身份的征途。大多数克隆孩子相信,既然他们各自是从某个正常人类的原型克隆出来的,那么这些原型一定存在于世界某处。只要找到自己的“原型”,就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真实存在,甚至有可能预测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然而,当追寻未果后,露丝说出了深埋心底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我们是模仿社会渣滓创造的。吸毒者、妓女、酒鬼、流浪汉……如果你想要找到原型,那就去阴沟里、垃圾桶里找找吧。”
在追寻自己的梦想破灭后,露丝意识到自己出生于“社会底层人口”或“物质底层废物”中,这让她陷入绝望。因此,她和同伴们明白了在人类社会中,他们并未得到认可,且社会地位低下。尽管凯西表面上对“原型论”持怀疑态度,但她私下里仍会在色情杂志上寻找自己的“原型”,企图借此解释她内心深处涌现的强烈性欲。这正符合了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理论。人类本身是边界模糊、缺乏完整性的存在。在构建自我身份时,人们需要在与内在“自我”的偏离中寻觅,借由外界的映像来弥补对完整性的想象。然而,当人类将克隆人明确地界定为物品、废弃物、服务的客体时,克隆人便无法在与人类的相似性中找到归属和认同,“仿佛你每天经过的镜子里,突然映照出的是一件令人不安和陌生的物体”。
3.画廊
画廊,作为想象的、象征性的表征空间,是克隆人没有见过,甚至对其心存疑虑的地方,但这里却成为他们确立自我身份、寄寓生活憧憬的舞台。
3.1 作为表征空间的幻想画廊
在真相大白之前,克隆孩子都认为,感情深厚的情侣或夫妻可以通过将作品提交至画廊,以此作为证明,从而赢得延期捐赠器官的机会,延长享受世界的期限。起初,画廊被视为对他们创造力的最高褒奖,然而,当凯西重遇昔日黑尔舍姆的管理员时,她得知所谓的“画廊”只不过是一个废弃的“黑暗之地”,布满“蜘蛛网的痕迹”,也就是说,根本没有画廊。空间的幻象破灭,象征着对延迟捐赠美梦的彻底粉碎。
3.2 表征空间中自我身份的确立
事实是,管理员收集克隆孩子作品的初衷在于她认为这些创作能揭示他们的灵魂本质,或者说,她意在证实克隆人同样拥有灵魂。“我们对整个捐赠过程提出了质疑。最重要的是,我们向世界表明,如果学生在一个人道和文明的环境中长大,他们就有潜力成长为有思想和聪明的人,就像任何普通的人类成员一样。”[3]但这个世界充斥着冷漠,人们最关心的是治愈癌症,许多人拒绝承认克隆人为“生命体”。凯西和汤米终于明白了他们是为器官捐赠而生的克隆人,注定无法被外界所接受。在一次简单的发泄和一段时间的愤怒之后,凯西和汤米各自踏上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
经历了无数克隆生命轮回的凯西,终于在心灵深处找到了救赎。在这个独特的表征空间中,她成功塑造了自己的身份,并领悟到了自身存在的深远意义。“一个好的照看者可以对捐赠者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3]凯西坚信,尽管汤米已经不再需要她,但新生的“克隆人”还需要她的关怀,这种无私的精神激励着她继续前行。如果说露丝及其他克隆人的死亡揭示了无知之死,那么汤米和凯西在了解所有真相后,选择坚守使命而非逃避,则是他们成熟蜕变的标志,象征着他们已经放下过往,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群“工具人”面对死亡的态度,从最初的恐惧演变为一种平和的接纳。伴随着友谊与爱的力量,他们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无间。他们相互扶持,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小说的最后,凯西站在一大片耕地的边缘,平静地迎接即将来临的捐赠任务,她没有哭泣,也没有失控,只是稍作停留,随后转身返回车内,加速驶向人生的终点站。
三、结语
《莫失莫忘》作为石黑一雄的代表作之一,细腻描绘了克隆人的成长历程。黑尔舍姆、农舍与画廊,这些地点见证了凯西等人的人生轨迹及其记忆,映射出一条艰辛的自我身份探寻之旅。从空间的角度剖析这部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视角,去理解三位主角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探寻“自我”。
空间不仅是人类活动的领域,更是叙事构成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根据莱文的说法:“不仅仅是我们吃什么,还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和我们走过的房间。我们的感觉适应我们居住的空间,就像我们改变我们居住的空间一样。”[5]空间塑造了在这个空间里的人。同时,人们通过在空间中的生活经历认识自我。因此,解读人与空间的关系,能够为我们审视身份提供别样的视角。
显然,空间在凯西、汤米与露丝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农舍和画廊,这些空间与时间交织在一起,给他们一种归属感,勾勒出他们的生存状态,决定他们的存在方式。本文首先解析了黑尔舍姆寄宿学校的空间特性。其地理景观笼罩在神秘的氛围中,很少有人进出这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全体克隆孩子都在监护人的监视之下。正如福柯在边沁的“圆形监狱”概念上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和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表征”。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理论认为,圆形监狱的设计使得中心的监视者可以无死角地观察到所有囚犯,而囚犯却无法确定自己何时被观察,这种不对称的监视机制导致了一种自我规训的现象。
教育的目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而是为了约束克隆孩子的行为。对孩子们来说,黑尔舍姆的回忆是甜蜜的,但这一切源于他们无知。潜藏于空间下的监视机制,令他们对自己到底是谁一无所知,只能遵从监护人的命令。随后,本文探讨了农舍的空间属性。相较于学校,农舍的建筑与设施都很破旧,但克隆孩子在那里得到了更多的自由。尽管最初很不习惯,但他们不久便可以开车到处转了。事实上,克隆人仍然处于隐藏力量的控制之下,因为如果他们想出去,必须得到签字同意。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孩子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特殊的,于是积极地寻求“自我”,这符合列斐伏尔对空间实践的定义。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凯西和汤米形成了自己的想法。第一次得知自己只是克隆人的残酷现实,以及无法过上正常人生活的事实,令他们对“画廊”所象征的真相倍感痛苦。在了解了最终的无形表征空间后,凯西和汤米对自己有了全面的认识,不再将自己与其他克隆体或“正常”联系起来定义自己。在那之后,汤米继续践行自己的“使命”,而凯西则知道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死亡,她变得忠于自我。在小说的结尾,即使心中悲痛,她也没有停下脚步,重新确立了自己的身份。
综上所述,小说一方面揭示了生物技术滥用与异常文化机制引发的身份危机,以及对伦理缺失和人类异化的批判。克隆人作为悲剧的承载者,遭受主流社会的排斥,致力于寻找自我价值,以期获得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作品展现了作者对边缘化群体的深切同情。作者频繁在不同文化间穿梭,这导致他的身份碎片化,归属感缺失。通过小说创作,作者成功地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为这一群体发声,生动描绘了该群体共同承受的创伤记忆与不懈探索。
参考文献
[1] Lef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Blackwell,1991.
[2] Foucault M.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M].New York:Vintage,1979.
[3] Ishiguro K.Never Let Me Go[M]. London:Vintage Books,2005.
[4] 谷伟. 沤浮泡影——略论《千万别弃我而去》中“黑尔舍姆”的体制悖论[J]. 外国文学,2010(5).
[5] Toker L,Chertoff D.Reader Response and the Recycling of Topoi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J].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2008,6(1).
[6] Semelak M. The Suffering of Existence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J]. Ars Aeterna,2018,10(2).
(责任编辑" 余"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