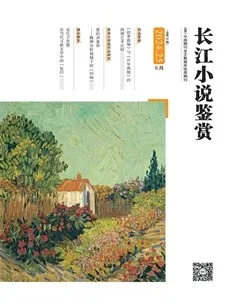撕裂的认同:库切《青春》中的文化身份构建
[摘要]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所著的小说《青春》是一部视角独特、内涵深刻的作品,它通过自传体的形式反映了后殖民时代被殖民国家人民面对社会巨变时的深刻反思。本文从小说中主人公的文化身份转变切入,分析了一位流浪作家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游离、断裂与融合。以库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多种文化之间被迫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往往伴随着内心的痛苦和挣扎。小说揭示了在后殖民时代,被殖民国家的人们在面对多变的世界时的迷茫与无措,以及他们如何在流离失所的世界中寻找自我认同和文化身份的定位。
[关键词]《青春》" "库切" "自传体小说" "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 I06" "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25-0070-05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一位南非白人作家,1940年出生于南非的开普敦。他在1983年和1999年荣获英国文学最高荣誉——布克奖,成为首位两度获得此奖的作家。由于布克奖仅授予英语创作者,库切的南非背景便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在库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前一年,他的作品《青春》(Youth: 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Ⅱ,2002)面世,这是他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为《少年时代:来自省城生活的情景》(回忆录)(Boyhood: 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1997),第三部为《夏日》(Summertime: 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Ⅲ,2009)。这三部作品的背景分别设在南非、英国和美国,与库切在南非成长、赴英美留学、移民澳大利亚的人生轨迹相呼应。库切做过电子信息工作,也曾在大学里教授文学,其跨学科的学习经历和丰富的地理阅历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地域和文化的多样性。
小说《青春》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细腻地刻画了主人公约翰(实际为库切的化身)从19岁至24岁这一青春阶段的成长历程。19岁时,约翰进入开普敦大学,开始了数学学习之旅。毕业后,为了逃避南非即将发生的暴乱,他“逃”往英国伦敦,成为软件编程员,但是他渴望成为艺术家的梦想一直存在。身处他乡,约翰的内心始终处于激烈的斗争中,他在矛盾中挣扎,渴望着自由,却又时常被一种不甘的麻木感所笼罩。《青春》并不是库切最为出名的作品,但是作为一本自传体小说,读者可以从中读出他在成长过程中找寻自我道路与身份时的迷茫与失落、恐惧与兴奋,尤为重要的是,约翰在他乡的成年之旅,不仅是个人的心灵探索,也隐喻了南非国家在政治定位上的艰难探索与坎坷历程。
身份问题构成了当代后殖民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在社会交往中,个体与群体通过辨别与选择,将自己或他人归类于某一特定群体。这些群体既可以是现实存在的实体,也可以是基于精神层面或想象构建的虚构群体。个人或集体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社会环境的变迁、自我心态与追求的发展,会感到自我身份的断裂(rupture, discontinuity),由此产生不安定的归属感,进而激发自我身份的焦虑。文化快速变迁是后殖民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也是造成自我连续性(self-continuity)中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无法摆脱的南非身份
“身份”的英文是identity,这个词也有“认同”的意思,是个人或集体对自己的定位,也就是“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是谁的问题”[1]。文化身份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正如霍尔所分析的那样,身份的构建并非源自外部,而是源自语篇内部。然而,对身份的分析不能简单嫁接到种族化和人种化的分析中,还需要理解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和意识形态[2]。
自传是关于自我信息的记忆,是从古至今都盛行的文学体裁。自传中不仅有感情的表达和对事物的独到见解,也蕴含着人生体验和教训。但这些并不仅仅是对自我复杂记忆的混合记录,它更深层次地探讨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故乡与他乡以及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对比。记忆并非只是无声的反思和怀旧,它常常是痛苦的过程:我们将破碎的过去拼凑起来,试图为当前的伤痛赋予意义[3]。库切将自我的记忆写成自传体小说,这不仅仅是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更是对后殖民社会中受压迫群体在寻找自我身份过程中所经历的困苦与迷茫的深刻反映。
《青春》的主人公约翰为了逃避南非即将发生的暴乱,来到他梦想中的英国。他自幼接触的学习材料皆源自英国,家庭环境也使他始终沉浸在英语的氛围中。由于对英国文学的喜爱,所以在他的眼中,英国是此生必须追寻的圣地。来到英国之后,他试图抛却一切“南非”的印记,重新开启艺术的人生,但事实并不如他所愿。为了成为“英国人”,他远离了母亲对他的控制,并努力抹去脑中关于南非的记忆。《青春》一开篇,约翰就表明了追求自由与独立的观点:“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你不需要父母。”①在刚成年之际,他就已经实现了经济独立,在求学期间通过同时做多份兼职工作自给自足,不依靠家庭独自支付了学费以及生活费。除此之外,他还为未来在英国伦敦的生活攒下了一笔积蓄。源于对家庭记忆的逃避和自我梦想的追求,约翰在开普敦大学求学期间也很少回家看望父母。到了伦敦,约翰本期望能够通过远离故土来逃离家庭和母国对他的影响,但事实并非他所愿。远在千里的母亲每周都给他寄来信件;报纸上有关南非的消息总是不自觉地引起他的注意;他的南非身份和印记好似总在提醒身边的英国人,他并不属于伦敦。约翰努力融入新生活,但沉重的记忆使他无法完全摆脱南非身份,而英国人也将他视为来自殖民地的外来者,将他看作与他们不同的“他者”。
《青春》中写道:“作为南非人,现在待在英国不是个好时候。南非表现了巨大的自我公正,宣布自己是一个共和国,很快被开除出了英联邦。”在约翰看来,英国对南非的态度冷淡且毫不关心,就算南非消失于世界,英国也并不会在意。这种态度不仅反映了后殖民时期复杂的国际关系,也深刻揭示了身份认同与文化隔阂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小说中,约翰不仅仅认为南非的地位低于英国,毫无民族自信;他还认为自己作为南非人,也是地位低下的“他者”。就算他的工作能力以及学历水平能够让他在英国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他依旧认为自己不适合待在英国,对南非身份极度缺乏自我认同。与此同时,他个人对于英国的认同感也逐渐变得模糊起来,这进一步凸显了身份构建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比如,在谈到英国对待文化艺术的观点时,《青春》中这样写道:“现代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平庸得令人不安的国家,和威廉·亨利时代的英国及埃兹拉·庞德在1912 年强烈谴责的大排场游行没有什么不同。”
事实上,就算从非洲移居到英国的移民接受了来自英国的语言、文化的影响,但由于地理距离和殖民历史遗留的阻隔,他们难以真正融入英国社会,更无法与长期生活在英国本土的居民享有同等地位。他们可能深受殖民教育的影响,认为自己已经融入西方社会,但在深入探究其根源时,他们仍能感受到被排斥在英国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感。他们竭尽所能地向英国主流文化靠近,寻求与英国文化历史的关联,却因为他们的南非文化背景而被视为“他者”,最终被迫成为英国社会中的孤岛,被孤立于主流社会之外。然而,作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库切在时代的洪流中努力发声,他致力于“激起不同语言和声音之间的争鸣和碰撞,在这种碰撞的过程中寻求真理”[4]。
二、难以确定的英国身份
《青春》中花了大量笔墨来描述约翰的交际网络——来自不同国家的情人、公司的男女同事们、诗歌协会的成员、偶遇的英国女人,以及某个情人的房东等各色人物——对他的看法,几乎一致地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冷漠”。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在英国,女孩子对他根本不予注意,也许是因为他身上仍然残留着一丝殖民地的傻气,也许仅仅因为他衣服穿得不对。”“在火车上,女孩子的眼睛从他身上一滑而过,或者不屑地呆滞地看着他。”即便遭受英国人的区别对待,约翰仍然选择积极融入英国社会,从外表穿着、谈话内容、表达方式等方面做出改变,模仿并试图成为英国人。
尽管殖民地文化的烙印在约翰身上可能难以从根本上消除,但个体的外在形象,如衣着和发型,却可以通过外界干预和个体选择而改变。这种外在形象的调整,不仅关乎审美和时尚,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社会认知和自我认同。约翰努力融入伦敦的时尚文化,穿着与他们一样的黑西服,可是不管约翰如何改变自己的外在形象,也无法改变他被标记为“南非人”的事实。约翰仿佛能从伦敦人的眼中读出:“我们不需要一个没有风度的殖民地人。”在与同事交谈中,约翰发现他们避免深入探索志向与追求等深层次的个人话题,对于个人生活、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以及政治、宗教和艺术等话题更是只字不提。因此,约翰在交流中仅能就无关紧要的话题,如天气等安全且非私人的话题表达一些看法。这些显示出约翰与英国同事在沟通内容和深度上的局限。
此外,公司的女孩对待约翰和英国本土男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约翰无法真正融入英国的社交圈,唯一能够深入交流的英国朋友仅有一位男性同事,他们交流的话题也仅限于英国的天气和公司的发展状况。这无疑加剧了他作为“他者”的感受,加深了他对于英国和南非之间历史隔阂的认知。由于伦敦人对他的轻视,他发现自己难以融入伦敦的社交圈子,于是便将心思倾注于自己的艺术理想。在异乡,他把空余时间寄托于影院、书店和博物馆,期望能在欧洲悠久的艺术文化中寻求灵感。闲暇之余,他常常独自漫步于大英博物馆,沉浸于各种作品之中,怀揣着创作出令人钦佩和敬仰的诗篇的渴望,期望能在文学世界中留下自己独特而深刻的烙印。
约翰曾经认为只要远离了家庭和南非的束缚,就能够实现成为伟大诗人的理想。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来到英国后,他对英国的水土不服以及英国人对他的“他者”标签,让他难以像十七八岁时那样随心所欲地创作出诗歌。他自己也感觉到,远离了母国熟悉的文化与生活,他的创作才能在逐渐褪色。让他最为愕然的是,过去一年中他唯一钟爱的那首诗歌,其内容竟然与他的南非文化背景惊人地契合:
捕龙虾人的妻子
已习惯于独自醒来,
她们的丈夫多少个世纪都是黎明出海;
她们也不像我夜不安寐。
如果你已离去,那么就到葡萄牙捕龙虾人那儿去吧。
这首诗讲述了捕龙虾人的妻子等待丈夫归来的故事。南非龙虾价格很高,尤其是尾肉,是一种主要在高端餐厅才供应的美食。约翰描写南非本土寻常夫妻间的故事得心应手,然而,当他尝试在散文作品中描绘英国时,他意识到自己对伦敦的熟悉程度尚未能全面展现其深邃内涵。尽管他对伦敦有独到的见解,却自觉这些看法并无特别之处。他尚未能完全掌握伦敦的精髓,反而被伦敦深刻影响。身处繁华与现代的大都市伦敦,他的思绪却紧紧围绕着不堪回首的南非记忆,如平凡的农村家庭、不良的教育环境,以及家中南非语言的缺失。在这样的背景下,约翰既无法摆脱南非给他留下的深刻烙印,也难以在英国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这种双重身份的困境,使他在文化和身份认同上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挣扎。
对于怀有伟大文学梦想的约翰来说,发表作品是让自己的才华被看见、思想被接受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但是他却认为自己难以在英国出版那些有关南非的故事,因为英国人未曾见过南非海滩上的卵石,没听过海鸥与风搏斗时发出的尖啸声,所以可能无法理解其中蕴含的情感与力量。约翰的担忧其实反映了他内心真实的南非情感——激情澎湃、历史悠久,这也注定了他无法轻易摆脱南非身份。约翰曾认为,只要将自己的外在变得“英式”,就会得到英国社会的认可,摆脱南非身份并确立英国身份。但现实却是约翰永远无法摆脱他的南非文化之根,也难以轻易找到属于他的欧洲文化源头,只能被迫成为欧洲文化中的“他者”。
三、努力构建的“居间人”身份
霍米·巴巴在探讨身份的自我塑形时,提出的“双重身份”理论赋予了身份多维度和流动性的特征。身份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在环境巨变中建构具有连续性的身份,这意味着身份并非固定的,而是开放流动的。个人可以拥有多个身份,这些身份相互补充、互相影响。“双重身份”概念在跨文化交流中尤为适用,它既能保留个体在主流文化中的初始身份,也为在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吸收其他文化提供了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同时选择多种身份,而是指一个人在时空和语境的变化中,会经历不同的身份认同阶段。作为帝国流浪者的库切恰好经历了这样的身份变迁,因此他的身份认同显得复杂且充满撕裂感,游离于英国身份和南非身份之间。《青春》的主人公约翰,时而自我定位为英国人,时而又被英国人视为殖民地的后裔——布尔人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库切在多数情况下,对这两种身份标签都未给予明确的认同。
库切徘徊在南非与英国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原因,根植于南非独特的社会背景以及库切个人的家庭背景。库切既无法完全融入英国文化,也难以完全归属于南非本土文化,然而,他又无法彻底摆脱这两种文化的深远影响,最终成为一个混合文化中的夹缝人,身处边缘地带,不断寻求自我认同的归属。
库切是一位流浪作家,其显著特点就是不与任何单一的文化身份相认同。他作为一个文化流浪者,既痴迷于新世界,又对此感到深深的困惑。他不断地与各国的文化进行交流,在青春时期,这种交流主要围绕两种文化——本国南非文化与理想中的英国文化。在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中,他与各种文化既建立联系,又被迫经历断裂。库切在《青春》中细腻地展现了约翰在探索自我身份与寻求归属感的心路历程。同时,小说中对人物身份模糊状态的刻画,也巧妙地映射出后殖民社会中青年人所面临的真实生活状态。这些青年人既在反叛旧传统与寻求革新,又在接纳与融合新文化,展现了他们复杂而多元的身份认同过程。
在一个人员流动频繁、文化交流密集的世界中,“试图将文化和身份捆绑在某一具体的地域上,反而变成一种最为倒退的意识形态”[5]。因为在流动的过程中,地域与文化的位移现象显著。举例来说,在传统民族概念的框架下,英国的文化往往与其特定的地域紧密相连,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在现实的国际语境中,英国文化早已通过殖民主义的深远影响,跨越地域界限,深入世界各地,展现出其超越国界的广泛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若坚持使用民族来界定文化和身份,便会遭遇一系列难题,如约翰的困境:无法摆脱的南非身份和难以确定的英国身份。约翰这样的“居间人”成为混杂体,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或者说是别无选择。换而言之,这是一种妥协的身份,既然无法完全摆脱任何一种文化,又无所适从,同时内心拒斥一种文化,又无法被另一种文化接受,只好退而求其次,以一种“居间人”的姿态面对文化的两难窘境。从此意义上而言,这可谓是一种被动中的主动策略。
在经历长时间的内心反思后,约翰才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这一独特特点。在英国长时间生活后,他对南非身份的态度从曾经的闭口不谈转变为逐渐释然并接受。他曾经怀揣着对英国民族身份的强烈渴望,这种追求驱使他产生了与其他民族划清界限的迫切需求。因此,他选择逃离南非,试图从根本上断绝自己与那片土地的关联。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即使他置身于英国,对于任何与南非相关的消息,他依旧无法忽视。在英国探寻自我认同的旅程中,约翰与不同的女性交往、频繁更换工作,最终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并找到了自己作为“流浪者”所拥有的多样且独特的归属感。正如小说最后一章所言,在静谧的夜晚,他沉浸于个人的书海和论文撰写之中,而午后的时光则献给了他热爱的板球运动。每隔一周,他还会在皇家饭店小憩,享受与阿特拉斯——这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计算机独处的宁静夜晚。若单身生活注定是一个人的旅程,那么这样的生活方式无疑是其中最优雅、最充实的选择[6]。
四、结语
身份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个人或集体的身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流动,此间包含着无数和谐又矛盾的情感与思想。身份出现在特殊权力形式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并因此成为具有差异与排他性的标记性产物,而不是在无外力作用下自发形成的统一体的标志[7]。《青春》主人公约翰的身份受到转移的地理时空和变化的民族语境影响,更凸显了他在殖民话语中的生存困境,但是库切以冷静客观且深刻自省的态度书写了自己的青春成长。流浪的过程充满了与祖国分离的痛苦和理想归属感的失落,但也有其优势。正如霍米·巴巴所说的移民文化视角,“最真的眼睛现在也许属于移民的双重视界”[8]。流浪知识分子为后殖民语境下外来文化的变迁与碰撞提供了双重研究视角,他们主导后殖民批判话语,为弱势群体发声,并提供新的立场与解决途径。他们关注多重身份群体的诉求,反思民族和种族问题,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青春》,王家湘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
② 布尔人,是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的旧称,是南非和纳米比亚的一个白人种族。
参考文献
[1] 陶东风,和磊.文化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 斯图加特. 文化身份问题研究[M].庞璃,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3] Bhabha H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Routledge, 1994.
[4] 段枫.想象不可想象之事:库切的小说创作观及其后现代语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5] 生安锋.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4.
[6] Coetzee J M. Youth[M]. London:Viking,2002.
[7] 徐明玉.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研究[D]. 沈阳:辽宁大学,2020.
[8] Bhabha H K. Life at the Border:Hybrid Identities of the Present[J]. NPQ: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1997.
(责任编辑" 余"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