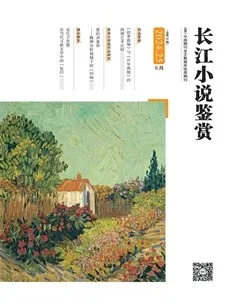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黑人女性的身份建构
[摘要]《秀拉》是托尼·莫里森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出发,不难发现小说中黑人女性角色在身份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压迫,以及在这些压迫下她们所采取的身份建构策略和产生的不同结果:海伦娜始终处于盲目和顺从的状态之中,心甘情愿地扮演“他者”形象,在既定的规则中安分守己;伊娃在建立起自身权威后,虽变为压迫者的同盟,却依旧面临着主体意识的缺失;秀拉则在激进反抗后,体现出对一切事物的疏离感,最终消解了全部的生活意义。面临多重压迫,对姐妹情谊的培养成为莫里森所提倡的黑人女性进行身份建构的可行途径。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 "《秀拉》" "身份建构" "后殖民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I06" "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25-0064-06
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是20世纪最重要的美国作家之一,著作颇丰,她先后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以及诺贝尔文学奖。不同于前辈黑人男性作家从社会、经济等宏观层面对剑拔弩张的种族关系进行描写与抗议,莫里森将目光对准与她同肤色的女性同胞们的处境,以她们的日常生活为自己的创作灵感来源。凭借自己的种族及性别特质,莫里森“进入到那些不是黑人、不是女性的人所不能进入的一个感情和感受的宽广领域”[1],将处于多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的生活带入大众视野,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题材。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秀拉》中,莫里森刻画了多个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黑人女性形象,展现了她们在种族与性别重压下的挣扎,以及身份建构的不同策略。
关于《秀拉》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75年,Joan Bischoff发表了研究其与《最蓝的眼睛》之间共同主题的论文[2]。短短数年后,莫里森的研究便迎来了女性主义转向。以Barbara Smith为代表的一众学者开始关注小说中蕴含的女性主义思想,秀拉这一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也因此被视为具有反抗精神的新型黑人女性形象[3]。截至目前,对《秀拉》的研究已涵盖了主题、人物塑造、叙事技巧、象征手法、黑人传统文化等多个领域。小说的内涵也不断被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等流派所丰富和充盈。在莫里森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外对其关注度不断提高,相关研究更是呈现出涵盖范围广、关注主题多样的特点。但值得一提的是,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分析解读莫里森《秀拉》中女性角色的身份建构,依然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与空间。
一、理论基础
后殖民女性主义,又称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其形成受到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4]。作为弱势群体发声的重要理论工具,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和力,二者都试图颠覆“主体/他者”这一对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5]。但是,它们各自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后殖民主义理论往往忽视了被殖民群体内部存在的性别压迫现象,而传统女性主义则把目光局限于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第三世界女性的独特困境与挑战被排除在外。对此,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钱德拉·莫汉蒂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传统女性主义中隐含着种族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遗留[6]。
传统的“第三世界”概念,通常指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西印度群岛等历史上受殖民影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和地区。然而,这种地理上的划分实际上忽视了部分身处第一世界但同样受到多重压迫的女性群体。莫汉蒂在其著作《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的卷首即对“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提出了质疑,并主张重新定义。她认为,第三世界的范畴不应仅由地理位置来界定,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应纳入考量范围。因此,她所指的“第三世界”包含了美国少数族裔及有色人种在内的群体[7]。莫汉蒂的这一思想拓展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有效提升了第三世界女性的可见度,并对白人中心主义和父权制社会提出了挑战。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奴隶制被废除,黑人在法律上获得了公民权与选举权,但内部殖民主义的影响却远未结束,反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被殖民者实施了一种更加隐蔽的控制。在后殖民批评的经典之作《东方学》中,萨义德借用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hegemony),指出在大众社会中,观念、机构和他人的影响力并非通过直接控制实现,而是通过葛兰西所说的对主流文化形式的积极赞同(consent)来实现[8]。白人统治阶级正是利用这一潜移默化的手段对黑人群体进行文化侵蚀和意识形态操纵,这使得黑人女性的身份建构变得无比艰难。除此之外,父权观念所导致的女性客体化问题并未因种族团结而消失,黑人女性因此同时遭受来自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双重他者。
小说《秀拉》于1973年首次出版,此时距离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尚有五年之遥,距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兴起还有近二十年。然而,莫里森却以其非凡的前瞻性,在这部作品中深刻探讨了黑人女性在种族与性别双重压迫下的生存状态与身份探索,展现了她们在逆境中寻求自我认同与建构的多种可能性。
二、身份建构的不同策略
在小说《秀拉》中,莫里森围绕同名主人公及其好友奈尔的成长经历展开叙述,其间穿插描写赖特和匹斯家族其他女性角色的遭遇。这些女性角色在追求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种族与性别双重压迫所带来的挑战,而这些成为她们必须去应对和解决的问题。
1.盲目与顺从
海伦娜从小便渴望逃离“日落楼”,虽然作者没将海伦娜渴望逃离的原因明确点出,但是结合文本细节,我们不难猜出种族与性别这两个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原因,美国南方的社会风气更为保守,种族问题也较其他地方更为突出。作为一个有着克里奥尔血统的妓女的女儿,这种血统背景在当时的社会中往往被视为边缘化和不受尊重的,海伦娜便生长在这样一个充满种族歧视与性剥削的环境之中。在“日落楼”所在的新奥尔良,海伦娜仅凭自身力量逃离“日落楼”的机会十分渺茫,但好在她懂得借力。于是,海伦娜抓住了威利·赖特这个宝贵的机会,凭借美貌让他帮助自己实现了逃离。
利用性别帮助自己摆脱困境,同样的情节还发生在海伦娜带女儿南下参加葬礼的旅程中。在开往辛辛那提的火车上,海伦娜因意外闯入白人车厢而遭到男列车员的训斥与嘲讽。此情此景,她竟出人意料地露出了谄媚的笑容,“就像刚刚被一脚踢出来的流浪狗在肉铺门口摇着尾巴一样”[9]。没有丝毫羞耻与愤怒,海伦娜自然而然地希望通过讨好和示弱来换得对方的“网开一面”。面对列车员的故意挑衅与歧视,海伦娜再一次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化解了危机,避免陷入更深的麻烦之中。而她之所以会如此熟练地露出笑容,正因为这是在无数次类似遭遇中习得的最佳解决方法。海伦娜深知,除了自己,谁也靠不住,即使是同车厢的黑人士兵,在她被刁难时也都默契地保持了沉默。于是,面对来自白人列车员的言语羞辱,海伦娜不得不牺牲一部分尊严来换取暂时的安宁。
列车越往南深入,成长时经历过的不堪就越多地涌上心头,压得骄傲的海伦娜喘不过气来。所以她才会在返回位于梅德林的家时感到放松,因为她又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可是,她的命运真的掌握在自己手里吗?结婚后,海伦娜被丈夫威利安顿在一座带有长廊和蕾丝窗帘的房子里。当丈夫外出工作时,这栋漂亮的房子便成为海伦娜独享的空间。九年后,女儿奈尔的出生更是为她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海伦娜对自己的婚后生活十分满意,更为自己能够轻易支配丈夫和女儿而沾沾自喜。殊不知,这种“支配”的权力非但没有丝毫实质性用处,更是男权社会赋予她的,这也意味着他们随时能剥夺这种权力。海伦娜自以为能控制丈夫与女儿的能力是虚幻的,但她被家务与琐事消耗的精力却是实实在在的。漂亮的房子成为困住海伦娜的囚笼,在平淡而没有波澜的日子里,女儿的婚礼便成为海伦娜“这么多年来一切存在、思想和行为的顶点”[9]。不难看出,性别给了威利能够在广阔世界中寻找人生价值的自由与资格,但也让海伦娜的梦想只能在一隅之地上寻求。
尽管海伦娜在性别压迫下实现了一种相对自洽的生活状态,但她身份中作为黑人的部分往往受到主流社会的忽视或歧视。“当黑人自我在社会中得不到肯定,有不少黑人便开始在自身塑造一些白人特征,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1]因此,海伦娜便加倍努力地淡化自身的种族特征,试图向白人文化靠拢。她主动放弃说自己的母语——克里奥尔语,转而选择英语作为表达自我的语言。这种对母语的放弃,意味着与原有文化、历史和传统联系的弱化,导致黑人的自我认同和身份归属感逐渐流失,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被边缘化,成为被定义为“他者”的群体[10]。海伦娜还努力摆脱与黑人妇女相关的刻板印象,积极追求白人社会推崇的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她向往中产阶级白人的生活方式:对内,她严守作为一位贤妻的本分,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对外,她将“一头浓密的头发盘成髻,双眼总是像在审视他人的居心一般眯起”,凭借极强的存在感与对自身权威的自信,加入了当地最保守的黑人教会并掌握了权力[9]。
此外,海伦娜的审美观念深受白人中心主义的影响。作为黑人,海伦娜的内心却也有一条“肤色鄙视链”,她看不起比她更黑的汉娜,因此不允许女儿与汉娜家的秀拉来往。她的审美偏好也明显倾向于白人标准,试图通过晾衣夹来夹高女儿扁塌的鼻梁,更是每周都坚持用烧热的梳子为女儿拉直头发。种种迹象表明,海伦娜无法接受,甚至排斥黑人与生俱来的生理特征与文化传统,她为自己比其他同胞更贴近白人的特征而产生一种虚假的优越感。海伦娜对白人生活方式的刻意模仿,以及对自身种族特性的排斥,反映出白人中心主义对黑人女性思想层面的渗透,加大了她们身份建构的难度。
2.挣扎与同盟
在经历了家庭暴力、丈夫出轨后,伊娃被迫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在黑人社会中,男性通常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但他们总是缺乏一定的责任感。波依波依在婚外情暴露后一走了之,丝毫不顾及妻儿日后的生活。于是,在那个毫无预兆地被抛弃的冬天,伊娃全身上下只剩下“一美元六十五美分、五个鸡蛋、三颗甜菜”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9]。如果说黑人身份本就限制了伊娃的就业范围,那么作为母亲的身份也让她在劳动市场上毫无竞争力:照顾孩子使得她无法分出更多的精力与时间。于是,走投无路的伊娃只能铤而走险,通过伤害自己来骗取高额的保险金,用一条腿来换得三个孩子成长的机会。
即使受到种族与性别带来的压迫,伊娃骨子里的野性与反叛决定了她不会像海伦娜一样逆来顺受。断腿的自残行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伊娃对于自己身体的主权,而后她更是主动出击,以一个全新的统治者形象在自己建立的王国里主宰一切。首先,伊娃是木匠路七号那座布局怪异的房子的建造者和掌管者。她居住在房屋的最顶层,像君王般居高临下地掌控着这个空间。房子内部空间的无序和凌乱彰显着她对父权性别规范的对抗和控诉[11]。其次,在挑选领养孩子时,她 “查看他的手腕,研究他的头型,从目光中揣摩着他的秉性”[9],与奴隶主挑选奴隶时的表现别无二致。伊娃更是无视被收养来的孩子们的原本姓名,统一将他们唤作“杜威”,仅以编号来区分。最后,伊娃掌管着生命,同样也控制着死亡。她能在数年前的冬夜用家里仅存的食物挽救奄奄一息的李子,也能在多年后发觉李子萎靡不振、自甘堕落后,亲手放火结束他的生命。
可事实上,伊娃最终仍未建立起一个独立的自我:对丈夫入骨的恨给了伊娃活下去的动力,证明丈夫当初选择之错误、行为之愚蠢构成了伊娃生活的重要意义。“心怀对波依波依的这种恨,她就能坚持下去,只要她想或是需要借助这种恨意来确认或强化自己、保护自己不受日常的侵蚀,便能从中得到安全感、刺激和持续的可能。”[9]因此,伊娃的自我是一种依靠男人建立的间接的自我。但更可悲的是,她不仅没能摆脱父权对她建立独立身份的阻碍,反而将其逻辑内化,成为男性社会的同盟与帮凶。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伊娃督促女租客要尽好照顾丈夫的职责一事上得到印证,还表现在催促秀拉结婚生子、安稳度日上。
3.反抗与疏离
秀拉对于种族主义的反抗与贝尔·胡克斯的策略不谋而合,后者将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付诸实践,并受法侬的影响提出“反凝视”和“顶嘴”策略。“反凝视”即在被白人凝视时凝视回去,表达“我不但要看,并且我的目光要改变现实”的决心[12]。放学后,面对白人男孩的围堵和骚扰,奈尔的胆小怯懦暴露无遗,“直到他们玩腻了,不想再看到奈尔那副害怕无助的面孔才罢休”[9]。但秀拉没有保持沉默,她当着那群男孩的面用小刀划开自己的手指,“双眼直视着他们,口气很平静:‘我对自己都能这么干,你们想想我会对你们怎么干?’”[9] 这种激进的自残方式对那群白人男孩起到了震慑作用,“反凝视”则让秀拉在这场对弈中反客为主,摆脱作为被凝视的客体身份,以平等的姿态向对方传达自己的愤怒与态度。
如果说秀拉对于种族主义的敏感源自身边人的经历以及对他们遭遇的共情,那么她早先被蒙蔽的性别意识的觉醒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所受的教育。小说以年份来命名章节的方式非常值得关注。在“一九二七”章中,秀拉离开梅德林社区外出求学的事被一笔带过。直到下一章节“一九三七”,也就是十年后,秀拉才再一次回到梅德林。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时间为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而秀拉外出求学的时间点正是1927年至1937年。莫里森对于时间点的安排显然别有用意,意在塑造一个与蒙昧的海伦娜、伊娃形成对照的女性形象,探索像秀拉一样处于觉醒状态的黑人女性在当时社会中的身份建构及其选择。
秀拉始终拒绝将自己束缚在婚姻关系中,这令社区里的居民,尤其是其他妇女很不满。在她病入膏肓、穷困潦倒时,奈尔终于说出:“你不能全靠自己。你是个女人,还是个黑种女人,你不能像个男人一样行事,你不能摆出一副独立架势走来走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想扔什么就扔什么。”[9]她们潜意识里认为,作为女性,秀拉就应该和她们一样尽职尽责地扮演父权制社会中的他者,而奈尔的勃然大怒恰恰从反面说明了秀拉没有遵从这些“职责”。受到女性主义的熏陶,见识了婚姻中男女责任分配的不平等,以及女性身上所背负的道德枷锁,秀拉对于男女关系有着自己的思考。因此,即使最终落得孤独死去的结局,她也心甘情愿。
值得一提的是,秀拉对奈尔劝说她找一份糊口的工作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西方女性主义者们提倡妇女们走出家门,参与到社会劳动中去,但正如海克特在《内部殖民主义》中所指出的那样:“优势的族群乐于位于核心,希望通过机构化和永久化这种现存的分层系统来稳定和垄断这种优势,它主要寻求控制社会角色的分配,将优越的位置留给自己的成员。”[12]不同于白人女性所从事的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性工作,留给黑人女性的往往都是些低薪的简单劳动。因此,秀拉宁愿像一棵红杉一样带着尊严地倒下,也不愿在这种工作中消耗自己的生命。
秀拉敏感而清醒,为了避免自己被操纵与控制,她选择从一开始就对周围的一切保持着警惕。没有亲朋、没有羁绊、没有信仰,秀拉变成一叶浮萍。她的自我发现之旅过于激进与冒险,因此到最后,她的发现也仅仅是一次个体化的自我发现[6]。
三、身份建构的可行之道
如前文所述,海伦娜、伊娃、秀拉进行身份建构的尝试均不理想。海伦娜为其因女性身份而获得的不值一提的便利感到沾沾自喜,同时自豪于自己更为白人化的审美与价值观。但可悲的是,她并未摆脱从属性的他者地位。海伦娜丝毫没有意识到,正是性别的不平等使她不得不讨好占强势地位的男性,也正是种族带来的压迫使得她摒弃了传统的黑人审美与生活方式。同样,伊娃的身份建构在这两座大山的阻碍下也走向了歧途。同为种族与性别压迫下的受害者,伊娃却将这套权力运行逻辑内化,摇身一变成为压迫者的同盟。但尽管建立了如此权威,她的自我始终建立在对丈夫的恨意之上,是一种不牢靠的、二手的自我。秀拉的身份建构之路较两位前辈来说则更为激进。她清楚地意识到种族和性别对于黑人女性的深远影响,也见过了太多由此引发的悲剧,因此选择从一开始就对周围事物保持警惕,拒绝所有联系与羁绊。诚然,这种极端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反抗压迫的作用,但同时它也消解了生活本身的意义。那么,对于黑人女性来说,究竟怎样的身份建构之路才是可行的呢?莫里森通过塑造奈尔这样一个人物给出了她的答案——姐妹情谊。
姐妹情谊原指所有女性团结起来反抗父权制。但是随着女性主义的不断发展,姐妹情谊因忽略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而逐渐引起了少数族裔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的质疑。贝尔·胡克斯认为,姐妹情谊是由资产阶级白人妇女所定义的概念,她们坚信全世界的女性都面临着共同的压迫。但是,种族、阶级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这种“共同压迫”的概念站不住脚。事实上,女性并不需要以消除差异为代价来实现团结,通过共同的利益、信仰、对多样性的接纳等依旧可以实现姐妹间的团结[13]。因此,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性,但随着更多的黑人女作家对姐妹情谊内涵的丰富,它依然是女性在面对多重压迫时进行身份建构的有效途径。
对于黑人女性来说,双重维度上的“他者”身份加深了她们对于性别、种族和自身的理解,促进了她们之间独特的姐妹情谊。在小说中,秀拉与奈尔之间亲密友谊的产生,不仅是因为她们共同生活在父权制的压迫下,还因为她们身上都背负着来自种族主义的重担。“她们在多年以前就已发现自己既不是白人也不是男人,一切自由和成功都与她们无关,她们便着手把自己创造成另一种存在。她们的相遇是幸运的,这让她们得以依靠彼此而成长。”[9]虽然奈尔与秀拉的家庭环境截然相反,性格也不尽相同,但是同为黑人女性的命运却把她们紧紧联结在了一起,让她们在对方的陪伴下更好地认识自己。“对她们俩中其中一个的赞美就是对另一个的褒奖,而对一个人不逊也就是对另一个的挑衅。”[9]最后,这两个女孩之间似乎没有了任何差别,她们仿佛合而为一。
姐妹情谊促进了奈尔与秀拉主体意识的觉醒,而更重要的是,当奈尔的身份建构之路走向歧途时,正是与秀拉的姐妹情谊将她重新拉回正轨。随着结婚生子和秀拉的离开,奈尔曾经亮起的微弱的自我的火苗逐渐熄灭,她开始把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寄托于男性身上。“在裘德提到她的颈项之前,她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而在裘德把她的微笑看作一个小小的奇迹之前,她也从未意识到除了咧开嘴唇之外,它还意味着什么。”[9]甚至在被丈夫抛弃后,奈尔便认为自己的女性器官再也没有任何用处了,仿佛它们仅仅是为了男性而存在。除了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贬损外,奈尔更是默认了黑人女性生来就应处于社会底层的观念。小说情节发展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奈尔曾经短暂觉醒过的自我被彻底摧毁了。但即使在秀拉去世多年后,姐妹情谊依旧为奈尔的身份建构提供了力量。在一次去养老院的探望中,伊娃的一番话使奈尔重新回想起与秀拉间的情谊,也让她猛然忆起和秀拉在一起时自己的大胆、自信与叛逆。在小说的结尾,奈尔尘封已久的主体意识开始苏醒,而巧合的是,这段情节出现在书中的“一九六五”章,这也正是历史上妇女解放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一年。
四、结语
性别与种族是黑人女性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两大阻碍,并且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将她们构成双重意义上的“他者”。海伦娜对所遭受的性别和种族压迫浑然不觉,陶醉于父权制为她划定的狭小天地,并为能在其中大展拳脚以及拥有比自己同胞更白人化的生活方式而感到心满意足;伊娃将权力运行逻辑内化,成为压迫者与父权制的同盟,但她也依旧未能形成独立的主体意识,对波依波依的仇恨成为她活下去的主要动力;秀拉清醒、警惕,具有极强的主体意识与叛逆精神,然而激进的反抗方式也让她变得与一切疏离,最终失去了生活的意义。通过对黑人女性艰难的身份建构之路的书写,莫里森对白人中心主义及父权制对黑人女性肉体与精神的侵害进行了批判,表达了对弱势边缘群体的关怀,同时点明了姐妹情谊在黑人女性身份建构中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 王守仁,吴新云. 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Bischoff J.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Studies in Thwarted Sensitivity[J].Studies in Black Literature,1975(3).
[3] Smith B.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J].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Quarterly,1979(2).
[4] 林树明.性别意识与族群政治的复杂纠葛: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2(3).
[5] 李小林.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J].妇女研究论丛,2003(1).
[6] 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 Mohanty C T.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
[8] 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9] 莫里森.秀拉[M].胡允恒,译.海南:南海出版社,2014.
[10] 罗钢,裴亚莉.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1).
[11] 赵辉辉,黄依霞.空间视域中黑人女性的身份建构——以托尼·莫里森的《秀拉》为例[J].外语教学,2020(2).
[12]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3] Hooks B.Sisterhood: Political solidarity between women[J]. Feminist Review,1986(1).
(责任编辑" 余"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