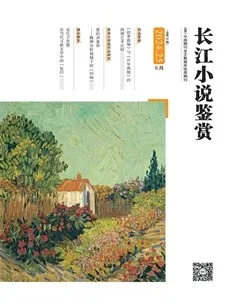伍绮诗《无声告白》中的流动性研究
[摘要]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的小说《无声告白》以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为故事背景,通过揭示中美跨族裔家庭的悲剧成因,再现美国社会中族裔和性别他者流动能力差、流动受限的生存困境。本文运用流动性理论视角,从性别和种族的双重维度分析《无声告白》中的流动性政治书写,进而揭示人物流动受限背后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成因。华裔父亲詹姆斯及混血孩子都因种族歧视和身份危机主动或被动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处于不动的状态;而白人母亲玛丽琳深受婚姻、子女和社会的禁锢而丧失空间和身份流动性。此外,女儿莉迪亚自杀的悲剧同样与父母流动受限的处境休戚相关。
[关键词]伍绮诗" "《无声告白》" "流动性
[中图分类号] I06" "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25-0052-04
蒂姆·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指出,“流动性是一种资源,不同群体的人们获得流动性的渠道和权利也判然有别”[1],也就是说,不同群体的流动能力、可流动的范围和流动性资源的获取等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深受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影响,呈现为“流动性政治”(politics of mobility)。新生代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Celeste Ng,1980—)的处女作《无声告白》(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2014)以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为故事背景,通过揭示中美跨族裔家庭的悲剧成因,再现了美国社会中族裔和性别他者流动性受限的生存困境。本文运用流动性理论视角,从性别和种族的双重维度分析《无声告白》中的流动性政治书写,揭示人物流动受限背后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成因。
一、从边缘到中心——祛魅族裔流动性神话
《无声告白》讲述了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民权运动前后的华裔流动境遇。《排华法案》等歧视性法案废除后,华裔在美国的地理生存空间得到较大拓展,在美国本土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小说中的华裔詹姆斯似乎在这乐观的流动现状中实现了“美国梦”,不仅拥有大学终身教职,还迎娶了白人妻子玛丽琳,但看似完美的生活因大女儿莉迪亚自杀戛然而止。小说在倒叙与插叙中一步步解开莉迪亚的死亡谜团,华裔真实的生存境遇也逐渐公之于众。实际上,无论是詹姆斯还是保留着华裔特征的混血儿,都始终无法实现真正的流动自由,来自白人的目光强化了空间区隔和种族秩序,他们一家被动乃至主动地保持静止,直至不动(immobility)。
小说中,华裔在主流社会空间中饱受种族歧视和民族拒斥,于是主动隔离,导致流动自由实质上的缺失。詹姆斯幻想着白人妻子与他结婚就意味着“美利坚这个国家对他敞开了怀抱”[2],但现实中,他们婚后从不上教堂做礼拜,大多时间都待在家,外出频率极低。在儿子内斯眼中,“他的父母既不出门交际,也不在家请客,没有办过派对,也没有朋友”[2]。而大女儿莉迪亚和内斯同样如此,日常在学校与家庭两点一线固定、重复地流动,暑假除了上暑假班补习,更是不外出,“整天都待在家里”[2]。克里斯维尔指出,可流动的范围、流动体验、流动频率都是流动性政治的体现,流动背后体现着意识形态。小说中族裔空间流动性被削弱,实际上是由于以白人为中心的种族秩序所带来的空间区隔与边界,一张亚裔皮囊已经决定着他们的流动境遇。在《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White Masks,1967)一书中,弗兰西·法农(Frantz Fanon)指出,在白人的凝视中,黑人意识到了自己的黑人性,“黑人不能获得显现的主体性,而是被特征化,只是一个‘黑人’而从来都不是‘人’”[3]。小说中同样如此,“你会发现,走廊对面的女孩在看你,药剂师盯着你,收银员也在盯着你,你这才意识到自己在他们眼中的形象,格格不入”[2]。当进入主流社会空间时,白人通过确认黑头发和黑眼睛的外貌,将刻板印象赋予詹姆斯一家,此时他们在美国出生、成长的事实,纯正的口音都已经没有意义。
詹姆斯渴望融入社会,于是试图逃避叩问自身与外界的关系,主动缩小流动范围。法兹指出,种族化凝视最终被族裔内化,成为创伤并约束着身体的活动,“空间是显现种族差异最重要的能指:在殖民统治下,移动的自由(心理、社会和物理)成了白人的特权……黑人被剥夺了获得主体性的机会,永远被封印进了客体化世界”[4]。开学第一天,面对白人同学审视异类的目光和随之到来的嘲笑,“你的眼睛怎么了?”詹姆斯第一次意识到“这种时候自己应该表现得难为情才行”,于是“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时,他吸取经验,立即红了脸”[2]。即使多年之后,从劳埃德学院到哈佛,再到入职的米德伍德学院,詹姆斯依旧对来自白人的他者化凝视高度警觉,这让詹姆斯感到焦虑,“提醒你与环境的格格不入……好比动物园的动物趴在笼子里,拼命忽略围观的游客”[2]。这个跨族裔家庭唯一一次外出度假的时候,“每到一家餐馆,女招待都会盯着她父亲,然后看看她母亲,接着是她、内斯和汉娜……莉迪亚那时候虽小,但知道,他们再也不会出来旅游了,自那时起她父亲都会在暑假班教课,这是为了避免带着全家人出门度假”[2]。即使婚后,詹姆斯在面对白人的目光时,依旧感到压抑,不得已再次确认自己的华人身份,于是他主动减少流动频率,通过隔离在家来逃避自己无法融入美国的事实。
过去的詹姆斯通过否定华人身份来界定自我,他厌弃自己的民族文化,努力摆脱族裔特征。但莉迪亚死亡的真相使他被迫承认自己游离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境遇,承认自己融入美国的梦想彻底破灭。于是他在与华人助教路易莎的婚外情中麻痹自己,在长时间开车兜风后,“他会不由自主地去路易莎的公寓”[2]。路易莎的家,不仅让他可以暂时逃离家庭,忘却丧女的悲痛与自责,更使他得以追回族裔身份,再获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此,路易莎的家扮演着与美国主流社会相隔离开来的“飞地”角色。詹姆斯的流动境遇实际上重演了20世纪30年代华裔因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种族歧视等原因选择自我隔离,聚居于唐人街的境遇。华人的外貌特征似乎已决定了他们的流动现状,他们很难突破自身的种族身份所“规定”的流动范围。
二、跨越性别空间界分——女性流动性之殇
《无声告白》打破常规线性叙事方式,“全文采取多视角、多叙事、多层套叠的非线性多重叙事策略”[5]。但如果以时间顺序来梳理小说的情节线,可以发现母亲玛丽琳驾车离家是触发一系列事件的多米诺骨牌,也是一家人悲剧的开端。1965年圣诞节,母亲因梦想离家出走9个星期,这给5岁的莉迪亚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2]。对于莉迪亚的死亡,母亲玛丽琳自然难以推脱其责任。但如果将小说置于流动性的理论视角下,会发现玛丽琳对莉迪亚高标准的培养,并非来自她专制的性格,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对女性压迫下的身不由己。通过几次离家的流动,玛丽琳先是感知到实现自我的可能,又最终意识到自己的梦想遥不可及,莉迪亚对数学表现出的兴趣是使她免于崩溃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伍绮诗对玛丽琳几次流动的书写体现出女性打破流动受限境遇的困难,反映了她对女性生存境况的担忧与反思。
玛丽琳的生活看似安稳,实际上体现出女性受婚姻、子女、社会角色的禁锢,不得不囿于家庭空间,从而丧失流动性的残酷现实。玛丽琳在美国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感召下,勇敢追求医生的职业梦想,并成功进入哈佛攻读医学专业,但却因丈夫和即将到来的孩子不得不放弃学业,成为家庭主妇。当两个孩子开始上学时,她试图重回学校,却受到来自丈夫和社会的双重拒斥。即使两个孩子出生后,丈夫詹姆斯也不同意玛丽琳工作或继续完成学业,“他知道别人会怎么说:他挣得不够多——他妻子不得不出去找工作”[2]。此外,外界社会也提醒她作为母亲的身份与责任,强调所谓的性别规范和家庭分工,将她隔离在公共区域之外。当她向丈夫的同事争取工作的机会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如果你的丈夫不介意的话,那就可以”[2],“我不知道你是认真的,因为你还有孩子和丈夫要照顾”[2]。道林·马西(Doreen Massey)指出,“对女性流动性的控制,包括身份流动与空间流动,在多重文化语境下都是维持女性从属地位的重要方式。”[6]在父权制社会中,对女性流动的限制加强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乃至社会中的从属地位,玛丽琳作为家庭和社会中的双重他者,被牢牢限定在家庭主妇的身份中,空间流动性也因此削弱,仅为了处理家庭事务,在家庭、购物地点、学校等女性日常实践空间之间来回流动,与外界鲜有往来。
而家庭主妇角色对玛丽琳流动性的限制直到她驾车离家才被打破。小说中对玛丽琳仅有的两次驾车流动经历的描写富有隐喻意义,象征着她对性别空间和角色束缚的僭越。通过流动带来的空间变化,玛丽琳得以映照母亲和伍尔夫医生两位“他者”,进而反思自己当下的身份和生活现状,重新审视过去的选择,最后决定重拾自己的医生梦。第一次离家是玛丽琳回弗吉尼亚州处理母亲的葬礼。母亲多丽丝代表着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的传统性别规范,玛丽琳在收拾母亲的遗物时,发现除了厨房里母亲在《贝蒂科洛克烹饪书》上的铅笔划痕,“她生命的印迹无处可寻”[2]。迈克·克朗提道:“家可以被看作有性别区分的文化地理景观的一部分,家庭空间内部也隐含着性别特征,女性与厨房被紧紧捆绑在一起。”[7]通过映照母亲,玛丽琳“如梦如醒,似乎有人在她耳边叫喊:你母亲死了,最终,唯一值得纪念的就是她烹调的食物……决不,她对自己发誓,我决不能活得像她那样”[2]。汽车的另一个目的地医院,则代表着玛丽琳正式重拾过去的梦想。第二天她再次开车离家,却不自觉地开到了医院。她“放下车窗,绕着湖边转圈,一圈,两圈……她茫然地开着车,横穿米德伍德,经过大学、杂货店、旱冰场,等她发现自己转进了医院的停车场,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打算到这里来”[2]。医生梦想一直存在于玛丽琳心中,汽车作为身体的延伸,其去向反映着玛丽琳的潜意识。玛丽琳发奋读书,立志当一名女医生,而这并非易事。“二战后女性就业人数成倍增长,但是商业、法律、医生等行业女性很难涉足。”[8]正因如此,玛丽琳虽开车到了医院,但一开始并未抱有期望。但之后她在医院见到了女医生伍尔夫,感知到社会歧视的缓解“超乎她的想象”,感知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我也能做到”[2]。汽车的流动性使得玛丽琳暂时逃脱了家庭空间的束缚,到达的两个站点——母亲家和医院,象征着母亲和医生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她在观照他者时,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与境遇,最终做出选择。身体的流动带来思想的流动,给予她认知自己以及反抗的力量,这是过去在时空疆界很明确的情景下,即一直困在家庭空间时所无法达成的事。
重回校园搬离家庭意味着玛丽琳从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流动,然而玛丽琳在选择逐梦后仍没能彻底逃出家庭的禁锢,心理上被家人牢牢抓住,极大的物理自由与无法自由的内心形成鲜明对比。因过去8年的家庭生活,玛丽琳不知不觉把子女和丈夫的需求内在化,把家庭生活和关系视为自我责任和思想寄居之处,几乎丧失自我意识。玛丽琳终于重新踏足校园,租住在校园附近的小公寓里,但在这离家的9个星期内,对孩子和丈夫的挂念却无时无刻不让她备受煎熬。这种情感甚至体现到身体反应上,“感到体内有一种尖锐的疼痛……她突然觉得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不应该远离家人跑到这里来”[2]。看着课本,她甚至想念起家务劳动,“想起煮鸡蛋、单面煎的荷包蛋和炒鸡蛋” [2]。但如果回家便无法完成学业,将再次面对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占据全部时间的生活,“晚饭需要做,内斯需要喂饱,莉迪亚需要有人陪着玩,她哪有工夫学习?”[2] 9个星期后,又一个新生命的意外到来,成了击垮玛丽琳心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她终于承认,自己没有勇气再撇下他们不管”[2]。
玛丽琳最终被丈夫詹姆斯接回家,离家时前进的极大自由,与再回家时目标的迷失形成鲜明对比,家庭对玛丽琳的身份流动进行了强有力的捆绑。玛丽琳为逃离家宅空间和主妇角色的多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心灰意冷的玛丽琳回家见到女儿,女儿的一番承诺才让她燃起希望,于是将她的梦想寄托在女儿身上,最终成为女儿自杀的重要导火索。悲剧与其说是专制自私的妈妈所导致,倒不如说是男权社会下,女性地理、社会和心理流动受限的绝境所共同促成的,社会看似给予女性更多自由,但实际上大多数个体依旧困于母亲身份中,无法实现流动。
三、结语
伍绮诗在《无声告白》中通过揭示跨族裔家庭的悲剧成因,再现了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中华裔和女性流动能力差,流动受限的社会境遇。本文在分析小说人物流动受限背后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成因后发现,华裔父亲詹姆斯看似实现了美国梦,但实际上却因其族裔身份深陷他者的凝视,遭受隐形社会边界的排斥,无法实现空间流动自由和从边缘到中心的身份流动;白人母亲玛丽琳深受来自婚姻、子女和社会的禁锢,最终未能成功逃脱传统性别角色和家庭牢笼,只能再次重演家庭主妇的流动困境。詹姆斯和玛丽琳都因难以摆脱的流动受限困境,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大女儿莉迪亚身上并步步紧逼,父母双方的期待最终酿成莉迪亚在重压之下自杀的悲剧。小说的流动性政治书写凸显了作者对女性和种族问题的关怀,体现了作者对更为平等正义的空间的追求。
参考文献
[1] Cresswell T.Towards a Politics of Mobility[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2010(28).
[2] 伍绮诗.无声告白[M].孙璐,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3] Frantz F.Black Skin,White Masks[M].Charles Lam Markmann,Trans.New York:Grove Press,1967.
[4] Diana F.Interior Colonies+Colonial History and Racism-Fanon,Frantz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fication.[J]Diacritics-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1994(24).
[5] 汤琳.天花板上的鞋印——试论《无声告白》叙事伦理建构[J].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2020,37(3).
[6] Doreen M.Space.Place and Gender[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7] 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 朱刚.20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 刘英.女性与流动性:美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书写[J].妇女研究论丛,2014(6).
(特约编辑" 张" "帆)
——基于三元VAR-GARCH-BEEK模型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