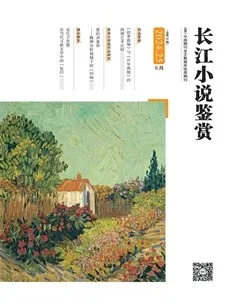多余人和幻想家
[摘要]《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多余人”奥涅金与《白夜》中的男主角“幻想家”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两类重要形象。其二者的外在特性相似,但内在逻辑的建构却有着鲜明差异:“多余人”以排斥和逃离面对现实社会,将爱情视作排遣苦闷的工具,在个体与群体矛盾中消极搁置问题;而“幻想家”则在面对社会时犹豫和徘徊,将爱情视作双方走向幸福的途径,既坚持个人追求也对群体的利益与发展予以重视。
[关键词]《叶甫盖尼·奥涅金》" 《白夜》" 多余人" "幻想家
[中图分类号] I06" "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25-0031-04
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为19世纪的俄国著名作家,都在各自的创作生涯中创造出大量贴近现实且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为世界文学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1]中的“多余人”奥涅金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2]中的男主角“幻想家”在外在呈现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彼此都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都对现实世界保持一定的疏离关系,都为生活现状感到忧愁郁闷。但在人物形象建构的内在逻辑上,两类人物作为代表各自阶层的典型形象,在面对社会环境时所采取的行动,在对待爱情时的具体态度,在个体与群体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等方面都存在显著且根本的差异。本文将从叶甫盖尼·奥涅金以及《白夜》男主角的差异入手,对多余人以及幻想家两类人物形象进行比较研究。
一、逃离之人与徘徊之人
普希金塑造的奥涅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白夜》男主角,二人都在与现实世界的疏离中不可避免地承受着精神上的苦闷与忧郁,因此在外在呈现上不约而同地表现出较为相似的孤独气质。其人物共性一定程度上与俄罗斯人独特的民族性格有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他们只可能选择矛盾的两个极端之一,对事物的选择与评价只能是好或坏。他们性格中这种特有的矛盾性,被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伊林、索洛维耶夫称为‘二律背反’。”[3]而在两位男主人公的具体处境中,顺从其民族天性的“非此即彼”受到更为现实的“非此非彼”的冲击,从而使二者陷入苦闷与忧郁。但二者表征的类同并不意味着其形象的内在逻辑也类同,对此需要从这两类人物所面对的不同社会环境,及其对该环境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入手。此外,二者各自所处的不同阶层,以及奥涅金的逃离与《白夜》男主角的徘徊态度,都对建构其孤独气质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将这两种状态概括为逃离之人和徘徊之人。
19世纪初,在社会变革与政治改革的催动下,俄国的贵族阶层内部不断分化:部分贵族逐渐觉醒并投身于反抗封建专制和农奴制度的革命活动之中;与此同时,也有部分贵族继续通过依附旧思想与旧标准来寻求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奥涅金作为其中的一名贵族知识青年,受到西欧启蒙思想和进步思潮的熏陶,试图做出一些改变,但也仅限于浅尝辄止。在二律背反的张扬民族个性与圣愚文化盛行的俄国异质土壤,以贵族的落后身份参与到政治改革与农奴解放的运动中反倒是一种打破传统,但符合民族秉性的选择,但当社会与时代的重担真正放置于奥涅金的肩膀上时,其周遭声色犬马的环境,以及其软弱且摇摆的性格,构成了阻挠其实现理想的双重障碍。受此影响,奥涅金最终成为一个深知个人使命,却难以将之付诸具体行动的矛盾个体,他既试图逃离腐朽的旧贵族式生活,同时也在逃离时代赋予他的使命。可以说奥涅金本人“不是一个恶棍,不是一个放荡淫乱的人,虽然同时也完全不是一个道德的英雄”[4],而是一个逃离之人。
自我定位与现实基础相矛盾,民族秉性与个人选择相矛盾,这种混乱状况直接导致奥涅金难以融入其身边的各个圈层。因此即使他与周围的其他人一样同为贵族,但实际上却在名为贵族的圈子中找不到属于他自己的位置,这也导致其始终沉浸在空虚、孤独、无助的悲观情绪中不能自已。其身份与现实之间产生了深刻且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永恒矛盾”[5],奥涅金因此陷入一种难以圆融自洽个人存在的“精神危机”[6],他以多余人的形象排斥着一整个贵族圈层,但同时也在事实上被各个贵族圈层排斥。在这双向的排斥中,奥涅金不可避免地对其所处的上层社会产生逃离倾向,并由此生成无法掩抑的割裂与疏离情绪,最终以一种多余人的形象将其内在孤独与忧郁呈现在人物外表之上。
而《白夜》男主角则与奥涅金不同,其虽然也处在农奴制解体,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展的历史时期,但其与奥涅金在历史浪潮中的位置却大有不同。在沙皇政府通过专制统治自上而下打压国内底层资本主义萌芽时,底层平民与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激化,原本沉默的社会底层平民逐渐被推上历史舞台,并开始发声,《白夜》男主角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社会变革仍然由贵族所主导,因而,如果说奥涅金的贵族身份使之生来便进入变革社会的行列,并且使之在面对是否将社会变革的理想付诸实践的问题时,仍然保有介入或逃离的选择权,那么作为市井平民的《白夜》男主角,则是以一种缺乏选择权的姿态,被时代洪流不由分说地裹挟着进入这一社会矛盾的浪潮之中。对于《白夜》男主角这样一个有知识修养的小人物而言,其所面对的问题在于是否要选择顺应时代,融入由他者构建的新的社会环境之中。
《白夜》男主角对世界有着美好的憧憬与幻想,因此他对市侩且低俗的市民文化与底层现实深感厌恶。在个人幻想与社会现实的强烈反差中,他选择沉浸于个人幻想的温柔乡,拒绝与其他人来往的同时也被其他人所抛弃。但同时也要注意到,他的弃世并不彻底,其内心深处仍然保有着与社会融合的渴望,正如《白夜》的开头,男主人公发现城市中的人都开始离开城市,开始前往各自的家族聚居地,其内心也不免涌出孤独无援的情绪。由此可见,他并非完全对现实世界感到绝望,相反,他始终期待着现实世界有朝一日能和他所幻想的一般美满和谐,并且他也幻想着融入一个能够接纳他的道德风气良好、人民追求高雅的新社会。但现实的黑暗与低俗却使他的期待一次次落空,这导致其始终徘徊于疏离与融入之间,取舍不定、犹豫不决,最终成为所谓的徘徊之人,陷入悲观、孤独的境地,所幸最终在与温柔优雅的娜斯金卡的爱情幻想之中得到救赎。
二、自我的爱与无我的爱
爱情是人类亘古永恒的主题,也是众多创作者的书写对象。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别在《叶甫盖尼·奥涅金》和《白夜》两部作品里对爱情主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呈现与探讨,两位男主角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一定程度上延续他们逃离之人与徘徊之人的形象差异——前者将爱情视作逃离之路中抚慰并弥补其空虚灵魂的工具,后者则将徘徊情绪摆在一边,将爱情看作人类通往幸福和希望的路径,是双方彼此都能从中获得升华的一种力量。
奥涅金与达吉雅娜的爱情可谓跌宕起伏。奥涅金起初被达吉雅娜众多美好的道德品质所吸引,但找了众多借口拒绝其爱意。而在多年后遇到身为人妻的达吉雅娜时,为了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和孤独,他选择将自己的灵魂重新寄托在她身上,但最终达吉雅娜恪守了自己高贵的道德准绳,拒绝了奥涅金自私且无理的请求。在这段失败且曲折的爱情中,奥涅金始终是一个人自说自话,他所希望得到的只是自我的解脱和宽慰,而并非建立起一种双向平等的爱情关系——当他为达吉雅娜动情并面对她的表白时,他只愿独自享受脑海中的爱情虚像,而不愿在现实中与达吉雅娜携手承担起爱情的责任;当他难以排遣孤独,疯狂追求达吉雅娜时,也并未考虑对方会因此受到道德与感情上的双重煎熬。其行为无疑是自私且野蛮的,爱情对于他而言更像是面向自身的私人工具。奥涅金从中汲取个人生存所必需的养料,却不愿与他人分享,并对试图进入其自我世界的他者持不合理的戒备心与不信任感,从而招致这一段悲剧。可以说,奥涅金的爱情之所以以悲剧收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爱情这种本该属于两个人的双向关系,进行了过于自我的单方面误读。
而《白夜》主人公则与奥涅金不同,他对待爱情的态度并没有陷入自说自话的怪圈,也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徘徊不前,而是以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无我态度去面对人际关系的难题。《白夜》男主角是一个常常沉浸于个人幻想之中的幻想家,自始至终对于社会制度、道德秩序等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唯独对娜斯金卡的爱没有止步于幻想的、不现实的爱,而是从徘徊状态中脱离出来,由美好的幻想之爱落地成为自我牺牲、成全他者的无我之爱。幻想之爱无疑也是偏向于满足幻想者个人的情感需求的自我之爱,爱情中的另一方将不可避免在虚无的空想中被当作幻想主体的附庸,这与奥涅金的自我之爱可以说如出一辙。但《白夜》男主角最终转向的无我之爱,是一种“不排斥异己,也不在对方身上寻找自我”[7]的爱,它将被爱者的需求与情感也包含到爱情关系成立的考虑范畴之中,当爱人者发现自我的牺牲将使得被爱者获得更为幸福的生活时,其愿意以克制个人私欲、折损个人追求爱情的权利等方式来平衡爱人者与被爱者之间双向的情感,这自然是一种无私的爱。可以说,他的爱情历程展现出的是“全世界任何文化背景的人们都能共同理解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伟大的人类情感”[7]。《白夜》男主角透过爱情思考的并非只在于个人的悲喜得失,而是更为广阔的人类交际与发展问题,当爱人者愿意为被爱者的幸福而自我牺牲,那么局限于二人之间甚至是只局限于自我的小爱就将蜕变为一种超越个体情欲的大爱,《白夜》男主角与娜斯金卡双方在这段无我的爱情中获得的并不是来自爱人者或被爱者单方面的倾轧与束缚,而是双方精神上的满足与升华,与此同时只存在于幻想家脑海中的美好世界,也一定程度在现实世界的阴霾中得以复现。
三、个体与群体矛盾中心的二人
在以多余人以及幻想家这两类人物特性为引,对奥涅金与《白夜》男主角展开聚焦于个人特质的比较研究的同时,还需要将研究视角延伸至两位主角与各自文本的内生世界之间的关系,即二者不同的个人特质将使之以何种不同的方式来面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二者将如何处理个人与群体相处所面临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如智量先生指出,作为多余人的奥涅金是一个“既不愿意坚持个人主义又不能为群体献身的人”[8],奥涅金在自我认识陷入混乱的同时,也在通过一种消极且自我封闭的措施来面对其个人之外的世界整体,并对个人与群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采取一种搁置不论的态度。作为幻想家的《白夜》男主角与奥涅金正好相反,他是一个“既想坚持个人主义,又自愿为群体献身的人”。下文将由此入手,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
奥涅金对其所处社会环境的症结有着清晰且全面的认识,其厌恶部分传统贵族通过阶级特权,对身处社会底层的农奴进行非人道的肆意压迫。他虽然认识到这种阶级压迫不合理,但却不能下定决心与他所同情的广大群众站在一起,这使得其对自我的认识陷入一种难以处理的混乱,他想要为所有人争取利益,但最终谁的利益都争取不到。从本质上看,奥涅金不愿意以牺牲个人权利的方式来换取大众的利益,他在精神上脱离了其所处的贵族阶层,但在现实实践上并没有完全融入社会解放的时代浪潮。在时代的矛盾中,奥涅金既缺乏恬不知耻、安于现状的心理抗压能力,也同样缺乏毅然决然选择正确道路的勇气与膂力,他难以在自己的生命中找到“解决根本人性矛盾的办法和立场”[8],同时也对寻求这种办法与立场并不积极,这使得他在直面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矛盾时,只能以一个多余人的自视,悬浮在明哲保身与积极改革的两极之间,以一种搁置不论的消极态度面对各种问题,饱尝被精神追求与现实困境撕裂的孤独与痛苦。在此基础之上,反观奥涅金面对爱情的态度,实际上都与其难以解决个人与群体矛盾的困境有关,他在对生命困境的消极逃避中,陷入无目的的自我放逐,“多余人”的悲剧也就因此而产生。
而《白夜》男主角则与奥涅金恰恰相反,当处于个体与群体的矛盾中心时,他既没有对维护并发展自我有所犹豫和怀疑,同时也愿意以牺牲个人的方式使群体获得更好的发展。《白夜》男主角作为幻想家,之所以在现实中不以自己“卑微的地位而心惊胆战,更不去逢迎什么长官的意志”[9],是因为他在个人长期的幻想之中构建出了一个高尚且伟岸的自己。在其幻想中,他不容置疑地占据社会权力的中心,并在其中受到他人的尊重与讨好,他通过这种带有精神胜利的形式进入到社会环境与时代潮流中去,这是其内心自信空想的真实写照,也是其个人发展的迫切渴望。在自我认识上,《白夜》男主角始终对于其自身的发展路径充满自尊与自信,他一直朝着积极的、发展的方向进行幻想,并在幻想中不断建构自身。而当这样一个精神自足的个体被放置于群体之中,并因此面临矛盾与抉择时——即他意识到娜斯金卡相较于他更爱房客时——他又能自愿从暧昧温情的男女之爱的幻想中脱离出来,以牺牲个人成全房客与娜斯金卡的方式来做出这一矛盾的最优解,某种意义上,当《白夜》男主角决定自我牺牲的一刻,幻想中的美好品格与现实中的高尚行为逐渐接轨,存在于幻想中的他与现实群体中的他实现了最终的统一,这种牺牲无疑是崇高且震撼人心的,《白夜》男主角也在为群体的奉献中顺利化解了个体与群体的矛盾,并且将一场失败的爱情转化为自我精神和生命的洗礼与升华。
四、结语
俄罗斯别具风格的异质土壤与鲜明独特的民族气质映射在其作家的创作之中,塑造了诸如“多余人”“幻想家”等矛盾且细腻的人物。二者生命的苦闷与困惑来源于文化路径与个人选择的冲突,社会理想与具象现实的背离。透过这两类人物,人们需要在穿越时间、超越阶级、跨越民族的视角下不断叩问、审视自身,从而寻找一种超越人类自我的可能。本文作比的二人虽然都是同一时期具有一定道德修养、知识素养的男性青年,但二者以多余人和幻想家这两种不同人物形象呈现,其中缘由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参考文献
[1]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M].智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2]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M].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3] 郭鸿伟.俄罗斯民族性格“二律背反”的语言文化学阐释[D].大连:大连外国语学院,2011.
[4] 别林斯基,王智量.论《叶甫盖尼·奥涅金》[J].文艺理论研究,1980(1).
[5] 智量.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形象体系与创作方法[J].外国文学评论,1990(3).
[6] 吴平春.论“多余人”叶甫盖尼·奥涅金[J].文学教育(上),2019(11).
[7] 赵宁.从《白夜》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终极追求[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12(2).
[8] 智量.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形象体系与创作方法[J].外国文学评论,1990(3).
[9] 王庚年.简论《白夜》[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3).
(特约编辑" 张"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