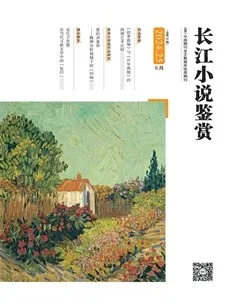论《李双双小传》中的女性“称谓语”
[摘要]人物本身的“称谓语”作为修辞元素的身份符号,放在特定的语境和社会环境下具有深厚的意蕴。《李双双小传》中人物对主人公李双双的“称谓语”是小说细节呈现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这些对李双双的“称谓语”整体特征为从“代称”到“自称”,从“无名化”到“姓名化”。李双双“称谓语”隐晦但又显著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集体劳作中女性的参与度和话语的勇敢表达,而且也是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的重要表征。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 李双双" "称谓语" "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I06" "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25-0015-04
《李双双小传》是著名作家李准的代表小说,于1960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因小说描写的内容和典型人物而在之后产生了轰动的影响,曾被称为“新中国妇女的颂歌”。小说以李双双这一典型的农村女性作为重点人物,对特定时代背景下妇女参与集体劳动的重大事项着力描述。李双双作为集体中的个人与性别中的女性获得了社会的讨论与认可,也意味着“广大的劳动人民,尤其是劳动妇女,从一切旧习惯旧影响的羁绊中获得了真正的解放”,而李双双的形象则概述了农村劳动妇女“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当中的具有代表性的生活道路和生活命运”[1]。这篇小说表明了李准创作风格的转变,展现了李准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人性、爱情、家庭以及时代的思考。这些内容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解读。比如,学界对李准和“李双双”的阐释与再阐释十分丰富,其中涉及比较多的就是女性解放的议题,虽然女性解放的相关论述是一项世界性的论题,但“在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实践走的却是与西方女权/女性主义完全不同的历史路径”[2]。《李双双小传》体现出来的女性解放意识与典型的事件在整个20世纪中国女性解放道路中是独特的一支。其中,比较隐晦的是小说对李双双这一女性人物的称谓及其变化。
一、称谓语:作为修辞元素的身份符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与国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础单位,承载着传统文化中五伦理念的维系和传承。通过遵守伦理规范,人们能够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秩序,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繁荣。而称谓的语言系统纷繁复杂且意蕴无穷,特别是汉语的亲属称谓,内部称谓语多,彼此区别精细,关系复杂。据刘超班先生的研究,汉语现代标准亲属称谓语共363个,其中父系245个,母系65个,妻系44个,夫系9个[3],而在此称谓的系统中一般遵循着尊敬、亲密的原则。特定称谓会随着社交场合场所、第三者或多者在场等不同情况而产生众多的称谓变体。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一般男子特别是有一定地位和声望的男子对其妻子称之为“夫人”,这个称谓从表面来看有一定尊敬的意味,但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夫人”可以拆分为“夫之人”,而“夫”是指丈夫,这其实也意味着女性是男性的附庸。之后,“贱内”“内人”“内子”等夫妻称谓语层出不穷。而中国社会底层大众的夫妻称谓中,如“暖脚的”“做饭的”“屋里头的”“婆娘”“孩儿他娘”等称谓体现的不尊重含义则更甚。一般而言,称谓包括姓名、称呼、外号、代号、数字、字母等,而这些称谓也可以视为身份符号的统称与集合体。对特定人或人群的称谓语言体现出特殊的内涵与外延之意义。如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卡夫卡小说《城堡》中的K,间谍小说中的特工代号007等,这些称谓语言放在特定的个体身上,会呈现出不同的身份符号,并携带着某些特定的意义。
《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呈现了一种典型的性格特征,她被农村人称为“炮捻子”脾气,这样的形容意味着她有一种坚毅的气质和血性。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李双双属于“多血质”类型。年轻的李双双嫁给了孙喜旺,一个具有强烈男权思想的人。尽管李双双的个性还未充分发展,但她很早就生了三个孩子,这使她在家庭中承担着艰辛的劳动,且鲜有机会参加村庄的集体会议,与外界的联系与接触也很少。所以,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场域里李双双被称为“喜旺家的”“小菊妈”,以及孙喜旺口中的“屋里的”或者“做饭的”等,“双双这个名字被这么多名称代替着”[4]。孙喜旺对李双双的称谓语言系统属于夫妻称谓语。在一些农村地区,仍然存在这种类型的称谓,比如“屋里头的”“婆娘”“孩儿他娘”等。这些称呼反映了过去社会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作为修辞元素的身份符号在文本中承担的功能,可以是结构性的,也可以是非结构性的。结构性身份符号参与文本生成,是承担文本结构框架支持功能的修辞元素。李准《李双双小传》女主人公李双双的身份符号属于结构性的,她丈夫孙喜旺的身份符号属于非结构性的[5]。小说的开篇就是“李双双是我们人民公社孙庄大队孙喜旺的爱人,今年有二十六七岁年纪。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之前,村里很少有人知道她叫‘双双’,因为她年纪轻轻的就拉巴了两三个孩子”[4]。小说名为“李双双小传”,属于人物名称式小说标题,但小说开篇的第一句却介绍说很少有人知道李双双的名字,她的名字更多地被其他称谓语代替。由此,小说标题与小说开篇的内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隐性张力。从这个角度分析,《李双双小传》的隐含一面就是李双双这一女性主人公名字逐渐从“无名化”到名字被喊起的过程。
出自孙喜旺之口的李双双身份符号的转换,始于“俺做饭的”,终于“我那个做饭的”,这一过程隐藏了孙喜旺和李双双的婚姻伙伴关系,显示了李双双和孙喜旺的劳动服务关系[5]。通过命名或称呼语言来构建、传达和体现个体或群体的特定身份、地位、角色或身份认同,它在语言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并且对于描述人物、情境或社会关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非亲属的称谓语还是亲属类称呼语,都呈现出复杂的人际关系及其背后隐含的内质。而后者便是一个人身份符号的修辞元素,蕴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
二、女性称谓语的变化:地位变化的重要表征
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语言学的蓬勃发展和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使语言和性别问题得到了更加全面、系统的研究[6]。自古以来,我国社会家庭中的男性个体为女性设立了各种称呼,这些称呼展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它们的出现、变化和消失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的基本态度,并且彰显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
在《李双双小传》中,李双双的名字在情节中首先出现在她写在大字报上的落款“李双双”,而大字报的内容有一句非常重要:妇女能顶半边天。李双双这一名字被大家讨论并追问是谁家人的时候,老进叔认为兴许是喜旺媳妇。当大伙询问喜旺的时候,孙喜旺给出了肯定的回应。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农村基本上只有家庭/家族这样的小共同体,再往上就是国家这一“超级共同体”。封建家庭这样的小共同体,固然也有对女性保护的一面,但主要方面却是压迫和禁锢。正如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概括的那样,农村存在四条束缚农民的极大绳索,即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妇女被压在最底层。农村合作化、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导致农村的社会结构出现一个革命性变化,就是在家庭这样的小共同体和国家这样的超级共同体之间,建立了人民公社这样的“大共同体”,每一个农民都因此获得了新的身份,即人民公社社员。人民公社是中国革命的产物,其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当然是支持妇女解放的,这就为农村妇女摆脱夫权束缚提供了极大便利。
李双双在人民公社的框架内逐渐取得和喜旺平等的地位。首先,李双双认为自己作为人民公社社员,具有高度的主体性与集体劳动的参与性,并且作为大集体中的重要一员,有责任且有义务参与公共集体劳动和管理,时刻维护集体利益,不损害人民的共同利益。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使李双双在生产队里的威望越来越高,她还得到了公社党委及各级领导的支持。相比之下,孙喜旺所属的旧社会男性集体就显得黯然失色。而且在《李双双小传》的情节发展中,李双双与孙喜旺二人的夫妻关系也在持续地“拉锯”,孙喜旺认为李双双在家做饭、洗衣、烙饼、做家务、看管小孩才是应有的活动,但李双双在家憋得慌,就算公社没派她去劳作也要去,最终的结果就是喜旺逐渐认同了双双。他认识到双双的行为不仅符合大家的利益,显然也更符合时代潮流。当集体劳动中的男性劳动力不够时,李双双就带领“姐妹们”一起上场扛起劳动的大旗。李双双和围绕在她身边的那些“叽叽喳喳”的妇女,也许还不能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但她们的直觉却是正确的,即如果不能在公社的生产劳动中获得和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那么也不能在家庭中获得和男性平等的地位,“只能在家里收拾收拾孩子,伺候伺候男人”,继续被男人轻视。
李双双作为村庄中广大妇女的典型代表,其乡村社会地位提升之根基来源于集体劳动的参与、受知识教育后话语的表达。此话语的表达主要方式就是贴大字报。在李双双一次次大字报的冲击下,村庄中的广大妇女都在李双双的带动下积极参与集体劳作。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对李双双的称谓便成了“双双”,或“双双嫂子”,而非“喜旺嫂子”,这是非常具体的指称。特别是小说最后部分:“双双嫂子!食堂饭做的好!我们要贴你们的大字报了!”这是李双双小传中女主人公从无名到有名并实现了女性自身的价值与贡献的完美收官。
总之,在《李双双小传》中,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和笔墨对李双双这一本有姓名的人物赋予多种称谓的代称。李双双在老一辈人口中被称为“喜旺媳妇”“喜旺嫂子”“喜旺家”,在孙喜旺口中被称为“俺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等,这便是中国社会特殊的女性“无名化”现象。女性的称谓语从“无名化”到“姓名化”体现了女性的地位以及话语力量不断上升,女性成为独立的个体且拥有不被他人定义的人格。在小说中,李双双是典型的代表,带领着众多“双双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贡献女性的力量,获得了妇女参与公共劳动事务的权利和机会以及人格解放的意义。
三、历史隧洞中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代表:李双双
无论是李双双参与集体劳作的方式和态度,还是她称谓语的隐含转变,都存在着巨大的阐释空间。李双双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她的“泼辣”性格与传统中国女性的温柔、顺从等特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性格特点的形成与特定时代中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等因素有关。李双双的故事也与时代要求的新道德、中国传统价值观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小说故事中,李双双通过她的行为和对道义等价值的坚守,体现了一种新型的道德观念。她是一个勇于挑战传统观念、坚持自我原则的人物。通过她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新道德观念和传统中国人关于“义”“理”“公道”等价值观念是如何进行对话和融合的。这样的故事可能对我国几代人的情感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他们的价值观念中形成了一些积淀。李双双的故事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历史价值的文本,通过对她的性格、行为以及社会对她的接受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她作为一个“新型妇女”的形成过程,以及她对时代要求的新道德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之间的有效连接。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历史的变动与妇女形象的演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女借助“集体”的力量从实践中获得了处境的改善,她们学习了文化,也敢于与封建夫权抗争,提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集体生活带给她们精神上解放和愉悦的感觉,她们确实在集体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这也难怪她们对集体劳动的热情高于男性,比男性更容易找到集体认同感[7]。妇女参加集体劳作是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特殊现象,同时也是彰显女性现实生活价值的重要参照。针对《李双双小传》中孙喜旺和李双双的“打架”过程和话语可以做更多的阐释。李双双看着青年们都上黑山头水库修渠了,她也要求跟着一起去修渠。但遭到了孙喜旺的反对,他认为队里没有派工,没有必要做多余的工,在家照看孩子更好。但是李双双认为孙喜旺的想法太过落后。最后李双双如愿以偿地上了工。但因为上工休息时间较短,原本由李双双负责的家庭伙食就会被耽搁,她担心回来很晚就在门上写着:“你要先回来,可先把火打开,添上锅,面和和。”但是李双双回到家发现孙喜旺什么都没做,而且还在床上清闲地躺着。较有意味的话语从孙喜旺口中说出:“哎!我就不能给你起这个头。做饭就是屋里人的事。”孙喜旺与李双双二人的吵架细节、动作和话语表达十分精彩,他们的吵架中透露出隐晦的亲密感,二人的争论其实紧紧围绕着“相互帮忙”的生活道理而展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妇女因为从家庭中走出,融入热闹的集体而获得相当的精神解放感,这是切实存在的,而此时国家为鼓励妇女从事社会性生产劳动,对托儿所、公共食堂、养老院等“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愿景过于乐观,也是切实存在的,这造成了当时妇女不得不兼顾生产、家务和生养职责,但也不能由此就完全否定李准所看到的许多妇女有过的精神解放感的存在[8]。李准对农村生活极其熟悉,成功塑造出了一个勇于向私有观念挑战的社会主义农村新人李双双形象。特别是李准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李双双》以后,更进一步强化了李双双这一富有时代气息和性格力量的农村妇女形象。这个形象不同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妇女,她要求走出家庭,摆脱丈夫控制的动机,不是为了出人头地,是希望自己投身到社会集体当中,参加热火朝天的社会建设,能为国家、为集体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四、结语
无论是讨论《李双双小传》中的集体与个人,还是女性称谓语的细节呈现,作家李准都将故事和情节准确地放置在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背景下。对女性的称谓语从“代称”到“自称”,从“无名化”到“姓名化”,这些隐晦但又显著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集体劳作中女性的参与和话语的勇敢表达,也呈现出妇女参与社会度的提升及其地位的显著提升。
参考文献
[1] 冯牧.新的性格在蓬勃成长——读《李双双小传》[J].人民文学,1960 (10).
[2] 贺桂梅.人民文艺中的婚姻家庭叙事与妇女解放的历史经验[J].妇女研究论丛,2020(3).
[3] 刘超班.中华亲属辞典·中华亲属标准称谓语简表[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1.
[4] 刘文田.峻青李准小说欣赏[M].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5] 谭学纯.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李准《李双双小传》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J].文艺研究,2008(5).
[6] 张辰昀.从对女性称呼的变化看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7).
[7] 郭丽君.“集体”场域中的“个体”与性别——以《李双双小传》为个案[J].文艺争鸣,2014(6).
[8] 李娜.李双双:从更深的土里“泼辣”出来——试探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型妇女”的一种生成史[J].妇女研究论丛,2022(2).
(责任编辑" 夏"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