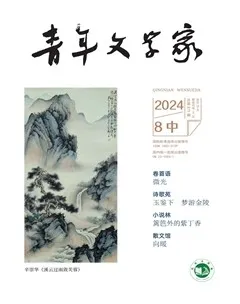寻鲁迅“诗意的、情绪的笔”


李长之在谈及鲁迅的写作特点时说:“鲁迅的笔是抒情的,大凡他抒情的文章特别好。”(《鲁迅批判》)而探寻鲁迅作品的意蕴与创作价值最直接也是最合适的途径,便是剖析作品中“我”的抒情话语。作品中的抒情话语与鲁迅情感世界之间有不可割裂的紧密关联,倘若从这种紧密的关联入手,对“我”的抒情话语进行深入探究,不仅可以更有力地发掘鲁迅笔下抒情话语的深刻意蕴,甚至可以真正走进抒情话语背后鲁迅那不同流俗的精神世界。
“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在鲁迅笔下得到充分彰显。李长之在谈及鲁迅时说:“鲁迅在性格上是内倾的,他不善于如通常人之处理生活。他宁愿孤独,而不欢喜‘群’。”(《鲁迅批判》)观鲁迅的作品,随处可见沉浸在抒情中的文字,甚至有的文章可能整篇都是“纯粹的抒情文字”(《鲁迅批判》)。
陈鸣树先生认为,鲁迅的作品主要为两种形象赋予抒情话语,“一类是农民或农村劳动妇女,另一类是当时进步或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显然,对这两类人物所赋予的抒情语言,不但要表现他们不同的阶级地位的特点,而且要表现他们在阶级性制约下的个性化的特点,这还不够,还必须表现他们这种阶级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思想情感如何在特定的情势支配下的抒情方式。正是他们这种抒情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抒情语言的特色”(许祖华《鲁迅小说修辞论》)。陈先生的观点精准指出了人物“抒情方式”与“抒情语言”的内在联系,这同样是鲁迅作品中人物抒情话语真实合理,可以经得起现实和艺术双重逻辑检验的重要因素。
另一重点是,在鲁迅的作品里,有很大一部分是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创作的。这可以使读者身临其境,容易进入人物内心,使人感觉十分真实。“我”便是一个具有特殊作用的重要人物,故事大多从“我”的口中娓娓道来。鲁迅的三十三篇文学作品里,有十二篇是以“我”的视角叙事的,近乎一半。别林斯基认为,“可以算作语言上的优点的,只有正确、简练、流畅”(许祖华《鲁迅小说修辞论》),这用来形容鲁迅作品里“我”的抒情话语再合适不过。本文以《伤逝》《阿Q正传》为例,试探寻鲁迅“诗意的、情绪的笔”。
一、《伤逝》之“悔恨”与“悲哀”
听闻爱情十有九悲,《伤逝》通篇都是采用内心独白表达抒情话语的。在鲁迅的笔下,只有《伤逝》是专门描述爱情故事的,与一般类型的爱情小说不同,它既非理想主义的爱情赞歌,也无让人绝望的凄美与悲惨,而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忏悔录。“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鲁迅《伤逝》)。翻开小说,扑面而来的是满纸自责的气息,奠定了故事悲剧的基调。
小说处处可见饱含“我”强烈的“悔恨”与“悲哀”的抒情话语,“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鲁迅《伤逝》)“悔恨”与“悲哀”既是“我”抒情话语要表达的核心情感,也是作品主题的底色。
这篇小说的抒情性“多倾向于现代知识分子社会情怀的通联,侧重社会文化伦理意义的探讨”(席建彬《诗情的“蛊惑”—鲁迅诗化小说的叙事读解》)。故事以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故事为起点,描述了当时知识青年对自由解放的追求,可落后社会的脚步拉扯着他们无力前行,他们看不清当时社会环境模糊的面目,只能在迷途中苦苦挣扎,“就在这第二道关口面前,子君却悲惨地失败了,屈服了”(许祖华《鲁迅小说修辞论》)。他们虽然强烈渴望“个性解放”,但新事物在萌芽时期难以与旧事物抗衡,当时的社会是没有反叛者的容身之地的,子君与涓生的爱情终究是被埋葬在了那“无爱的人间”。另外,子君与涓生之间前期并没有建立深厚的感情基础,后期也没有再寻得共同的新的奋斗目标,他们在实现所谓的“恋爱自由”后,便再没有共同的追求了。子君安于现状,不再读书与思考,而涓生爱的正是子君勇敢无畏的解放思想,所以他曾经对子君的纯真热烈的爱终于在失业袭来时荡然无存了。“子君的悲剧并不因为她信奉了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思想,并不因为她信奉了民主主义,恰恰相反,是因为她缺乏充分的、坚定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思想,缺乏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许祖华《鲁迅小说修辞论》)。
小说的抒情话语大多是比较经典的情感知性化的语言,充满引人深思的哲理以及对生命的真谛或对人生价值的审视与思考。这些哲理与“我”的“悔恨”与“悲哀”交织在一起,是须痛彻心扉才能明白的道理,最终凝聚成“我”的一句句抒情话语。这些抒情话语不仅有力地为作品渲染了浓郁的感情色彩,使小说更有思想深度,更是长久地引发后世的思考并指导其行动。而在小说中抒情话语的背后,我们分明看见,站着的善于抒情、善于直抒胸臆的鲁迅。
二、《阿Q正传》之“悲”与“喜”
在鲁迅的诸多作品中,还存在一种充满反讽意味的抒情话语,它们出现在看似不合理的位置,在该“悲”时“不合时宜”的“喜”。在很大程度上,在封建社会这样的环境中,民众只是活着就已耗尽了生命力,更何况是在生杀予夺的专制淫威之下,他们不得不活得更加小心翼翼,以致在苟活中养成根深蒂固的奴隶性。
在《阿Q正传》的“大团圆”中,阿Q在大堂看到上面坐着的人满脸横肉,怒目而视,“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这样紧张的审判环境促使阿Q奴才的本性一下就从灵魂深处冒出来了。阿Q被抓、画押、游街、枪毙,虽然“几乎魂飞魄散”,“两眼发黑”,“似乎发昏了”,但“并不十分懊恼”,“有时却也泰然”,因为他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最后也只是“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连“救命”也没有说出来。至于“圈而不圆”,也并非其“‘行状’上的一个污点”,因为他认为“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
小说并没有用悲剧的手法呈现结局,而是充满喜剧气氛,令人发笑。鲁迅用讽刺幽默的话语勾勒了喜剧的轮廓,但从内而外溢出的却是悲剧的眼泪。故事悲剧的结尾不能简单地归于阿Q个人的愚昧无知,因为,阿Q这种思想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的土壤的,这就是未庄作为缩影在当时社会的体现。站立在这片大地上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逃离这片土壤。在这种环境下,底层社会的人无法幸免,这就是鲁迅曾经非常郁闷,甚至心灰意冷称之为无法打破的“铁屋子”(《呐喊》),未庄就是一个铁屋子,一个让阿Q们窒息而死的铁屋子。在这里,等待阿Q的唯一的归宿只有一个—死去!
再如阿Q对比自己更弱势的小尼姑、小D等人施暴以及他通过“精神胜利法”获得心理胜利时表现出“得意”的神态,都是理应受到批判与否定的,鲁迅也确实用意味深长的话语对其进行了辛辣讽刺,但又会出现诸如“看哪,他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的抒情话语,这完全而有效地扑灭了抒情话语中的全部褒义成分,取而代之的是富有鲁迅独特风格的强烈、犀利的意味。这种“不合时宜”的抒情有一个特别的作用,便是当抒情话语中褒扬的成分越多,其反讽意义往往越是强烈、尖锐,“喜”的氛围越浓厚,字里行间越是弥漫着久久不能消散的“悲”。
精神胜利是《阿Q正传》中“悲”与“喜”交织的一座高峰。阿Q被假洋鬼子剥夺了革命的权利,这对他而言属于侮辱性极强的事情,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要面子”的人。虽然这个面子看似卑微,但是对于他那样一个去过县城见过几次世面就可以回家显摆一番的人而言,这显得弥足珍贵。因此,阿Q更不准他一直看不起的小D革命,“小D也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了,而且也居然用一支竹筷。阿Q万料不到他也敢这样做,自己也决不准他这样做!小D是什么东西呢?他很想即刻揪住他,拗断他的竹筷,放下他的辫子,并且批他几个嘴巴,聊且惩罚他忘了生辰八字,也敢来做革命党的罪。但他终于饶放了,单是怒目而视的吐一口唾沫道‘呸!’”阿Q在精神上又胜利了。阿Q滑稽可“喜”行为的背后,其实是当时民族一种可悲的病态:现实不允许你抬头,内心想尽办法要找到让自己的郁闷得以排遣的渠道,取得自我胜利,即精神胜利。
在《阿Q正传》中,鲁迅创造了一个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悖论:要革命的是阿Q,虽然他革命的目的并不纯粹,甚至是庸俗地为了钱和女人,但是客观上这种懵懂的、好奇的革命愿望总归是为了解除他人给自己带来的压迫的,从人性解放的层面上,还是具有鲜明的积极意义的。但是,令人吊诡的是,阿Q自己属于被压迫者,却不允许同样属于被压迫者的小D等人去革命,简单地说,他革命的前提是以压迫比他更可怜的人为代价的,他如果得到了自由,就意味着要剥夺更卑微的另一大批人的自由。这正应了鲁迅先生说过的,穷人拿起刀,不是砍向欺压他们的强者,而是更加严厉地砍向比他们还穷苦的人。阿Q这种革命观,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国底层被剥削压迫的人民有强烈的改变生活现状的诉求,但由于社会环境造成的阶级局限性,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的观念,这些都形成于旧制度下的未庄,是落后乡村的真实写照。
在《阿Q正传》中,所有情节几乎都体现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用“悲”写其“不幸”,用“喜”写其“不争”。“喜”的内核是“悲”,悲喜交集,相互转化,将“阿Q相”真实展现在世人眼前,映射出民族病态的心理,也体现了鲁迅作为一个批判者、一位民族战士强烈而又鲜明的情感。
三、抒情语境及其审美意义
小说文本依托语境进行衔接与构建,作为“我”抒情话语产生的特定艺术条件,语境具有衡量“我”抒情话语审美意义的关键作用。抒情话语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或情景,这样话语本身才有意义,才能表达小说的核心思想与创作目的,否则便无法赋予抒情话语自身价值,更无法产生文学作品。
从文学作品文本构建这一视角出发,无论是何种话语,既包括直抒胸臆的抒情话语和细致入微的描写,也包括逻辑缜密的议论或客观质朴的叙事语言,都是文本构建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唯有通过它们相互之间的配合、演进,小说的整体语境才能实现建构,文学作品才能产生,话语本身才有意义,才有产生的价值。假设一个句子没有和段落中的其他语句搭配衔接,或者与其他话语相矛盾,那么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甚至会干扰文本本来的秩序,适得其反。
由此可见,语境作为“我”的抒情话语产生的特定条件,对这些抒情话语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是探寻和研究“我”的抒情话语为何产生,何以产生的重要线索和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我们验证“我”的抒情话语是否真实合理的依据,是衡量这些话语是否有价值的标尺。
探寻鲁迅作品的意蕴与创作价值追求,最直接也是最合适的途径便是剖析作品中“我”的抒情话语。众所周知,鲁迅诸多作品里大量“我”的抒情话语所承载与传递的情感内涵,虽然不能单纯地完全等同于鲁迅本人的全部情感,但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紧密关联。正如郁达夫主张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在某种程度上,文学作品是对作家人生经历、思想、人生观的再现。还有专家提出:“鲁迅主要是个主观作家,他写的东西大抵都跟自己有很深感受的事情有关。”(许祖华《鲁迅小说修辞论》)从这种紧密的关联入手,对“我”的抒发话语进行深入探究,我们不仅可以更有力地发掘鲁迅笔下抒情话语的深刻意蕴,甚至可以真正走进抒情话语背后鲁迅那不同流俗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