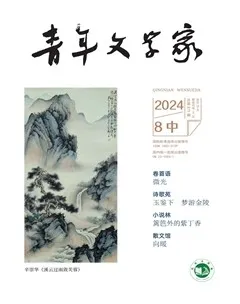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明清俗曲是指明清时期出现的一种文学与音乐、表演相结合的艺术形式。作为明、清两个时代特有的音乐文化现象,明清俗曲是在各地民歌基础上,吸收诸多文化因素发展、兴盛起来的一种古代歌曲形式,主要流行于内地。作为内地特有的一种音乐艺术形式,处于边陲的云南地区本是没有的。但随着历史上中央政府对云南统治的逐渐加强,以及明清时期大规模内地移民迁徙入滇,再加上政府对于儒学教育的大力推行和“改土归流”等政策的实施,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得以快速发展,这也为明清俗曲在云南的传播发展培育了良好的艺术土壤。在孙明跃老师所著的《明清俗曲在云南的传播与衍变》一书中,其首次运用传播学理论,就明清俗曲在云南的传播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观照,分别对明清俗曲在云南传播的历史文化背景、自然传播、制度传播、传播特点、传播效用和衍变等六个方面展开了详尽的论证和研究,并就明清俗曲在云南传播衍变的四种模式和其形成的原因特点进行了综合分析。
一、明清俗曲在云南传播的历史文化背景及传播形式
明清时期,云南城镇与经济文化发展显著。明初,朱元璋废除元代行省制,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并实行移民入滇和儒学教化,以期实现“以夏变夷”。清朝统一云南后,改明代三司为云南省,设巡抚和云贵总督,沿用明代移民入滇和儒学教化方针,尤其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政策使更多汉族移民入滇。汉族移民和汉文化的推入促使云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快速发展,与内地文化趋同。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萌芽发展推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崛起,内地明清俗曲随移民传入云南,并深刻影响本地说唱、戏曲和器乐音乐文化的发展。正如冯光钰先生在《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中所说:“一切传统音乐都是传播的音乐,在传播中不断演变,又在演变中不断发展。可以说,没有传播及演变就没有音乐文化的发展,不再传播演变的音乐文化,将是僵滞的音乐文化。”
明清俗曲的传播与衍变主要包括自然传播和制度传播。作者在书中详细论述了这两种形式,此为本书的重要内容。自然传播是指无意识、无目的的文化因素或特色传播。内地移民将俗曲带到云南,并将其传承传播。移民是俗曲在云南的主要传播者和欣赏者,也是主要媒介。战争、军屯、民屯、商屯和文人传播等属于自然传播,无智力或技术媒介介入,非政府机构组织。明清移民入滇促进了内地与云南文化的交融,汉人成为云南主体,夷汉杂居成为主要聚居形式,俗曲便由此融入本土文化,不同传播群体和类型的相互联系与渗透,构建了俗曲在云南的传播网络,促进了其传播和发展。
“礼”作为中国礼制文化的核心,其外显形式就是礼乐制度,而这一制度具有教化功能。当礼制俗化形成民俗,礼乐又同民间风俗对应,五礼(军、嘉、凶、吉、宾)在乡村礼俗中表现为结婚、丧葬、祭祀、宴客等,这都是礼制俗化的具体体现。五礼中音乐成为民俗用乐范本,鼓吹乐为代表。云南明清时期的俗曲中,鼓吹乐便证明了官方礼制用乐与民间礼俗用乐已经融为一体,通过乐籍制度相互沟通。乐籍制度是古代对专业乐人的管理制度,服务于官方,负责承载民间礼俗音乐的表演。虽在雍正时期该制度被废除,但礼乐制度仍有所保留,被除籍的乐人将官方礼乐传播至民间,使得礼俗之间的互通性更为明显,明清俗曲在云南得以迅速传播和发展。
二、明清俗曲在云南的传播特点
明清俗曲作为一种兴盛于明清时期且具有承前启后性质的特定的艺术形式,兴起于北方,蔓延至南方,在各个地区广为流传。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中央政府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推动了内地移民和汉文化的渗入,使得明清俗曲得以随内地移民的迁徙而在云南生根发芽。作者就明清俗曲在云南的传播特点进行了悉心归纳,将其作三点进行概论。
首先,明清俗曲作为一种移植性传播文化,具有“移民到哪儿,‘俗曲’就流传至哪里”(孙明跃《明清俗曲在云南的传播与衍变》)的特点。明代移民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云南腹地的城市和坝区,这也是汉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俗曲的流传也主要集中于此,也是俗曲最为发达的区域,其中包括以俗曲为唱腔的花灯、扬琴、莲花落、渔鼓等。相较于汉民族聚居较多的地方,那些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明朝时期还是实行土司制度,俗曲成了服务土司阶层的一种娱乐手段,对于少数民族的普通民众而言则很少有机会接触。对比明朝的移民模式,主要是以服从中央政府统治的强制性而言,清朝时期的移民就偏于自发性。在“改土归流”和移民垦荒政策的实施下,大规模移民涌入云南地区,其中就包括与云南接壤的蜀地,以及江西、湖广、山陕、江南的移民。由此,内地的音乐文化也深刻影响了云南本地音乐的发展,如云南的滇剧、花灯、曲艺等深受四川音乐的影响;湖广移民的襄阳腔、秦晋移民的秦腔、江南移民的昆腔等,这些通过移民而来的不同地方戏剧,在同本土音乐的交融中不断摩擦出新的火花,为云南本土戏剧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通过对云南地域文化的特征性进行文化圈的分层:一是汉族移民聚居区,二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区,三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聚居区。不同的聚居区,明清俗曲的分布与传播效应也有所不同。根据分层来看,汉族移民聚居区的明清俗曲分布较为广阔,即现在的昆明、曲靖、昭通、保山等地,最有代表性的属云南花灯,该区域的花灯唱腔多以明清俗曲为主,所存的明清俗曲曲牌最多、曲调最为古老,如【打枣竿】【挂枝儿】【哭皇天】【寄生草】【红绣鞋】等。再到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区,即现在的丽江市、文山州、红河州,该区域汉族依然为主体民族,但丽江的纳西族、文山的壮族,以及红河的哈尼族和彝族依然数量较多,因此该区域的戏曲音乐也多与当地少数民族音乐互通交融,像彝汉杂居的建水、蒙自、弥勒等地的花灯唱腔音乐就具有明显的彝汉风格,曲牌与明清俗曲有关的就有【打草歌】(即【打枣竿】)、【弦苏调】(即【茉莉花】)、【合婚调】(即【孟姜女调】)等都融入了彝族音乐元素,尤其是滇南彝族的“四大腔”音乐。而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即现在的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德宏州等,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是大于汉族人口的,俗曲音乐在当地属于小众,但因汉族也非极少数,俗曲音乐在不同程度也同周边民族音乐有融合交汇的现象,如以傣族和景颇族为主的德宏州,其芒市的五岔路乡作为汉族聚居地,也有同明清俗曲有所关联的曲牌,包括【一杯酒】【采茶调】【散花调】等。
最后,明清俗曲的“俗”最早源于“雅”,而脱离“雅”之后的“俗”,就成了民间的自然选择。流行于内地的明清俗曲,其发展离不开文人雅士,在他们的推动下,那些民间音乐成了一种“雅化”代表,且总有些文人的矫揉造作之气。尤其到了后期,脱离生活和群众的明清俗曲,最终也落得被民间抛弃的下场。作者以云南传统花灯剧为例,虽还存有部分较为“雅化”的曲牌,但其在唱词上也都有变“俗”,曲也变“简”,如流传于元谋、禄丰、红河等地的【打枣竿】,被简化为单乐段或多乐段结构,以分节歌形式演唱,歌词变得通俗易懂。在这场雅衰俗胜、由雅变衰的过程中,作者将其主要原因归于文人雅士群体的逐渐消失和乐籍制度的废除,而传播者和接受者的消亡,使得雅化俗曲曲牌的整体衰落也就成了必然。
三、明清俗曲在云南的传播效用
明清俗曲以其鲜活性和真挚性反映着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仅为众多文人所看好,也为市井所传唱,成为当时城市生活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在当时政策的推行下,云南地区对于中原文化具有强烈认同感,明清俗曲在随内地移民入滇的过程中,不仅以单曲或小唱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在此基础上还通过融合云南本地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了本土戏曲戏剧的发展。今时今日,内地传入至云南的明清俗曲都还保存在云南的传统音乐之中,包括云南花灯、云南扬琴、云南洞经音乐、云南各地的鼓吹乐和云南民歌等。
在书中,作者就云南花灯、云南扬琴、云南《洞经音乐》中的明清俗曲都做了举例论证,印证其“活化石”的意义。与此同时,汉族移民及汉文化的不断扩宽,使得明清俗曲在云南的传播与演变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模式,在壮大自己的同时,也推动了云南多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像云南汉族的曲艺艺术有的就是在明清俗曲基础上发展的,如云南扬琴、云南花灯等。云南扬琴在后来的发展中,又不断吸收各类曲艺的养分中逐渐形成了新的戏曲形式,即云南曲剧;而云南花灯在广为流传的过程中也深受云南本地少数民族的喜爱,如红河彝族地区的花灯,在演唱中使用彝语还有彝族特有的演唱技巧,正因如此,该地区的花灯也被当地人称为彝族花灯。
不过,明清俗曲虽是一种娱乐性的产物,但其作为明清时期统治者推行的边疆治理政策下移民入滇所带来的“移民文化”,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从明清中央政府的政治角度来看,以文化艺术形式去传播儒家文化是再适合不过的了。云南扬琴中的唱腔就多以曲牌连缀为主,板腔体为辅,唱腔分为书腔类和唱曲类:书腔类的剧目多以佛道的劝善为主要内容,宣扬善恶有报的因果报应来教育人们;唱曲类所用声腔基本为明清俗曲,剧目多以传播汉族历史文化和儒家道德伦理为主,具有“高台教化”的功能。云南花灯艺术中也体现了许多“忠孝节义”的主题,那些内地而来的文人仕宦来到云南后,接受政府“以夏变夷”的政治思想和肩负边疆“教化”功能的责任,使他们在娱乐中更倾向于“寓教于乐”。而云南花灯和扬琴的流传范围不止于达官显贵、文人雅士等,同时也深入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其次还有具有移风易俗、敦品励行的云南《洞经音乐》和有着“忠孝节义”为宗旨的云南傩戏,在潜移默化之中都深受汉文化影响,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就如陈独秀先生在《论戏曲》中所说的:“戏园者,实普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是普天下之大教师也。”在歌舞演故事的过程中,明清俗曲身上所带有的“政治教化”性,也得以在云南地区广为流传渗透。
四、明清俗曲在云南的衍变模式
在对明清俗曲在云南发展过程的详尽叙述中,作者总结出了明清俗曲在云南传播衍变的四种模式:第一种模式为汉族聚居区,传播者和接受者是移民;第二种模式为汉族聚居区和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区,传播者和接受者为移民与少数民族;第三种模式为土司府统治地区(包括“改土归流”以后依然实行土司府统治的地区),传播者为少量内地乐人和少数民族乐人,接受者为土司府上层贵族;第四种模式为“改土归流”后的土司府统治地区,传播者为移民和少数民族乐人,接受者为移民和少数民族。从明清俗曲在云南的传播来看,明清时期汉族移民及其后裔作为传播俗曲的主体、载体和接受群体,对明清俗曲在云南传播和衍变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就乐籍制度在内的国家礼乐制度则在其中更为关键,毕竟在国家政权力量所控制的地区才能发挥由政府主导的政策实施,汉族移民也能得以顺利去往云南并将俗乐进行传播。因此,作者将明清俗曲在云南的自然传播和制度传播进行了一个主体和关键的划分,即以自然传播为主体、制度传播为关键。
作者在对明清俗曲是如何在云南进行传播和衍变的研究中,首次运用传播学理论,在善用冯光钰等人的自然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又引入项阳等人的乐籍制度传播理论,就文化传播所处的环境、主体、客体等方面,对明清俗曲在云南的发展过程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观照,同时站在历史的角度对其传播衍变过程进行了具体分析,这对扩展明清俗曲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具有积极意义。但就本书的撰写来看,还存在一些值得完善的地方:第一,有关明清俗曲的界定可以再明晰一些;第二,明清俗曲在云南的传播和衍变过程中的具体呈现,可以再多一些田野材料作为例证依据;第三,作者针对明清俗曲在云南的传播与衍变,主要倾向于历时性研究,若是在此基础上多一些共时性研究,那么研究内容也将更为饱满。总的来说,瑕不掩瑜,孙明跃老师所著的《明清俗曲在云南的传播与衍变》的价值性不言而喻,有兴趣的学界益友不妨一睹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