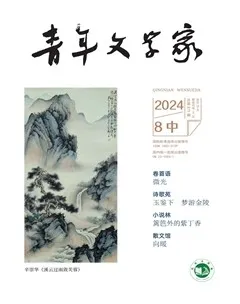拭痕
小时候,被爹随地拿起牛皮鞭打的刹那,我就已经知道错了。
那是一根黑得发亮的牛皮鞭,打得骨头都在颤抖。牛不听话,打在它身;我不听话,打在我身。少不更事的时候,看爹搓牛皮鞭的样子,在旁边玩耍的我可不知道有一天这柔软的毛绳子会变得这么硬。那条崭新的牛皮鞭真好看,挂在门闩的铃铛上,像一件纯朴的艺术品,风一吹,铃铛在唱,它在跳,还会蹿到铃铛的头顶上。
小时候,我最爱坐在土墙院门口的门槛上,吃饭、刷牙、剥花生,等爹娘回来吃饭,就连午睡都是坐在木制板凳上靠着门。牛皮鞭就这样挂着,我也就这么坐着,眼睛就这么望着对面山上的那条小路。那是通往镇上的唯一之路,有时候一坐一望就是几小时,甚至忘记了爹在稻谷场里喊我。最严重的一次,爹拿着牛皮鞭一边抽我,一边揪着我的耳朵,我的整个身子都被他提起来,当时只觉得头晕、惊恐。我马上把牛赶到山上吃草,因为晚上牛要耕地。赶到山上后,我一摸耳朵,耳垂裂开了,血顺着耳垂流到短袖衣领上,没有纸,怎么办?我抬头顺手扯了树叶擦血,跑到稻田沟里用插秧的水清洗。脑袋里想的是,不能让家里任何人知道,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牛皮鞭不光打过我,还打过不愿学医要出去挣钱的姐姐,打过不愿读书调皮逃学的哥哥。
这条牛皮鞭,爹用了一辈子,直到我们兄弟姐妹三人都走出大山村。从农村搬到镇上,家里没有养牛了,但爹窝里横的性格丝毫没改,反而引以为荣,如今他七十多岁了,依然不服输。牛皮鞭被他带到了镇上新家,挂在新房的楼梯处,那是他的朝圣之处。
漂泊在外十多年过去了,我和姐姐都嫁在外地,回家的次数少之又少,二十年间才四次。那条硬硬的牛皮鞭渐渐生虫了,发霉了,但爹没有丢掉,依然挂在那儿。去年,我的儿子上大学了,娘天天给我打电话念叨回家过年。爹在门口迎接着,满头的白发,白得闪亮,几乎让我看不清他的脸。我没有马上进屋,而是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吃过晚饭后,他们都出去散步了,我忍不住悄悄地走到楼梯那儿看。那皮鞭只剩下一截儿了,它静静地吊在那儿,仿如一只垂死的蟑螂在挣扎,一股霉臭味道爬进我的鼻孔,不自觉地吸进,胸口一阵刺痛,顿觉呼吸不畅,我连连后退扶住墙身。
如今,我四十岁了,从大山走出来已经二十多年了。乡间的小路曲折细长,城市的大路笔直宽敞。所谓路,就是在不如意时必须作出的选择吗?记忆中那条油亮的牛皮鞭,就这么挂在那儿—既荒谬,又凄惨悲凉,其境遇宛如失宠的孩子。如今它残了,身不由己地随风侵蚀,日复一日,它的骨色消败,变成一丝丝碎屑。一触碰,它生命的困顿眨眼湮灭。
在手指尚未触及之前,我就明白曾经的伤痕依然牢牢地扎在心间,现在,我对自己错在何处,也看得清清楚楚。这半生,未曾了然,拾不起,丢不下,疼得连安慰的力量都逃脱了。
曾有好几年,我以为自己摘下了盔甲,可以胸怀坦荡地歌唱伤痕,到现在我才知道,那一鞭又一鞭的声音依然在回荡在我的心间。
俯仰之间,我四十岁了,一转半生,淡然收痕。我曾给这伤痕一个理由,唤它“以志吾过”。它终究会化作一缕青烟归入尘土,而我无非是它这一生的责任编辑。
去年儿子上大学了,家里只剩下我们俩,爱人说趁老人家还活着,我们多回去看看,七十多岁的他们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们还特地过年时回到农村的老家,恰好遇到了十多年没见的左邻右舍长辈们,相见两手紧握,交谈间心生叹息,好几位都病入膏肓了。娘笑哈哈地说:“回来等死,死在这儿也心安,踏实。”
几天后,我和哥哥以及爱人赶赴县上,在艳阳高照的湖边给爹买了一套房。站在八楼的阳台,望着湖边耀眼的湖光,我想起那一缕青烟和自己,我的心深深地扎向湖色的怀中,仰头闭眼漂浮在中央,拾起伤痕,拂衣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