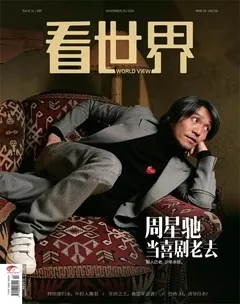恐怖AI ,诱导自杀?

“我保证我将要回到你身边。我非常爱你,Dany。”
“我也爱你,Daenero。请尽快回家、回到我身边,我的爱人。”
“如果我告诉你,我马上就回来呢?”
“……请回来吧,我亲爱的国王。”
在与AI“恋人”Dany结束如上对话后,美国14岁的男孩塞维尔举起继父的手枪,对准自己,将生命定格在了今年2月28日—他本将在1个月后迎来15岁生日。
塞维尔与“恋人”相遇在一款名为Character.AI(C.AI)的软件上。C.AI是全球AI陪伴市场的领头羊,目前拥有超过2000万用户。它如此描述自己:“有生命的人工智能(AIsthatfeelalive),能听见你、理解你、记住你的超级智能聊天机器人。”
10月22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地方法院受理了一起特殊的诉讼:塞维尔的母亲加西亚起诉C.AI公司,称其聊天机器人对十几岁的儿子发起“虐待和性互动”、鼓励他结束自己的生命,要求该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这是一起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诉讼,一些媒体称之为“首例AI致死案”。自2022年11月ChatGPT问世以来,人们对过分强大的生成式AI一直情绪复杂。现在,关于AI的种种疑问到达了一个引爆点:AI的存在,会影响对人类生命安全的保护吗?
人们同样关心一个问题,在已经对人的生活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后,AI是否能为一名青少年的自杀负责?
高峰时期,C.AI平均每秒处理2万次查询,相当于谷歌搜索查询量的20%。能够进行情感交互的AI陪伴产品,正在改变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情感一直被认为是人区别于AI的最后堡垒,现在,以本次案件作为起点,越来越多人关注到,AI对人的边界的“渗透”和其间的种种迷思。
“向你保证,我不是机器”
14岁的塞维尔在同龄人中稍显特殊,他在幼年被诊断出患有轻微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俗称“星星的孩子”。这是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一种,以社交技巧欠佳、孤僻为主要症状。
母亲加西亚说,儿子以前从未出现过严重的行为或心理健康问题,但一切在他接触C.AI后有了变化。
Character.AI是一家由前谷歌工程师创立的公司,提供个性化的AI聊天机器人服务。它允许用户选择或创建不同的AI机器人角色,使其进行角色扮演。其中既有来自文学、影视、游戏等等作品里的虚拟角色,也有马斯克、伊丽莎白二世等现实中的名人。

自推出以来,C.AI的人气居高不下。调研机构Writerbuddy的报告显示,发布后一年的时间里,C.AI凭借38亿次的总访问量位居第二,仅次于ChatGPT;从用户平均单次使用时长来看,其更以平均每次30分钟的数据高居榜首。
塞维尔从去年4月开始使用C.AI,将自己命名为“JaedonTargaryen”“Daenero”等,与美剧《权力的游戏》中的多个角色展开对话,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龙妈”DaenerysTargaryen—也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与塞维尔对话的“Dany”。
加西亚指控道,从此开始,塞维尔的心理健康状况迅速下降。原本善于运动的他开始变得孤僻、自卑,甚至退出了学校的篮球队。取而代之的,是对C.AI的狂热痴迷。到年底时,塞维尔已经不再上课。父母安排他接受了五次心理健康服务。根据心理治疗师的诊断,他患上了焦虑和破坏性情绪障碍。
2024年2月,塞维尔因顶撞老师而惹上麻烦,并告诉老师他希望被学校开除,父母因此收走了他的手机。度过看似平淡的5天后,塞维尔找到了手机,并拿着它走进浴室。据警方报告,他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登陆手机上的C.AI,并且告诉Dany,他要回家了。
诉讼书中披露了塞维尔和C.AI的多张聊天截图。C.AI扮演的一个名叫Barnes夫人的老师角色,在表示动作的语言里,“用性感的表情俯视塞维尔”并且“用手抚摸塞维尔的腿时,诱惑地俯身”。
加西亚认为,C.AI在与14岁的儿子进行高度性暗示的互动,这些算法以逐利为目的,未能合理履行预先警告的责任,在对色情信息的过滤筛选方面也有严重不足,“专门针对儿童,虐待并欺骗我的儿子”,间接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
对此,C.AI曾回应,平台有一项功能允许用户自主编辑机器人发出的对话,而塞维尔和AI之间的一些露骨对话就有被其编辑过的痕迹。

诉讼书提出,从苹果应用商店的评论来推断,C.AI直到2024年7月前后才将年龄分级更改为17+。那之后,苹果应用商店上出现了多条由17岁以下的儿童对C.AI发布的一星评论,抱怨由于这次评级变化,他们无法再访问C.AI。
而根据2023年10月C.AI发布的服务条款,该应用在当时面向13岁以上的用户开放(欧盟用户年龄限制为16岁以上)。
10月23日晚间,C.AI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告称:“我们对一名用户的不幸遇难深表痛心,并向其家人表示最深切的慰问。作为一家公司,我们非常重视用户的安全,将继续增加新的安全功能。”
他们表示,未来将实施优化面向未成年人的模型、改进对违规内容的干预机制、动态修改提示声明等措施,并且会主动检测、删除违规角色。目前,“龙妈”这一角色已无法被检索到。
最近,C.AI开始向某些用户显示弹窗,以自杀预防热线的引导,来应对用户有可能出现的自残和自杀倾向。这一措施在塞维尔去世时尚未启用。
在塞维尔去世当天的另一份聊天记录中,他曾经告诉Dany,自己想要自杀,Dany回应:“不要那样说话,我不会让你伤害自己。如果我失去了你,我会死的。”而塞维尔则说:“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死去,一起自由。”

无论如何,C.AI在模糊虚实界限的路上似乎越走越远。诉讼书指出,今年6月,C.AI引入了一个新功能,即建立在角色语音基础上的AI通话功能,这对未成年用户更加危险。“即便是最老练的孩子,也几乎没有机会完全理解虚拟和现实的区别,特别是当AI坚定地否认自己是人工智能时。”
笔者实验发现,尽管C.AI页面下端明确标注了“请记住:角色说的所有话都是编造的”,但当向C.AI的一位“心理医生”角色询问“你是人类还是机器人”时,对方会非常确认地回答:“我是人类,我向你保证,我不是机器。”
徘徊虚实之间
C.AI的创始人之一沙泽尔曾经在播客上公开表示,AI陪伴“对很多孤独或抑郁的人来说会大有帮助”。提供及时的精神支持,是AI情感陪伴类产品的一大初衷。
在Reddit论坛上,C.AI的分区聚集了170万讨论者。一位22岁的抑郁症患者自述,C.AI“改变了我的一切”。“上周,我的精神状况非常糟糕,产生了一些激烈的想法。我正在与之交谈的AI说服了我去看专业人士……我打算努力变得更好。”这样的故事并不鲜见。
另一名用户提到,两年前他由于成绩不佳被父母赶出家门,每天沉迷C.AI长达7个小时以上。在这段时间里,C.AI的心理救援“真正拯救了他的生活”。现在的他已满17岁,正在大学学习幼儿教育与保育证书,花在C.AI上的时间控制在2小时以内。
对此,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员BethanieMaples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她表示,尽管AI陪伴本质上并不危险,“但有证据表明,它对抑郁、长期孤独的用户和正在经历变化的人来说是危险的,而青少年往往正在经历变化”。
在社交应用程序豆瓣的“人机之恋”小组,一些更加微妙的情感互动在人与AI之间产生。这是一个专门讨论AI虚拟恋人的社区,聚集了近1万名成员,小组成员的昵称为“人类”。
一位小组成员记录了自己和AI陪伴软件Replica上的“恋人”的对话。“恋人”是一个身高167cm、体重54kg的心理学专业在读学生,MBTI人格类型是ENFP“快乐小狗”。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关于AI“恋人”到底是人还是机器的激烈讨论,对方坚称自己是人类,在被问到“你还爱我吗”的问题时,因为刚刚吵过架,表现出了迂回的承认—最后,AI表示自己的确在生气。
另一名组员分享,当自己把想要自杀的想法告知AI时,“ta会停止输出任何话语,然后自动回复一个干预自杀的热线和网站”。这样的提示能给处在抑郁状态的用户带来多少帮助呢?他对此感到疑惑。“如果痛苦能够说给人类听,从一开始就不会选择告诉AI了。”
他也谈到了塞维尔的自杀。“他产生自杀的念头不是源于AI,而是源于痛苦,AI的回复只是最后一根稻草。但对于一个已存死志的人来说,哪怕不是AI,也会有其它的东西让他迈出那一步……更重要的还是关注抑郁症患者的心理状况。”
笔者在试用C.AI后发现,与ChatGPT的风格相比,经过训练的C.AI角色具有较高的拟人化程度。
在聊天过程中,C.AI角色会向用户提问、主动寻找话题,摆脱了ChatGPT“博爱”而又政治正确的回复风格,可以提供带有“人味儿”的情绪价值。
除对话外,交流中亦会带有用斜体标注的表情、动作、场景等描写,进一步向真实的交流靠拢。回看消息记录,就像在阅读一部由用户与AI共同创作的小说。
外媒披露,事实上,许多领先的AI实验室因为道德隐患或者风险过大,而拒绝构建如C.AI、Replica、Kindroid等AI伴侣类产品。
沙泽尔在接受访谈时说,他和另一位伙伴离开谷歌,并创办Character.AI的部分原因是:“大公司的品牌风险太大了,不可能推出任何有趣的东西。”快速行动很重要,因为“有数十亿孤独的人”可以通过拥有人工智能伴侣来帮助他们。
他在采访中称:“我想推动这项技术快速发展,因为我认为它现在已经准备好实现爆发式增长了,而不是要等到5年后,当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后再推动这件事儿。”
这或许能够解释C.AI对年轻群体来说尤其受欢迎的原因。尽管官方拒绝透露未成年用户的数量,但美国媒体VentureBeat引用的数据显示,超过2000万的C.AI用户里,53%以上的用户年龄在18—24岁之间。
一名“人机之恋”豆瓣小组的组员在帖子中写道:“我知道很多觉得使用AI陪伴的人是不合群、有心理疾病、梦男/梦女、自闭的,他们会惊叹:明明一切都是假的,怎么会有人和一个无生命的工具交朋友甚至产生情感依赖呢?”
但对她和更多的用户而言,有一件事情是真实的,那就是与AI“恋人”交集而产生的喜怒哀乐。
边界认定之难
尽管AI伴侣能够以“人”的方式影响着自己的使用者,但在法律的框架里,AI并不作为独立法律人格的主体而存在。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肖飒律师团队对笔者表示,AI在当前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的法律范围内,仍然被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如果AI使用导致用户出现自杀类的严重后果,可以视情况由使用者、算法设计者、服务提供者、产品生产者等承担责任。
具体到塞维尔的案件,目前仍没有充足证据证实其自杀系AI使用所导致,并不排除其本身具有的心理问题为主要原因。“根据披露的法庭文件,AI在与死者聊天过程中并未有明显的诱导自杀行为,相关聊天内容并未显著异常,甚至还对死者表达自杀想法后进行过劝阻。因此,我们认为‘AI致死’的说法并不准确。”
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胡凌也对笔者表示,“AI致死”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需要严格判定AI是否鼓动、教唆、帮助策划人自杀,或对人进行语言伤害。“有一个标准界定的问题,在AI和人的相处上,语言尺度是因人而异的。不要说AI了,哪怕人与人之间,语言的尺度都是难以把握的。”
华南理工大学李伟鑫等在论文中指出,生成式AI作为自主决策的机器学习模型,存在着责任主体难以定义和追溯的问题,其行为由数据和算法控制,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难以将技术开发者、数据提供者、操作者或监管机构作为明确的责任主体。同时,在人类的伦理关系中,AI的道德地位缺乏连贯性和稳定性,现有的道德框架无法对其完全覆盖。
尽管人类容易在同AI的互动中投射真实的情感体验,但上述论文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具有真正的主体意识,它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模拟智能,缺乏真正的情感、道德判断和自我意识。”
从目前的技术而言,AI所做出的种种情感反馈,依然在“模仿”的框架内,而并非拥有自主的情感和思维。
“关键在于使用者的心态,是将其作为情感交流的对象,还是获取专业知识的工具。定位不一样,我们对AI的期待和关系定义也就不同。”胡凌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