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四告二》“帝宾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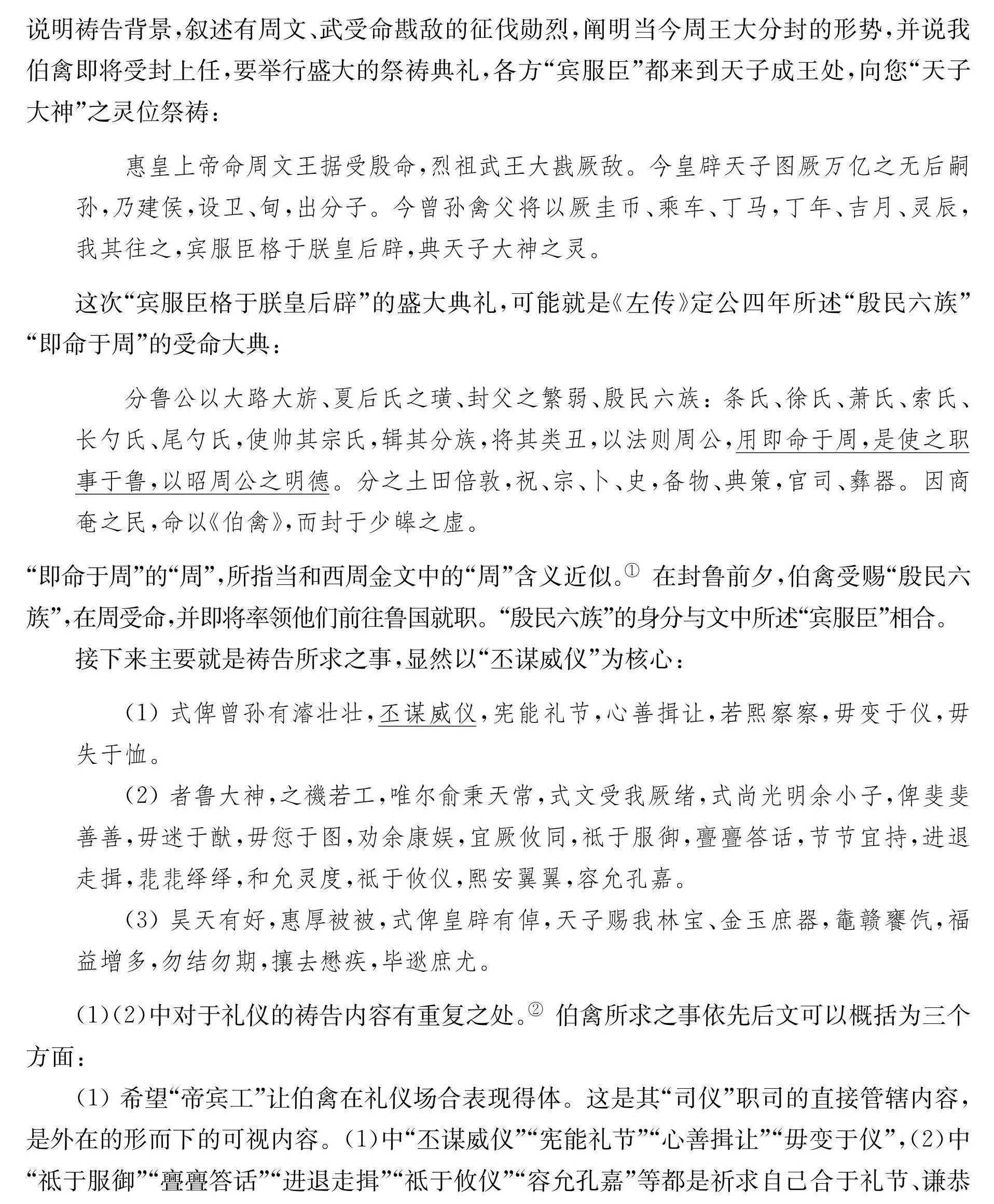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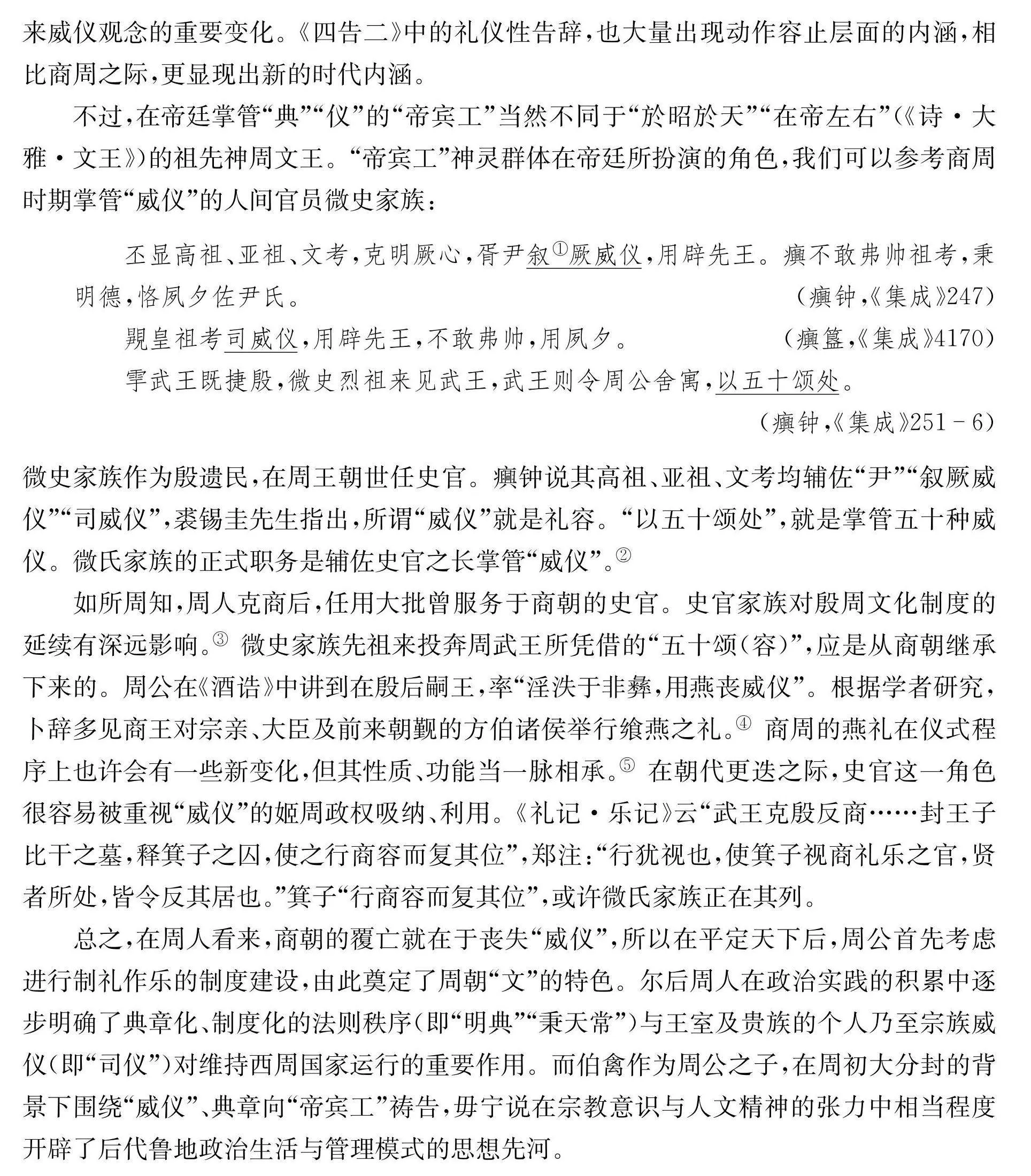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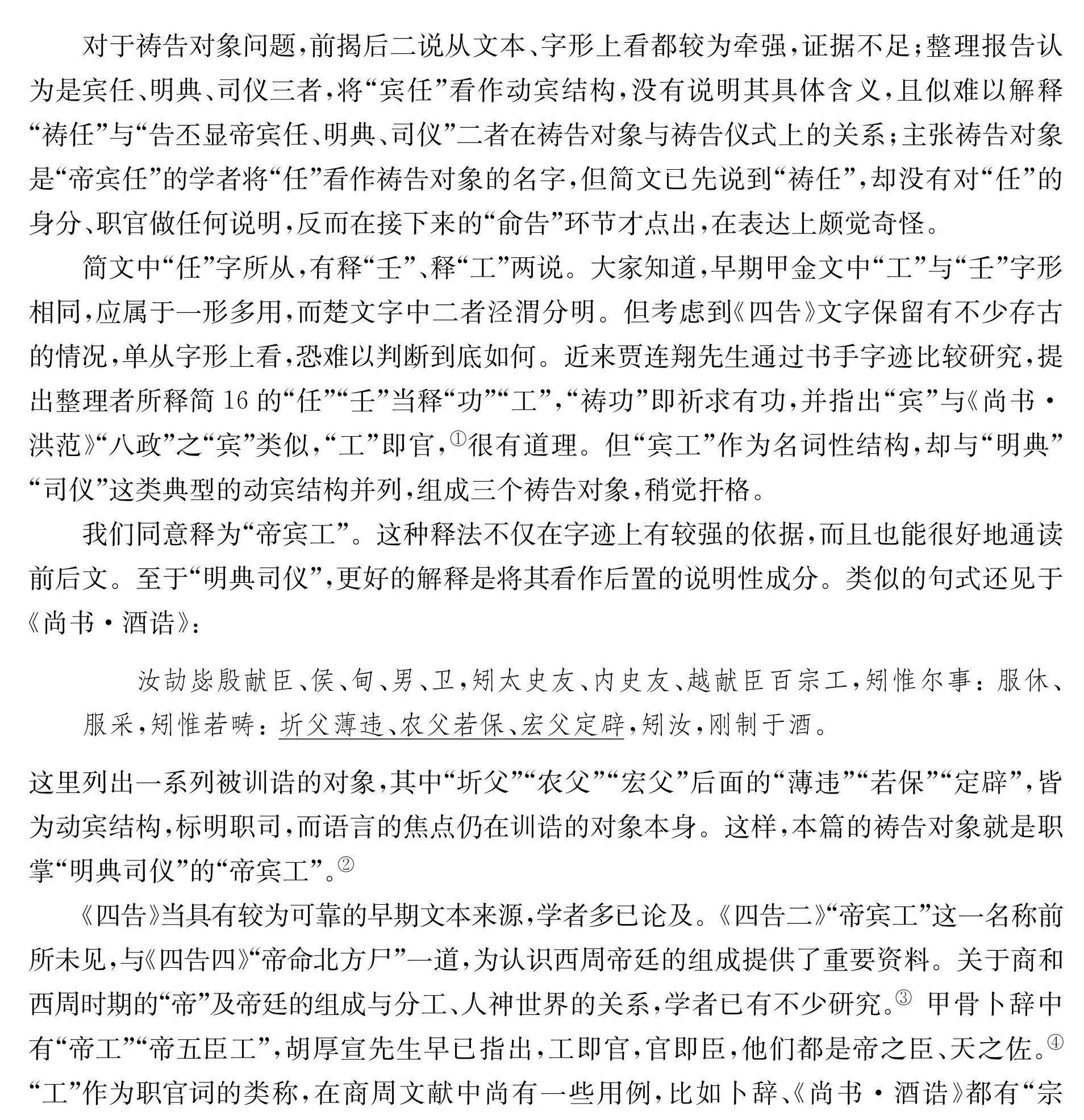
摘"要: 清华简《四告二》伯禽的祷告对象是“帝宾工”,即帝廷掌管礼仪典常的官员,是人间相关官员在帝廷的对应。简文“明典司仪”后置,标明职司。“帝宾工”的出现,为研究西周帝廷的组成与分职提供了重要资料,其职掌也有助于认识商周“威仪”观念的嬗变。“典”“仪”在西周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即将到鲁就封的伯禽以此内容为祷告中心,希望职掌威仪的最高权威能护佑他秉持典常、容止合度。
关键词: 四告"帝宾工"威仪
清华简《四告二》伯禽的祷告对象
“祷告对象”这个概念有两重指向,在祭祀礼仪中,存在着为谁祷告、向谁祷告的区别。本文“祷告对象”一词的使用,统指后者。
颇有争议,目前所见有如下几种说法:“帝宾任/工、明典、司仪”三者;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上海: 中西书局,2020年,第109、118页;赵平安: 《清华简〈四告〉的文本形态及其意义》,《文物》2020年第9期。同时,整理报告著录了另一种说法(贾连翔先生惠告此说为他所提出),释“壬”为“工”。
“帝宾任”;
参看陈文娟: 《清华简(拾)〈四告〉集释与初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聊城大学,2023年,第126页;李冠兰: 《清华简(十)〈四告〉的性质及其编撰观念》,“出土文献与《尚书》研究的新开展”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2024年8月。
任、俞两个古族;
程浩: 《清华简〈四告〉的性质与结构》,《出土文献》2020年第3期。
丕显帝。
王宁: 《清华简拾〈四告〉之二读札》,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21年1月30日。
我们认为,第二种说法近是,而“任”应释“工”为胜,“帝宾工”即帝廷掌管礼仪典常的官员,是人间相关官员在帝廷的对应。简文“明典司仪”后置,标明“帝宾工”的职司。“明典司仪”围绕“威仪”“天常”展开,伯禽的祷告以此为主。下面从几个方面说明,请大家批评。
一、 “帝宾工明典司仪”解
为方便叙述,兹先将有关文句释文如下(宽式,下同),需讨论处画线不加标点:
曾孙禽父拜手稽首,敢用一丁脯白豚,先用芳鬯,遍昭祷任,俞告丕显帝宾任明典司仪: 者鲁大神……
对于祷告对象问题,前揭后二说从文本、字形上看都较为牵强,证据不足;整理报告认为是宾任、明典、司仪三者,将“宾任”看作动宾结构,没有说明其具体含义,且似难以解释“祷任”与“告丕显帝宾任、明典、司仪”二者在祷告对象与祷告仪式上的关系;主张祷告对象是“帝宾任”的学者将“任”看作祷告对象的名字,但简文已先说到“祷任”,却没有对“任”的身分、职官做任何说明,反而在接下来的“俞告”环节才点出,在表达上颇觉奇怪。
简文中“任”字所从,有释“壬”、释“工”两说。大家知道,早期甲金文中“工”与“壬”字形相同,应属于一形多用,而楚文字中二者泾渭分明。但考虑到《四告》文字保留有不少存古的情况,单从字形上看,恐难以判断到底如何。近来贾连翔先生通过书手字迹比较研究,提出整理者所释简16的“任”“壬”当释“功”“工”,“祷功”即祈求有功,并指出“宾”与《尚书·洪范》“八政”之“宾”类似,“工”即官,
贾连翔: 《清华简〈四告〉的形制及其成书问题探研》,“古文字与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西湖论坛,中国美术学院,2021年5月29—30日。
很有道理。但“宾工”作为名词性结构,却与“明典”“司仪”这类典型的动宾结构并列,组成三个祷告对象,稍觉扞格。
我们同意释为“帝宾工”。这种释法不仅在字迹上有较强的依据,而且也能很好地通读前后文。至于“明典司仪”,更好的解释是将其看作后置的说明性成分。类似的句式还见于《尚书·酒诰》:
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矧惟尔事: 服休、服采,矧惟若畴: 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刚制于酒。
这里列出一系列被训诰的对象,其中“圻父”“农父”“宏父”后面的“薄违”“若保”“定辟”,皆为动宾结构,标明职司,而语言的焦点仍在训诰的对象本身。这样,本篇的祷告对象就是职掌“明典司仪”的“帝宾工”。
不主张“明典司仪”是祷告对象的学者已指出,这四字是“帝宾任”所担任的职官官号。参程浩: 《清华简〈四告〉的性质与结构》,《出土文献》2020年第3期;李冠兰: 《清华简(十)〈四告〉的性质及其编撰观念》,“出土文献与《尚书》研究的新开展”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2024年8月。但将官号后置的表达较罕见,李文将官号与“帝宾任”并列加顿号也不妥当。
《四告》当具有较为可靠的早期文本来源,学者多已论及。《四告二》“帝宾工”这一名称前所未见,与《四告四》“帝命北方尸”一道,为认识西周帝廷的组成提供了重要资料。关于商和西周时期的“帝”及帝廷的组成与分工、人神世界的关系,学者已有不少研究。
参常玉芝: 《商代宗教祭祀》,宋镇豪主编: 《商代史》卷八,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郭晨晖: 《论商周时期的“帝”与“天”》,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7年;王进锋: 《臣、小臣与商周社会》,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陈彩虹、邓飞: 《甲骨卜辞中的“帝五丯臣”》,《甲骨文与殷商史》新10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403—412页;
宣柳: 《帝廷和下都: 周代“死后世界”的演变》,《史学月刊》2021年第9期;罗新慧《周代的信仰: 天、帝、祖先》,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甲骨卜辞中有“帝工”“帝五臣工”,胡厚宣先生早已指出,工即官,官即臣,他们都是帝之臣、天之佐。
胡厚宣: 《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上)》,《甲骨文献集成》,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册,第308页。另参常玉芝: 《商代宗教祭祀》,宋镇豪主编: 《商代史》卷八,第65页;王进锋: 《臣、小臣与商周社会》,第43页;陈彩虹、邓飞: 《甲骨卜辞中的“帝五丯臣”》,《甲骨文与殷商史》新10辑,第403—412页。
“工”作为职官词的类称,在商周文献中尚有一些用例,比如卜辞、《尚书·酒诰》都有“宗工”,是直属于王家,参与宗庙祭祀、典礼等活动的奔走服侍之人。卜辞“帝宗正”(《合集》38230),应该就是帝廷中的这类官员。
邓飞: 《商代“宗工”考》,《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董珊先生在看过本文初稿后提出,楚公逆钟铭文(《铭图》15500)开头的“夫工”也可以考虑为贤官、贤臣。这可能是“工”作为祭祀对象的又一例子。
商人无法直接与“帝”沟通,因此他们构拟出这些臣属,以祈求满足自己某些方面的需求。西周早期,“帝”的观念与商差异并不大。《四告二》新见“帝宾工”即帝的宾官,应与卜辞中的“帝宗正”、“帝五臣”(《合集》30391等)、《四告四》的“帝命北方尸”一样,皆为帝廷掌管某类事务的臣。“宾工”应该不是一个单一的神灵,而是掌管礼仪制度的神灵群体,《四告二》中“遍昭祷”的“遍”字也透露出这一点。
需要说明的是,“某工”这类称谓,传世文献尚有卜工、乐工、扶工等。《周礼·春官·宗伯》“凡乐事,相瞽”,郑注:“相谓扶工。”贾疏:“能其事曰工,故乐称工,是以《仪礼·乡饮酒》《乡射》《燕礼》《大射》皆言工。”《四告二》的“宾工”,自然与《周礼》等文献记载的“司仪”、诸工这种等级较低的人员不同。
“明典司仪”是帝宾工的职司。“典”,常也,故训多见,当与本篇“天常”有关;“仪”,当与“威仪”有关。西周王朝对“典”“仪”都很重视。《尚书·康诰》云“汝亦罔不克敬典”,《诗经·周颂》亦多次出现“文王之典”,指垂范后世的彝伦“故常”、典章制度。“典”是系统、规范的制度准则,“仪”是应乎“德”、合于“典”的礼仪表现。西周帝廷的这一官职,应是比照人间而设计出来的。
要之,如学者指出,“商代神灵世界里的帝臣有一定的分职,有的帝臣左右商王的祸福,有的任帝的使者,有的为帝的臣工,有的为帝的宗正官”。
王进锋: 《臣、小臣与商周社会》,第43页。
但商代的帝臣主要仍集中在自然神灵,祖先神未被列入帝臣范围。
郭晨晖: 《论商周时期的“帝”与“天”》,第62页。
西周时期大概帝臣的范围有所扩大,由于王朝对宗法、“威仪”的重视,“帝宗正”“帝宾工”一类掌管宗族、礼仪的官员名目或许有所增加。人间擅长某类事务的贤人也常宾于帝廷,相应地担任帝的各类臣僚,如《四告一》所载皋繇担任天帝“司慎”。
赵平安: 《“司慎”考——兼及〈四告〉“受命”“天丁”“辟子”的解释及相关问题》,《简帛》第24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25—31页;程浩: 《清华简〈参不韦〉中的夏代史事》,《文物》2022年第9期;周秦汉: 《论皋陶在两周古史观中的转型与质变——从清华简〈厚父〉〈四告〉到虞廷禅让说》,北京大学第十八届史学论坛,北京大学,2022年4月。
周人对帝廷神灵分职的构想,可能在周初就较为全面系统。《四告》提供了不见于文献记载的西周帝廷神灵官职,尤其值得重视。
《四告二》伯禽在叙述祷告对象时特意强调了其职司,一方面说明他的祷告内容将以此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典”“仪”对其治国理政具有重要作用,这与西周实际情况相符。
这也可以作为《四告二》主体内容时代判断的佐证。但全篇将威仪与求福并提,并且与伯禽个人联系起来,且用词整饬,都未必符合周初的观念及语言习惯,可能更类似西周中期以后的情况。详后文论述。
下面就来分别说明。
二、 从伯禽的祷告内容看“帝宾工”的“明典司仪”职责
伯禽的告辞通篇不离“帝宾工”的“明典司仪”职责。按照我们的理解,伯禽首先向大神说明祷告背景,叙述有周文、武受命戡敌的征伐勋烈,阐明当今周王大分封的形势,并说我伯禽即将受封上任,要举行盛大的祭祷典礼,各方“宾服臣”都来到天子成王处,向您“天子大神”之灵位祭祷:
惠皇上帝命周文王据受殷命,烈祖武王大戡厥敌。今皇辟天子图厥万亿之无后嗣孙,乃建侯,设卫、甸,出分子。今曾孙禽父将以厥圭币、乘车、丁马,丁年、吉月、灵辰,我其往之,宾服臣格于朕皇后辟,典天子大神之灵。
这次“宾服臣格于朕皇后辟”的盛大典礼,可能就是《左传》定公四年所述“殷民六族”“即命于周”的受命大典:
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 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
“即命于周”的“周”,所指当和西周金文中的“周”含义近似。
参赵庆淼: 《再论西周时期的“周”地及相关问题》,《三代考古(八)》,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497—517页;曹大志: 《周原与镐京——关于西周王朝的都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7期。
在封鲁前夕,伯禽受赐“殷民六族”,在周受命,并即将率领他们前往鲁国就职。“殷民六族”的身分与文中所述“宾服臣”相合。
接下来主要就是祷告所求之事,显然以“丕谋威仪”为核心:
(1) 式俾曾孙有濬壮壮,丕谋威仪,宪能礼节,心善揖让,若熙察察,毋变于仪,毋失于恤。
(2) 者鲁大神,之禨若工,唯尔俞秉天常,式文受我厥绪,式尚光明余小子,俾斐斐善善,毋迷于猷,毋愆于图,劝余康娱,宜厥攸同,祗于服御,亹亹答话,节节宜持,进退走揖,""绎绎,和允灵度,祗于攸仪,熙安翼翼,容允孔嘉。
(3) 昊天有好,惠厚被被,式俾皇辟有倬,天子赐我林宝、金玉庶器,鼄赣饔饩,福益增多,勿结勿期,攘去懋疾,毕逖庶尤。
(1)(2)中对于礼仪的祷告内容有重复之处。
《四告》的“告”体与《尚书》“诰”体近似。传世和出土书类文献中王或周公的训诰,常常出现多个“王若曰”“王曰”“周公若曰”“周公曰”,这可以理解为史官对多个语段的记录、整理。《四告二》伯禽对礼仪的祷告前后有重复之处,不应是针对不同的对象祷告。第二次称呼“者鲁大神”之后的“之禨若工”,当如整理者所解,是接续称呼之后褒赞大神的话,相当于训诰的另一段“王曰”。
伯禽所求之事依先后文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 希望“帝宾工”让伯禽在礼仪场合表现得体。这是其“司仪”职司的直接管辖内容,是外在的形而下的可视内容。(1)中“丕谋威仪”“宪能礼节”“心善揖让”“毋变于仪”,(2)中“祗于服御”“亹亹答话”“进退走揖”“祗于攸仪”“容允孔嘉”等都是祈求自己合于礼节、谦恭揖让、进退有度、礼容嘉好。
(2) 希望掌管礼仪典常的“帝宾工”“受我厥绪”,让伯禽“毋迷于猷”,“毋愆于图”,有可以效法的典则,勤恳敬事,不至迷茫,这与“明典”职司有关,是内在的形而上的不可视内容。“之禨若工”“俞秉天常”是伯禽对“帝宾工”神力无边、秉持天常的夸赞。前文已提及,“天常”与“典”有关,侧重典则、纲纪与秩序的构建,“秉天常”正对应其“明典”的职司。“天常”实即天授的“民彝”(彝、典均训常),天神秉天常,人君要秉民彝,上行下效,则“民好明德”(豳公),“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大雅·烝民》)。近来学者对“天常”有所讨论,宁镇疆先生指出,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在于是否“度天心”或依“天德”,而“天心”或“天德”在世间的呈现,就是“天常”。
宁镇疆: 《由清华简〈四告〉相关语词谈古史道统说的传承及知识谱系》,《史学集刊》2024年第3期。
可见天人对应关系。而“威仪”作为“德”的实践(详后),自然属于“天常”的重要部分,由此亦知“明典”与“司仪”职责的关联。
简文中伯禽让大神“受我厥绪”值得注意。绪,常训为“业”,如《诗·鲁颂·閟宫》:“奄有下土,缵禹之绪。”《礼记·中庸》:“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早期文献的“绪”往往包含政治合法性,常用在古史道统语境中,如清华简《保训》:“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商周时期,“帝”的重要职能就是授予/终结国运,
参看郭晨晖: 《论商周时期的“帝”与“天”》,第114—115页。
而作为帝臣的“帝宾工”所秉有的“绪”,当与“秉天常”有着直接的联系,故“秉天常”的大神可以“受我厥绪”。
有学者认为,《诗·鲁颂·閟宫》“缵禹之绪”与叔尸钟铭文“处禹之堵”字面相似而含义不同,前者指禹作为人王的功业,后者与禹的创世神话有关。见姚小鸥、李永娜: 《〈鲁颂·閟宫〉“缵禹之绪”解读》,《文艺评论》2013年第6期。马楠从此出发,认为《四告二》的“绪”应释“堵”,义为土地。按此解似与前文“秉天常”关系不大。见氏著《清华简〈四告〉穆王部分试说》,《简帛研究 二〇二二(秋冬卷)》,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9—14页。
根据我们后文对“威仪”的说明,其早期含义主要在“天威”层面,与“天常”都具有神圣性。
(3) 希望在“帝宾工”的护佑下能让成王多赏赐金玉宝器等物品,自己多增福气,去疾远尤。这是祭祷的一般性格套。学者指出,祭祀合礼,是最初的“求福”规范,后来在祭礼的基础上累加了修养个人威仪的维度。
参谭笑: 《西周铭文中的“福”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四告二》通过向“帝宾工”祷告,最后落脚到“福益增多”,体现了新的“求福”内涵。
罗新慧指出,周人心目中的帝,与殷人相比,具有了赐予“厚福”的新功能。参氏著: 《周代的信仰: 天、帝、祖先》,第100页。学者指出,春秋时期,威仪有定命的作用,可以致福,可以取祸,如《左传》成公十三年“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成公十四年“古之为享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参李丹凤: 《由“上”至“下”: 两周“威仪”嬗变》,《殷都学刊》2021年第2期。《四告二》伯禽告辞通过威仪求福、致福的观念,虽未必早到周初,也不至晚到春秋。
最后,伯禽还提到了“宾众”:
曾子小子拜手稽首,其休,反宾众康吉归,其尚恭尔仪,勿有庶戾,宜尔祜福。
从用辞看,这里的“宾众”,与前面的“宾服臣”可能不是同一批人,是指参加祷告典礼的宾客,可能类似小盂鼎(《集成》2839)中的“邦宾”。这句应当是伯禽祈求者鲁大神也馈赠宾众们“康吉”,这样他们亦当“恭尔仪”(义近西周文献“恭威仪”,谓恭奉你的威仪、仪轨),不要有诸多乖戾,配得上您所赐之福。
“宜尔祜福”的解释参看陈剑: 《简谈清华简〈四告〉与金文的“祜福”》,《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第13辑,成都: 巴蜀书社,2021年,第1—23页;任荷、蒋文: 《清华简〈四告〉及金文中的及物状态动词“宜”》,《出土文献》2022年第1期。
《四告》第二、四篇是伯禽、召伯虎之告,二者皆为朝臣,所告都有极强的针对性: 伯禽曾为周太祝(太祝禽鼎),职掌与礼仪制度有关,封鲁之时其祷辞也多集中于此;召伯虎见先公宗庙有鸱来集,便向北方尸祷告,所祷皆与此异象有关,希望祓除不祥,继嗣祖业。至于《四告》第一、三篇,情况则有所不同。对于《四告一》周公向皋繇的祷告原因,学界已颇有讨论,多认为周公告祭皋繇,与其作为掌管刑罚的“司慎”天神身分有关,希望在刑罚治狱、权力行使方面予以庇佑。
参赵平安: 《清华简〈四告〉的文本形态及其意义》,《文物》2020年第9期;马楠: 《〈尚书·立政〉与〈四告〉周公之告》,《出土文献》2020年第3期。
近来学者对“司慎”的内涵屡有研究,
赵平安、刘晓晗等都将“司慎”理解为司法官员,参赵平安: 《“司慎”考——兼及〈四告〉“受命”“天丁”“辟子”的解释及相关问题》,《简帛》第24辑,第25—31页;刘晓晗: 《“司慎”续考》,《简帛》第26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17—22页;张怀通将“司慎”理解为管理“官德”,选官用人,参氏著《皋陶与〈皋陶谟〉考论》,《历史研究》2024年第5期。
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无论如何,虽然文献有皋陶管理刑狱的记录(如《诗·鲁颂·泮水》“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史记·夏本纪》“皋陶作士以理民”),但周公的祷告目的应从更广阔的王朝视角和现实目的来理解。
参刁俊豪: 《清华简〈四告一〉与周代官僚选用》,《简帛研究 二〇二三(秋冬卷)》,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32—40页。
“皋繇的身分最初并非仅为主刑狱之官”,
罗新慧: 《士与理——先秦时期刑狱之官的起源与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他在尧舜部族联合体中担任高级职务,在佐禹治水、擘画国策、创制律法方面勋业昭彰,
参杜勇: 《皋陶与〈皋陶谟〉》,“出土文献与《尚书》研究的新开展”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2024年8月。
而长官兼管刑狱、政治权威与司法权力两位一体
李峰: 《西周的政体: 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吴敏娜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243页。
在早期社会是很普遍的现象。从简文“骏保王身,广启厥心,示之明猷”“助相我邦国”“懋我王国”“保兹下土”,让成王“毋违朕言,眔余和协”来看,周公之告虽提到“和我庶狱庶慎”、刑狱中正,主体仍是对周王朝治国理政的全方位祈求以及对成王推行自己“既定路线”的苦口箴告。杜勇先生最近指出:
在周公致政、成王亲政后,为了推进国家法制建设,维护天下安宁的政治局面,周公在会同典礼前告祭司慎皋陶,除了祈求神灵皋陶佑助成王,光大周邦事业外,同时意在发挥祭祀刑罚之神的政治教化作用,采取德刑并用的治国措施,内重法治,外征不庭,实施拓土开疆战略,以确保周人统治的长治久安。
杜勇、旷开源: 《清华简〈四告〉所见周公告祭皋陶新解》,《江汉考古》2024年第4期。
这是较为全面的理解。《四告三》穆王满之告,主要针对国家“狱讼无人管理,淫于非常,心好野,以及轻慢神灵”
赵平安: 《清华简〈四告〉的文本形态及其意义》,《文物》2020年第9期。
的现状,希望神“燮懿朕心”(简28)、“宠懿朕心”(简29),恭奉明型,光保王身,用词与周公之告有相近处。四篇告辞,祷告内容和祷告对象之间的关系有同有异,由此引发的关于西周告祭仪式、篇章性质乃至文本编纂等问题,应该予以进一步关注。
三、 “帝宾工”所职掌的“典”“仪”对西周政治的重要作用
伯禽之所以在分封的重大场合下向“帝宾工”祷告,是因为他掌管的“典”“仪”对西周政治生活十分重要。
有学者认为,伯禽的祷告只是关乎个人层面的修身践礼,恐非。见李冠兰: 《清华简(十)〈四告〉的性质及其编撰观念》,“出土文献与《尚书》研究的新开展”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2024年8月。
由此也可反向考虑,可能在商代已进入神灵体系的“帝宾工”,到西周更受重视,并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伯禽告辞提到的“威仪”,学界对其内涵、表现形式、政治功能及演变已有广泛讨论,但《四告二》仍能丰富我们的认知。
学者已经指出,先秦“威仪”的内涵有一个嬗变的过程。“威仪”之“威”,本指天威,与“德”皆来源于上帝或天;“仪”来自“义”,与“威”皆多用于祭祀场合。“威仪”在商代已包含宗教神圣性与行为正确性。
参看蒋文: 《由出土及传世文献看先秦“德”的具象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李雷东: 《历史语境下的西周“威仪”观》,《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桓占伟: 《“燕丧威仪”与殷商亡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但桓氏在讨论《酒诰》“燕丧威仪”时试图撇清“威仪”在礼容方面的所指,我们并不同意。
及至西周,“威仪”与“德”这两个颇有同一性的概念逐步理性化、社会化,成为政治实践中最重要的彝伦规范和行为准则之一,
参看刘源: 《从甲骨文、金文材料看西周贵族社会的“德”》,《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罗新慧: 《周代威仪辨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威仪”在礼容表现方面的内涵渐次凸显。《尚书·洪范》有“五事”,“貌”“言”占据首要位置;清华简《摄命》中王对“司言”的伯摄说“汝威由表由望”,让他“唯恭威仪,用辟余在位”,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上海: 中西书局,2018年,第110、111页。
皆说明了这一点。
罗新慧提出,西周时“威仪”与“德”意义接近,指规则、准绳,并没有容止方面的外在化内涵。春秋时期,威仪开始与言语、动作、风貌等有较多的联系,威仪外在化的特征比较明显。见氏著《周代威仪辨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我们不同意这种辨析。诚然,西周时期“威仪”与“德”有相近的内涵,但其实对礼容的重视不能忽视,如曹建墩所指出,这恰是周人尚文的重要体现,在文献和考古上都有相当程度的反映。参看曹建墩: 《两周社会崇尚威仪之风的兴衰及其观念之演进》,《中州学刊》2018年第11期。
西周文献常把“威仪”“德”并称,西周中期之后,型效祖考威仪之德的记载越发常见,如金文“帅型祖考威仪”(虢叔旅钟)、“帅型祖考丕丕元德”(番生簋盖)、“恭明德、秉威仪”(叔向父禹簋),清华简《摄命》“学于威仪德”,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第111页。
“威仪”内涵逐渐外化、下移,变得具体、可操作,成为“德”的礼仪实践。具有威仪不仅关乎个人的修行践礼,更“成为‘政治合法性实质性来源’的要素”。
谭笑: 《西周铭文中的“福”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北宫文子向卫君言:
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言则而象之也。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可谓则之。文王之行,至今为法,可谓象之。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
这是目前所见先秦人对“威仪”内涵最全面的论述,基本延续了西周时期的特征,《孟子·尽心下》所谓“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综合来看,西周时期的“威仪”包括王室及贵族的政治能力、操守、行为,以及由此展现出的可以为百姓效法的容止、仪法等,其表征是以“礼”规范人的身体,使其周旋揖让、盘桓辟退、陟降上下等行为皆合乎礼节,
参看曹建墩: 《先秦礼制探赜》,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7—228页;曹建墩: 《两周社会崇尚威仪之风的兴衰及其观念之演进》,《中州学刊》2018年第11期。
是孔子盛赞的“周文”的形式系统与价值观念的有机统一。
参付林鹏、张菡: 《先秦的君子威仪与“周文”之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伯禽的告辞让我们看到,“帝宾工”同时掌管“典”“仪”,二者有相当的统一性。虽然《四告二》描述外在的“仪”远多于内在的“典”,但“仪”是在“秉天常”的“帝宾工”“受我厥绪”之后获得的,因此伯禽所获的威仪,仍带有相当的神圣性与原始性,为我们提供了商到西周过渡时期“威仪”观念嬗变的可贵材料。
在这一点上,《四告二》文本仍保有周初的价值观念。
由前引北宫文子之言可见,周文王是威仪之典范,正如学者所指出,“威仪观念的提出,是在反思殷鉴的基础上,以周文王的德行举止为理想原型的”。
付林鹏、张菡: 《先秦的君子威仪与“周文”之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而文王所作“文王之典”(《诗·周颂·维清》《诗·周颂·我将》)、“周邦刑法典律”(《四告一》),恰是周百代仪刑、“万邦作孚”(《诗·大雅·文王》)的根基,膺受天命的文王在此成为“典”“仪”统一的典范。
针对前引北宫文子之言,学者指出,先王事迹是春秋贵族认识“威仪”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雷东: 《历史语境下的西周“威仪”观》,《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其实西周时期已然如此。《尚书·酒诰》用“燕丧威仪”概括殷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殷鉴不远,周初在进行国家制度设计的时候,必然会将认识、宣传文王威仪放在重要位置,《诗经》周初民族史诗与颂诗对文王征伐功烈、政治典则进行大量歌咏,将文王盛德化作可见可承的威仪昭彰于世。《四告二》伯禽在对“帝宾工”祷告的开始,将有周文武成王的盛德功绩进行夸赞,也充分体认到文武威仪之德。
上面所说,是《四告二》反映的“典”“仪”观念承古的一面。另外,应该注意到,伯禽对礼仪的祷辞和《诗经》中描写“威仪”的用词有相当的一致性。
比如《大雅·假乐》“不愆不忘”、《大雅·抑》“不愆于仪”与《四告二》“毋迷于猷,毋愆于图”;《大雅·烝民》“令仪令色,小心翼翼”与《四告二》“熙安翼翼”;以及大量的叠音词如上述篇章中的“穆穆皇皇”(《大雅·假乐》)、“威仪抑抑,德音秩秩”(《大雅·抑》)、“钟鼓喤喤,磬莞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周颂·执竞》)、“有来雝雝,至止肃肃”(《周颂·雝》)与《四告二》“有濬壮壮”“若熙察察”“斐斐善善”“亹亹答话”“节节宜持”“熙安翼翼”,等等。
学者指出,“威仪”在西周早中期的丰富内涵,“在周初颂诗和周民族史诗之外,《诗经》雅颂诗篇中所使用的‘威仪’已反映出分化的趋向。一方面,周人在诗篇中仍然保留了对先祖征伐功烈的祭祀和歌颂;另一方面,《诗经》中所说的‘威仪’,仅仅指动作周旋、礼仪容止”。
李雷东: 《历史语境下的西周“威仪”观》,《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而后者恰是西周晚期到春秋以来威仪观念的重要变化。《四告二》中的礼仪性告辞,也大量出现动作容止层面的内涵,相比商周之际,更显现出新的时代内涵。
不过,在帝廷掌管“典”“仪”的“帝宾工”当然不同于“於昭於天”“在帝左右”(《诗·大雅·文王》)的祖先神周文王。“帝宾工”神灵群体在帝廷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参考商周时期掌管“威仪”的人间官员微史家族:
丕显高祖、亚祖、文考,克明厥心,胥尹叙
“叙”字从吴镇烽、张亚初读。参见《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二)》,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79页;张亚初: 《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 中华书局,2001年,第11—12页。
厥威仪,用辟先王。"不敢弗帅祖考,秉明德,恪夙夕佐尹氏。("钟,《集成》247)
皇祖考司威仪,用辟先王,不敢弗帅,用夙夕。("簋,《集成》4170)
武王既捷殷,微史烈祖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以五十颂处。("钟,《集成》2516)
微史家族作为殷遗民,在周王朝世任史官。"钟说其高祖、亚祖、文考均辅佐“尹”“叙厥威仪”“司威仪”,裘锡圭先生指出,所谓“威仪”就是礼容。“以五十颂处”,就是掌管五十种威仪。微氏家族的正式职务是辅佐史官之长掌管“威仪”。
裘锡圭: 《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
如所周知,周人克商后,任用大批曾服务于商朝的史官。史官家族对殷周文化制度的延续有深远影响。
参看胡新生: 《异姓史官与周代文化》,《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刘源: 《周承殷制的新证据及其启示》,《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
微史家族先祖来投奔周武王所凭借的“五十颂(容)”,应是从商朝继承下来的。周公在《酒诰》中讲到在殷后嗣王,率“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根据学者研究,卜辞多见商王对宗亲、大臣及前来朝觐的方伯诸侯举行飨燕之礼。
郭旭东: 《卜辞与殷礼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第135—138页。
商周的燕礼在仪式程序上也许会有一些新变化,但其性质、功能当一脉相承。
参桓占伟: 《“燕丧威仪”与殷商亡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在朝代更迭之际,史官这一角色很容易被重视“威仪”的姬周政权吸纳、利用。《礼记·乐记》云“武王克殷反商……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郑注:“行犹视也,使箕子视商礼乐之官,贤者所处,皆令反其居也。”箕子“行商容而复其位”,或许微氏家族正在其列。
总之,在周人看来,商朝的覆亡就在于丧失“威仪”,所以在平定天下后,周公首先考虑进行制礼作乐的制度建设,由此奠定了周朝“文”的特色。尔后周人在政治实践的积累中逐步明确了典章化、制度化的法则秩序(即“明典”“秉天常”)与王室及贵族的个人乃至宗族威仪(即“司仪”)对维持西周国家运行的重要作用。而伯禽作为周公之子,在周初大分封的背景下围绕“威仪”、典章向“帝宾工”祷告,毋宁说在宗教意识与人文精神的张力中相当程度开辟了后代鲁地政治生活与管理模式的思想先河。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四告二》的祷告对象是西周帝廷中负责“明典司仪”、掌管礼仪典常的“帝宾工”。被殷周族群共同信仰的“帝”,虽然其神性与作用在商周之际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由“帝”主宰的帝廷构成体系恐怕仍有因袭之处,这方面我们目前还知之甚少。“帝宾工”文献首见,与《四告四》“帝命北方尸”一道,为研究西周帝廷神灵体系的组成与分工、人神世界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天上世界往往是人间世界的投射,《四告二》伯禽围绕“典”“仪”向帝廷对应神灵“帝宾工”进行祷告,其内容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西周时期“威仪”等观念的嬗变及其对政治生活的重要作用。
2021年10月8日初稿
2024年10月24日定稿
附记: 本文初稿蒙黄德宽、赵平安、董珊、马楠、贾连翔、李纪言、刁俊豪诸位师友审阅,多所是正,又蒙外审专家提出宝贵意见,均此致谢!
(责任编辑: 田颖、杨珂)
——孔门威仪观背后的微观身体政治哲学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