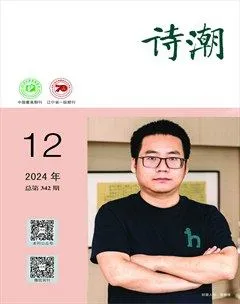海鸥蛋 [组诗]
衣 柜
以前挂着很多衣服
现在少了
以前挂着男装也挂着女装
现在只剩下男装
整理衣柜时
在两件西服之间
发现了
一件白色的女式衬衫
似乎没穿过几次
看不出有任何磨损
纽扣只需轻轻一抹
便能擦掉
一层薄薄的灰尘
我回忆了一下
没有关于这件白色衬衫的任何印象
我想
应该是她的
不会属于第二个人
我随手
又把它
挂了上去
陶 片
少说
也千年了
这枚弧形陶片
属绳纹陶罐的一部分
古人用它
装酒
——应该是这样一只陶罐
底足小
颈微细
中腹饱满
由此我联想到
一位古代少妇
曾经抱着它
从集市上走过
她美得无与伦比
年龄不超过二十三
闻见酒香的酒鬼
因为她的美
鸦雀无声
想到这枚陶片
与一位古代少妇有关
它就不再是
一眼看上去
那么普通了
拉 姆
采集野花时
拉姆的麻布长裙
堆在草地上
她把采到的野花
分送给我们
我以为这是习俗
接花的时候
我恭恭敬敬
那种湖蓝色的花朵
闻起来很香
拉姆很少说话
也很少
直视他人
她是茶卡镇
一个普通牧民家的女孩
和天下所有的女孩一样
拉姆的羞涩与生俱来
区别可能仅仅是
羞涩在拉姆的脸上
会保持得更长久一些
大悲咒
下山时
我应该放低身子
给迎面走过来的僧人让路
不等我表示
看上去比我年岁还高的僧人
侧过身
双手合十
先让我从窄小的山道上通过
锤子与光头
从古玩城淘到一只
民国小铜锤
刚下到五层
电梯里进来一剃光头者
我顿生
想敲一下他的光头的冲动
这个冲动很明确
实在抱歉
我不认识这位老兄
跟这位老兄
也无冤无仇
可是
他的头太光了
太想让人敲一下
白 露
我有办法让自己
穿暖和
一个人居住在
渐冷的屋子里
我有办法
扮演一个爱自己的人
今天是白露
沏一杯绿茶
便见
一根竖起的茶叶
在水中
向我招手
放生羊
从尕尔寺出来
正好看到一群羊
它们在寺院门前的一条坡道
上吃草
当有人告诉我
这是一群被放生的羊
我才把它们
重新打量了一番
并且把它们当作是献给神的
礼物
注视了它们
很长时间
摄像头
大街上的行人
看不到我
但我能看见他们
因为我坐在一扇茶色玻璃窗后
有人打着伞
有人接听电话
有人对着大街在用手指挖鼻孔
会不会有一双眼睛
也在暗处观察着我
而我一无所知
虽然我不能确定
安装在咖啡馆墙角的
那只摄像头是否在工作
但是它
正对着我坐的这个位置
我立刻警觉起来
墓 前
跪了好久
我眼眶里
才隐隐有了泪水
我依然认为
这不是我在哭父母
而是父母
借我的眼睛
在哭我——
哭他们的儿子
面孔沧桑
哭他们的儿子
此生不易
海鸥蛋
——致敬阿巴斯
那种悬而未决的
濒临危险的
不知下一秒
会发生什么状况的
处境
那种被旁观的
不被允许取回来
究竟谁先
被突然暴涨的海水
吞噬的
三只海鸥蛋
在悬崖上
看似静止
实则在微微震颤的
三只蛋
你无法预测
下一秒
它们谁先被海水卷下去
终于
一波更强烈的浪头打过来
将三只蛋
同时卷入海中
至此
三只蛋
有了结果
甲壳虫
一只甲壳虫
在沙漠里快速爬行
是什么力量
驱动着
如果这股力量
放弃了它
同时
也放弃了我
我能看见它
却永远也追不到它
在安福寺
一颗水滴
掉下来
正好掉在我身上
它是从一棵
高大的香樟树上
掉下来的
如果我早一步走过
或者
再迟一步
这滴水
就不会掉在我身上
青花瓷碎片
清水营古城废墟上
偶尔还能捡到
青花瓷碎片
它们是
清代的遗留物
基本还能判断出
71bd8139db08bc2b1a79122f202167a9哪片瓷是盘子的部分
哪片瓷是花瓶的部分
这些年
我捡回来的瓷片
足有数百枚之多
有时我也会分送给友人
并叮嘱他们要好好珍藏
其实,它们是历史的
不是我杨森君的
这就是幻象
猫送走后
每天我都感觉
屋子里
有三只猫
蹿来蹿去
样子就是此前
我养的那三只猫
鱼化石
如果这条鱼正在做梦
那么,它梦见了什么
也许是它的爱人
亿万年了
它被定格在一块石头中
一动都不能动了
它只剩下了
一副残骸
我都能摸到
它的完整的鳞骨
这条鱼
无疑是孤单的
即便它梦到的是另一条鱼
它是实在的,另一条鱼
是虚无的
下马关
一个从宋朝赶来的人
才到达下马关
这是千年后的某个下午
显然,这里的人们
有些诧异
他们奇怪地看着
这个浑身是伤
骑着战马的人
他手持长矛
身披铠甲
他同样用诧异的目光
看着眼前这群人
这时,人群中
一位女子
低头哭泣
她认出了他
他是她前世的爱人
他也认出了她
她是他前世的女人
几经转世
在下马关结婚生子
瞬间
他与他的战马
轰然倒下
除了一堆灰烬
再无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