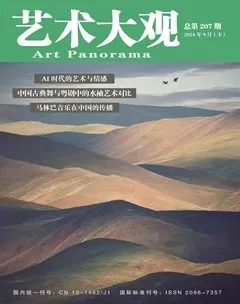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出土半坡四期陶塑解读
摘 要:半坡四期文化作为仰韶晚期的一个文化类型,随着被发现遗址的增多,面貌已经越来越清晰。这一文化类型已经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和陶塑作品,但目前从美术学角度对该文化类型陶器艺术的研究较少。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是半坡四期文化的典型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陶塑作品与同时期其他遗址出土的陶塑作品相比,具有较为独特的艺术风格。本文通过目前已发表的杨官寨遗址出土半坡四期陶塑,分析得出题材传统、塑造技法新颖等特点。
关键词:杨官寨遗址;仰韶晚期;半坡四期;陶塑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357(2024)27-00-03
半坡四期文化是在研究过程中被发现与半坡文化差距较大,从半坡文化中分离出来的一个仰韶晚期文化类型,分布于“晋陕豫的交接地带”,“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600年—前2700年之间”[1]。“张忠培在对半坡遗址发掘报告研究后认为,半坡四期文化是以半坡遗址H1、H10、H12、H108、H161、H309等为代表的遗存。其典型遗址除西安半坡外,还有高陵杨官寨、宝鸡福临堡、彬县水北等。[2]”作为典型遗址之一的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于2014年开始发掘,以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为主,其中半坡四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件陶塑作品,与之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塑相比较,有着较为独特的艺术风格,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但以新闻报道和简短的介绍为主,相关研究目前较少。本文将结合其他仰韶时期的陶塑作品、彩陶纹饰对杨官寨遗址出土的半坡四期陶塑的艺术特点进行分析。
一、杨官寨遗址出土半坡四期陶塑作品
2008年《华商报》对杨官寨遗址出土的两件陶器进行了介绍,其中一件就是半坡四期遗存中带有浮雕大眼睛的陶器残片[3],2009年的《陕西高陵县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将其命名为“高浮雕人面陶器”[4],2011年发表的发掘简报中,除上述高浮雕人面残片,又介绍了两件半坡四期的陶塑作品,一件是残缺的陶环,残余部分有“浮雕的猪面、口、鼻,局部涂有朱砂”[5],另一件是圆雕的陶塑猪首,从发表的线图看,猪面部的各部位清晰,颈部及以下残缺。2017年第15期《丝绸之路》杂志又发表了杨官寨遗址出土的一件在肩部浮雕蛙的头部和前肢的陶釜。4件陶塑中,两件猪形陶塑目前仅发表了简单的线图。高浮雕人面陶器残片和浮雕蛙纹的陶釜曾多次展出,出版物中不乏清晰的图像资料。
(一)高浮雕人面陶器残片
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高浮雕人面陶器残片以其大眼睛而出名,这件残片除一只完整的眼睛,还能看到其左右两侧仅剩一角的眼睛各一只,三只眼睛塑造手法、造型、大小皆相似。从完整的一只眼睛看,眼球凸起,眼睑刻画清晰。两只眼睛之间是凸起的鼻子,各部分的弧度明显,塑造细致。残片一端的边缘是器物的口沿,根据周艳涛的采访,考古人员推测“陶片另外几面的部分应该是对称的[3]”,即两只眼睛中间一个鼻子在圆形的器物外壁循环,无论从哪个面看都是完整的人面。眼和鼻之间的细节塑造考究,使眼睛的两端无论作为眼角看,还是作为眼尾看都很自然,使这类高浮雕人面既显得很写实,又独具匠心。
(二)浮雕蛙纹陶釜
杨官寨遗址出土的浮雕蛙纹陶釜用浮雕的手法在陶釜肩部的一面塑造了蛙的面部和前肢。这件陶釜的口部造型不是圆形,而是在圆形的基础上,将肩部塑造蛙纹的区域对应部分的口部改为内收,“口径26厘米,最大径29厘米,高9厘米”[6],从尺寸可见弧度最大处内收3厘米,显然口沿在此处的内收与浮雕的蛙纹有一定的关系,极可能是为了塑造蛙纹而做出的改变。纹饰重点塑造了蛙的面部和前肢,两只眼睛凸起,嘴巴大而弯曲,前肢健硕,肢端指爪明显,呈蓄势待跳的姿势与神态。整件陶釜除这一浮雕蛙纹外,再无任何纹饰和装饰。
从装饰部位看,陶器的外腹部多见绕器物一周的装饰形式,纹饰或者呈偶数对称分布,或者呈奇数平均分布。像浮雕蛙纹陶釜这样仅一面塑造纹饰的器物较少且特殊,如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彩陶缸,也只一面有彩绘。
(三)猪形陶塑
杨官寨遗址半坡四期出土的猪形陶塑到目前除简报发表的线图外,尚未有详细的图片资料发表,所以不像高浮雕人面陶器残片和浮雕蛙纹陶釜那样有多处报道,从简报的线图和文字描述看,两件猪形陶塑使用了不同的雕塑手法,一件为浮雕,一件为圆雕。浮雕的猪纹在一件残缺的玉环上,玉环为泥质红陶,“残高6、宽5、厚2厘米”[5]。圆雕残缺,残存部分“长5、宽4厘米”[5],目前尚不能分辨这件作品是一件猪形圆雕,还是一件器物的某一部分,简报对这件圆雕猪头的塑造技法评价较高,认为其栩栩如生。
二、杨官寨遗址出土半坡四期陶塑的题材特点
“对题材的选取是真正进入艺术创作的第一步”[7],对于史前美术作品来说,题材也是分析其内涵与创作意图的重要方面。上述四件陶塑作品题材的传统性特征非常明显,都是其前的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的常见纹饰。
史前陶器艺术一直都不乏对人的表现。半坡文化彩陶上的人面鱼纹、马家窑文化和宗日文化彩陶上的舞蹈纹是彩陶纹饰中的代表;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庙底沟文化陶塑人头像、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出土的人形纹彩陶壶是塑绘结合的代表;甘肃省礼县高寺头出土的陶塑人头像、陕西洛南出土的带流人头壶是将器物的口部做成人的头部的器物代表。由此可见,“人”这一题材是黄河中上游彩陶的传统题材,或者选择人体的某一部分,或者选择人体的全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进行塑造、表现。
在黄河中上游史前彩陶纹饰的发展序列中屡被发现,被严文明认为是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的母题之一,是仰韶彩陶的常见纹饰。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一件彩陶盆内壁绘爬行状蛙纹,背上的圆点描绘细致。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一件彩陶盆内壁满饰蛙纹,蛙的头部呈桃形,眼睛作圆点状,四肢很小,网格纹绘制的腹部被夸大。在陕西汉中发现的一块彩陶残片上,绘一跳跃状蛙纹,背部瘦长,后肢粗壮有力。
猪也是新石器时代陶器纹饰和装饰的常见题材,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遗存中都出土过猪形陶塑,半坡文化遗存中也曾发现过多件绘有猪纹的彩陶,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猪面纹彩陶瓶、甘肃秦安王家阴洼出土的猪面纹彩陶壶便是其中的代表。
由此可见,四件陶塑作品的题材都是黄河中上游史前彩陶纹饰和装饰的传统题材,具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涵。
三、杨官寨遗址出土半坡四期陶塑的技法特点
虽然四件陶塑作品的题材具有传统性和传承性,但表现技法从目前有详细图片资料的两件作品看,却是非常新颖的,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写实能力的提高、浮雕技术的提升和对器物整体设计感的重视。
(一)写实能力的提高
高浮雕人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写实能力和细节表现技巧,虽然仅残存一只完整的眼睛和两只较为完整的鼻子,人物的面部特征,甚至表情特征都已经表现出来,也正是因此,该陶塑和以往的陶塑形象相比具有独有的特征。这一特点不仅与史前其他表现人物的陶器纹饰和装饰比较时非常明显,半坡文化彩陶最常表现的鱼、庙底沟文化彩陶最常表现的鸟也没有如此精湛的写实技巧。
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遗存中也有多件人形陶塑出土,引起关注最多的是一件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和一件涂朱砂人面陶器,二者皆用镂空加堆塑的手法,双眼和嘴巴用镂空的方式,鼻子隆起,镂空人面覆盆形器的人面塑造于器物侧壁的一面,双眼和嘴巴皆呈月牙形,从比例看,嘴巴的大小大概是眼睛大小的两倍,隆起的鼻子只能看到一个大概的形状,远没有半坡四期遗存出土的高浮雕人面陶器残片上鼻子的刻画那么细致。涂朱砂人面陶器的人面塑造于内凹的陶器表面,双眼和嘴巴皆呈椭圆形,嘴巴稍大于眼睛,鼻子隆起,同样细节刻画较少,除细长的鼻梁外,鼻子的其他细节都比较概括。而两相比较,庙底沟文化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和涂朱砂人面陶器上的人面形象在仰韶文化陶塑中更为常见。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庙底沟文化陶塑人头像同样用镂空的方式塑造双眼和口部,鼻子凸起,鼻梁细长,其余概括,只是多塑造了眉弓的凸起和双耳,以及绘制的双眉和胡须。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彩陶人头器口瓶,双眼和口部也是镂空而成,鼻子凸起。甘肃礼县出土的人首红陶瓶也是如此。虽然也出土有将眼睛塑造为凸起状的仰韶文化陶塑,如陕西省安康市柳家河遗址便出土过一件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陶塑人头像,眼睛、鼻子、口部皆呈凸起状,但是刻画远没有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高浮雕人面细致,眼睛的形状概括,没有塑造眼睑,不够写实,在塑造手法上差距较大,人面形象差距也非常大。山东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也出土了一件眼睛凸起的人面形陶塑,造型要更加古拙一些。
浮雕蛙纹描绘了蛙的头部和前肢,这种表现方式也体现了写实技巧的提升。其前的蛙纹多表现完整的蛙形,尤其是临潼姜寨遗址出土彩陶盆内壁的蛙纹,不仅将头部、身躯、四肢都进行了完整的描绘,对蛙背部的刺也很用心地进行了描绘,其他蛙纹虽然没有细致到如此程度,也是头、躯干、四肢俱全。流行于半山马厂时期的蛙人纹,因其匍匐状被部分学者认为是蛙纹在半山马厂时期的特殊表现方式,纹饰变化多端,有头、躯干、四肢俱全的,也有省略头部的,还有只描绘一段肢体的,同时也有只表现头部和前肢的,但即使是与杨官寨遗址出土的浮雕蛙纹一样仅描绘蛙的头部和前肢的几例纹饰,二者的表现形式差距仍然很大。在以往发现的史前彩陶蛙纹中,蛙的头部一直都不是表现的重点,而杨官寨遗址出土的浮雕蛙纹,对头部做了重点塑造。这一方面有可能因为蛙崇拜的内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转变,所以从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对蛙腹部的关注转变为对头部的关注,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写实技巧的提高,以往的蛙纹仅表现了蛙的外形特征和非常局部的细节,其他方面的特征都较为概括,而浮雕蛙纹选择了一个较难表现的角度,进行了细节刻画。
(二)浮雕技术的提升
杨官寨遗址出土的浮雕蛙纹选择了与器壁融为一体的浮雕塑造方式,与其前发现的史前陶器相比,也较为新颖。虽然蛙纹在仰韶时代非常常见,但多为彩绘而成,且多绘于盆、碗类敞口器物的内壁,绘于器物外壁的蛙纹虽然有发现,但数量较少,如现藏于远东古物博物馆的一件彩陶壶,在壶腹部外壁以对称的形式绘制了4个跳跃状的蛙纹。浮雕于器物外壁的蛙纹就更少了。不只蛙纹如此,其他纹饰在这之前使用浮雕形式的也很少,在青海柳湾墓地发现的一件浮雕人形纹彩陶壶,曾因其浮雕的表现方式引起关注,与杨官寨出土的这件浮雕蛙纹相比,人形纹只是用浮雕手法对人的特征进行了粗略表现,然后采用塑绘结合的方式,细节使用彩绘的方式完成。其他在外壁装饰动物形象的陶器,以绘制的纹饰和贴塑的纹饰较为多见。将整个器物做成动物的形象,或者将器物的盖、盖钮做成动物形象的作品在史前陶器中也屡见不鲜,唯浮雕发现较少,杨官寨遗址浮雕蛙纹的发现让我们对史前陶塑的认识又加深了一步。
(三)巧夺天工的设计感
从纹饰的组合看,高浮雕人面使用了共生的方法,在两只眼睛共用一个鼻子的组合中,一个鼻子右侧的左眼,同时也是相邻的鼻子左侧的右眼。这种共生方式与半坡遗址出土的半坡文化彩陶尖底罐外壁所绘两个鱼头共用一个鱼身的纹饰、甘肃省临洮县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彩陶盆内壁所绘鱼和蛙共用一个身体的纹饰相比较,又将共生与史前彩陶纹饰常用的重复相结合,形成循环。马家窑文化的鱼蛙共生纹饰是单个纹饰的样式,半坡文化的两鱼共生纹饰虽然有上下两条,也使用了重复的方法,但未能实现循环,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高浮雕人面,则是巧妙地结合彩陶纹饰的共生和重复,形成生生不息的循环。这种循环往复与庙底沟文化被称为“花瓣纹”“勾叶圆点纹”的典型彩陶纹饰的循环往复有些相似,但是杨官寨遗址半坡四期出土的高浮雕人面更简洁,也更有独具匠心之感。
浮雕蛙纹陶釜在器物的整体设计上也体现出了与史前陶器的不同,此前发现的陶器,多是纹饰迁就器型,如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一件绘于彩陶盆外壁的人面鱼纹,为了迁就造型,省略了人面鱼纹头上的三角形。而浮雕蛙纹陶釜是一个整体的设计,器口造型的变化,既为蛙纹留出了更大的空间,又使器物的造型看起来更加精致。
四、结束语
通过对杨官寨遗址出土半坡四期陶塑作品的分析,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半坡四期陶塑的题材以黄河中上游史前彩陶纹饰的传统题材为主,在写实技巧和浮雕能力上,都较前有所提升,对器物整体的设计感也更加重视。但是很多问题也有待更多的资料做进一步分析。如在最初的报道中,浮雕人面便被指出与三星堆出土的人面像有相似之处,其中的关联,目前还无法进行详细分析。
参考文献:
[1]王梓耀.半坡四期文化研究[D].云南大学,2023.
[2]郝文驰.关中地区仰韶时代彩陶的器型、纹饰及相关问题研究[D].山西大学,2023.
[3]周艳涛.陕西仰韶文化遗址考古发现神秘“大眼睛”[J].今日科苑,2008(09):53-54.
[4]王炜林,袁明,张鹏程,等.陕西高陵县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2009(07):3-9+2+97-99.
[5]王炜林,张鹏程,袁明,等.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06):16-32.
[6]刘延久,刘梦.“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精品文物赏鉴[J].艺术品鉴,2019(28):26-31.
[7]王宏建.艺术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基金项目:1.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出土陶器艺术研究”(项目编号:24LW101);2.陕西省教育厅青年创新团队科研计划项目“‘互联网+’背景下陕西传统雕塑文创产品的创新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2JP06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庄会秀(1982-),女,山东临沂人,博士,副教授,从事美术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