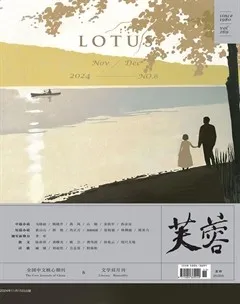富春江山水志
陆春祥,笔名陆布衣等,一级作家,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散文学会会长。已出散文随笔集《病了的字母》《字字锦》《乐腔》《连山》《而已》《袖中锦》《九万里风》《天地放翁——陆游传》《云中锦》《水边的修辞》《论语的种子》等三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北京文学奖、上海市优秀文学作品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丰子恺散文奖等数十种奖项。
千百年来,人们傍富春江为生,河岸与山林,与他们息息相伴。
对地球来说,所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都是客人。弱肉强食,你死我活,并不是最佳生存状态,最好的局面是,各方和谐,相生相安,如陶渊明之桃花源,虽是乌托邦,却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目标。
一、长林堰
我在写历代笔记新说系列的时候,就关注上了任昉,他生活在南北朝时期,与著名数学家祖冲之,都写有同名的笔记小说《述异记》。只不过,祖冲之的十卷散佚了,而任昉的两卷却留了下来。
任昉(460—508),字彦升,兖州乐安郡博昌县(今山东寿光)人,在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三朝,都做过官,廉洁勤政,文学与政绩都突出。这里只说他任职新安太守的一些事。
梁天监六年(507),任昉出任宁朔将军、新安太守,妻儿老小随任。徽州史志如此评价任昉:不事边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辞讼者,就路决焉,为政清省,吏人便之。在郡尤以清洁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户曹掾访其寒温。郡有蜜岭及杨梅,旧为太守所采,防以冒险多物故,即时停绝,吏人咸以百余年未之有也。
对任昉的评价,用词简洁,但几乎都是赞美。不注意衣着打扮(不穿官衣不戴官帽),独自一人(不前呼后拥),拄着拐杖(身体应该不是十分方便),到城镇村舍走街串巷(不坐车,真正深入基层),民间有是非官司,随即就地裁决。这样处理政事,真是既干净又省事,官民都感到很便利。
这是一位真正的“父母官”。年满80岁以上的老人,任太守都要派官员前去慰问。新安郡内的蜜岭,产杨梅,以前产杨梅的时节,官府都要派人去给太守采摘,任昉认为,不能为一己之私让百姓去冒生命危险,立即命令停采,官吏百姓都认为这是百余年没有过的德政。
天监七年,任昉死于任上。《南史·任昉传》这样记载:卒于官,(家中)唯有桃花米二十石,无以为敛。遗言不许以新安一物还都,杂木为棺,浣衣为敛。阖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于城南,岁时祠之。
死于工作岗位上的官员,十有八九都是好官,任昉的生命时钟停摆在49岁的格子上,家里的遗产只有桃花米二十石。桃花米是什么米?是米粒红衣未经舂去的糙米。任昉还留下遗言,不许家人把新安的任何一件东西带回京都。下葬时棺材是用杂木做的,平时穿过的旧衣服做装殓。新安全郡百姓都很悲痛,他们在城南给任昉立了祠,每年按时祭祀这位好官。
那么,长林堰与任昉有什么联系呢?
长林堰在分水江支流前溪河畔,分水西门外(今天英村),一名新堰。它的修筑,与任昉有关,但说法不一。《桐庐水利志》说是任昉在严郡任上下令筑堰蓄水;《杭州水利志》说是梁天监二年(503)任昉镇守吴郡任上令筑分水长林堰。
严郡应该是严州,但这显然有误,南北朝时还没有严郡。南北朝时的分水,倒是属于吴郡,但我查任昉的为官经历,不见他在吴郡任过职,且从天监三年起,任昉一直在宜兴任职。
去天英村走访,天英村微村志上的说法,我认为比较靠谱。
新安郡,当时包括徽州及严州的大部分地区,至少建德、寿昌、淳安、遂安都属于新安郡。而上面已经交代,如此尽心尽职的任太守,一定会跑遍全郡山水,他到分水,从淳安过来,就一两天的事,且分水无论从地理还是经济角度看都是重镇。任太守率相关工作人员,边走边看,一路体察民间疾苦。一日,他行至前溪畔,见河道宽广,北岸又有大片土地,便发动群众修堰。百姓肩扛人驮,先用大量松木在溪中打桩,再在水流中垒砌,建造了长约120米、宽约10米、高约3米的拦河石坝,以此抬高水位,引流灌溉,这就是被后人称为“长林堰”的堤坝。这项水利工程,为杭州市域内最早。
堰坝拦截的溪水,经北岸的引水沟渠(入口处有一人多深),蜿蜒曲折流经分水城区西门外和南门畈的大片良田,滋润着大片禾苗。该畈因土地平展、阳光充足、土质优良,再加上有堰坝引水灌溉,旱涝无忧,年年保收,一直被人称为“金不换”。
长林堰设计合理,坚固结实,沟渠配套,它充分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发展农业生产的智慧、才能和力量。在雨量充沛的季节,溢坝滚滚而下的流水,形成飞瀑,气势颇显壮观。
明朝洪武二年(1369),分水县令金师古,下令重修长林堰。资料表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重修。到了万历二年(1574),分水县令方梦龙,再次大规模组织人员重修长林堰。
按我的推断,任太守发起了这么一个修堰运动,且当时分水还没有建县,他一定会在天英驻留较长时间,一定得等堰坝修筑有了眉目才离开。甚至,每天,他都会在工地上转悠,筑堰的石头、打桩的松木、民工的伙食,他都会指点与关注。如此大片的良田,只有让河水听从调遣,才能有丰收的保证。而让百姓丰衣足食,就是官员的主要职责。
其实,任昉与桐庐的关系,不仅仅是长林堰。他写有两首与桐庐有关的诗:《赠郭桐庐山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诗》和《严陵濑》。前一首长长的标题,里面还有个故事:一个春日,任昉途经桐庐,欲与桐庐县令郭峙(郭桐庐)相见,郭县令见任昉未到,先进村去巡视春耕,任昉等了好久才等到他,于是留下了这首诗。此诗既见郭县令忠于职守,又反映出两人深厚的情谊。
天监是梁武帝萧衍的年号,从公元502年至519年,一共17年时间,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多次提到梁天监这个年号。就水利工程而言,丽水莲都的通济堰,也修筑于梁天监四年( 505),这是浙江省最古老的水利工程,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灌溉工程的世界遗产。
溪中筑坝引水,是南方一带保障农田灌溉的一种有效方式,仅分水江两岸,合村的麻溪堰,修筑于唐朝,沿麻溪右岸悬崖陡壁凿渠1760米,至今可灌溉千亩农田。明朝洪武年间,朝廷专门差官,在分水县境内修筑柏堰、范堰、邵舍、西村、花桥、后岩、云峰、宝山、殿山、长枫、新堰、天目溪堰等十二堰。邵舍堰、西村堰就在我白水老家附近,少年时候的夏日,我们常去那一带的溪中戏水捉鱼,而那堰坝下,有回水潭,往往藏鱼最多,有人也将鱼梁子装在堰坝下,等着鱼从坝上冲下来以拦截游鱼。据民国桐庐《分水县志》,至光绪三十年(1904),桐庐有堰179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分水有堰247处。
堰坝的建筑,大多为垒筑而成的石堰,它的基础,或寻河道中大的眠牛石为基础,或以松桩固定,再以篾笼填石,层叠而成。大溪的石堰,一般在50厘米至2米高,小溪常以柴草沙土等堆筑成浮堰,浮堰易成也易毁。桐庐、分水的民间管理规定,常以小满日闭堰,八月朔日开堰,岁修则管堰者监督管理,受益者如果不出工,则要按亩出谷子代偿。
据《富阳县志》记载,至明成化十一年( 1475),富阳县有堰坝73条,新登县有58条;到明万历七年(1579),富阳已增至86条,新登101条。这些堤坝中,最著名的,便是吴公堤了。
二、吴公堤
富春江富阳段干流长达52千米,因江中多沙洲,该河段多处江道形成南北两支。古代,富春江富阳段修筑防护大堤,主要在县城。唐万岁登封元年(696),富阳县令李溶,在城南用条石修筑防护堤,大堤东起鹳山,西至苋浦,长300余丈,名“春江堤”。唐贞元七年(791),县令郑早又全面整修,并将堤更名为“富春堤”。明正统四年(1439),县令吴堂再次重修,沿堤筑城墙,开四门,建船埠,民感其德,改称“吴公堤”。
吴公堤修完,富阳人陈观,正好从荆州府学教授岗位退休回家,他目睹吴县令带领民众修筑堤坝,就写了一篇《吴公堤记》,全文情真意切,娓娓道来。现在,我们就进入陈观的文章中,去体味600余年前吴县令修堤的壮举。
吴公堤,指的是古代所说的富春江的堤坝,不说“富春堤”而说“吴公堤”,是因为它是县令吴侯所筑,百姓喊它吴公堤,表示不忘本。
富阳县居杭州的上游,它背依山岭,面临大江,江水往下,直通钱塘江。潮水涨落往来,上接衢州、婺州、睦州、歙州,那些河流都会聚集于此。每当狂风大作,江涛汹涌,奔腾的江水就会冲击迸溅,大江被人称为险绝之江。另外,从鹳山开始,到苋浦桥为止,从东到西300余丈,正好处于县城的南部,如果要抵御洪水的话,只有建造堤坝才可以。但历朝历代,那些从政者,似乎都没有想到要研究一下这个事情。
唐代万岁登封元年县令李溶所筑的堤坝,雨洗风淘,到现在,堤坝也损坏了,江流渐渐逼近居民的居住之所,形成了不小的隐患,百姓一天天为此担忧。
明宣德乙卯( 1435)吴县令上任富阳,他首先关注到这条已经差不多废弃的堤坝,感觉修缮的迫切。他召开政府办公会议讨论,认为修筑堤坝是当务之急。众官员一致同意。于是立即打报告,向朝廷申请立项。朝廷很快批准,但偏偏当年收成不好,政府缺乏财力,修堤之事只得耽搁。明正统四年(1439),秋季谷物丰收以后,正要组织人员施工之际,又碰上有关部门要修筑钱塘江堤坝,修钱塘江堤坝,要开凿巨石,征调服劳役者,动辄几千人,但修筑富春江堤坝实在耽搁不得了。吴县令又急忙向上级汇报本县工程的重要性,申请富阳县免除此次劳役,力排众议,这才开工修筑。百姓闻听消息,一片欢腾。
这一年的10月8日,正是富春江的枯水季节,吴县令亲自带领一帮有经验、有名望的长者,遍访工程所涉江边各村,将人力物力逐一落实,石匠、木匠、铁匠、篾匠,能工巧匠们纷纷聚集,巨大的块石、方正的条石、粗壮的木材、长长的毛竹,筑坝材料堆成了小山。
吴县令又传授了新的筑坝方法,将其定为三个层次,下面用木桩打底,上面用石块堆叠。任务分配井井有条,责任落实清晰而精准,两个月时间不到,堤坝就筑成了,上坚下固,犹如天然生成那般。
堤坝竣工那天,富阳百姓说:这里过去是富春江水的要冲之地,现在却成了我们安居乐业的好地方。这是靠谁的力量呢?这是靠吴县令的力量啊。换言之,这一切,都是托吴县令的福。随即,百姓们要求,将此堤改名为“吴公堤”。
写到这里,陈观不禁自己也跳将出来,拍着桌子说:确实应该改名。
接下来,陈观更加思绪勃发,他对吴县令带领民众修筑堤坝这件事,十分感慨。他这样想:政府主导的大工程,需要用大量的民力,但只要事情有利于民众,百姓即便劳累也不会抱怨。此项工程,虽然时间紧,质量要求高,但吴县令将它一一落实,百姓高度配合,如此看来,吴县令是真心为民,而不是沽名钓誉。—个地方因一个人而命名——以前,苏轼任杭州知州,疏浚西湖造堤坝,这一堤坝被百姓赞为“苏堤”;现在,我们富阳,将堤坝命名为“吴公堤”——个中道理是一样的,都是对官员为民办实事的褒奖。
县令全名叫吴堂,字允升,饶州乐平人,他从进士开始进入仕途。他修吴公堤,使富阳境内景象焕然一新。
陈观断定,今后,人们想起吴县令之功绩的时候,一定还不止这些。意即用他姓氏命名这样的事情,还会再发生,不会仅限于这样一座堤坝。
陈观感叹完,陆布衣也感叹,中国百姓是多么善良,那些官员,只要为民做了一丁点好事,他们都会将官员做的事,用官员的姓名命名,不少还会替官员生前立祠,百姓做这一切,就是想永远记住官员的恩德。
甲辰春日的一个下午,我看完郁达夫故居后,沿着滨江大道往南随意行走。江风从阔大的江面上不时拂面,亭台楼阁错落有致,树木花草随风摇曳,鹳山公园、东门渡、南门渡、下水门,这些都是久远的历史遗存,这吴公堤延伸到此的下水门遗址,已经复建成一个码头了。
在南门广场,我细看富阳老城地图的铜雕,那些线条,深深地镶嵌进铜壁中。我知道,其中任何一条线,都可以拓宽并连接起几百上千年的时空,且与眼前的江水互相激荡,奏出富春江的时间之歌。
三、耕织图
公元前44年,凯撒打败了所有的对手,成了罗马帝国的首席执政官。喜欢讲排场的凯撒.随即在罗马大剧院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演出。
众目睽睽之下,凯撒在左右官员的簇拥下隆重出场。一身精美绝伦的紫色宽袖长袍,质地轻柔,衣角不时飘扬起来,凯撒张开两袖,感觉好极了,他不断向民众挥手致意,如大鸟一样张着翅膀。贵族们不知道,凯撒的这身轻盈羽衣,来自遥远的中国。此后,中国丝绸在罗马被追捧,价格最高时,一磅丝绸可卖十二两黄金。
其实,我们的祖先,4000多年前就开始生产丝绸了。中国的丝绸被西方人发现,惊为天物,古希腊及古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意即“丝国”。越王勾践被吴王放归后,他与谋臣计倪的一次对话中,就确定了“省赋敛,劝农桑”的国策,并“君自耕,夫人自织”,带头开发耕地,发展蚕桑,推行农战政策。那时,作为经济作物的桑树,已被百姓广为栽植。
《梁书》卷五三记载,建德县令沈瑀,教民众“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咸欢悦,顷之成林”。百草初长,春水荡漾,新安江、富春江畔,民众初尝各种经济作物带来的好处,尤其是蚕桑种植之利,山与林与水,和谐相处,百姓欢歌阵阵。
天目山下,天目溪畔,有个於潜县。
南宋时,於潜就成了京畿之地,距京城临安不过百余里地。天目山下有数十家窑场,生产大量的日用瓷器.而天目溪两岸河谷,土地肥沃,良田连片,桑园成畴,这里皆为粮食与丝绸的重要产地。所出之物,在於潜县北的后渚桥码头装船,一路顺水至分水江,再人富春江,一两天即可抵达京城。
南宋绍兴三年(1133),惊魂未定的赵构,终于率领众官员在临安城安下身来,此时,大宋江山已被金人撕得支离破碎,赵构们苟延残喘。然而,江南的土地还真是养人,没多久,临安城就呈现出暖风醺得游人醉的大好局面,而就在这一年,四十三岁的楼璃,出任杭州府於潜县令。楼璹是宁波人,出身书香门第,写诗作画皆擅,当他来到这富饶的河谷之地时,就决心要让百姓丰衣足食,“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宋楼钥《攻娩集》)。
似乎是在不经意间,楼璹完成了世界农业科普史上的一项壮举。
《耕织图》的横空出世,将中国农耕蚕桑的生产全过程,完整形象地向世人展示了出来。这是农事生产的全过程,这亦是诗与绘画完美结合的艺术,有人将《耕织图》与后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合并称赞,称它们皆在中国绘画史上立下了里程碑。
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淤荫、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簸扬、砻、春碓、筛、入仓。水稻生产,从浸下种子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千辛万苦万粒归仓,共有二十一道环节必须完成,每一道环节,楼璹都形象地配了耕图诗,我们看第一首《浸种》:
溪头夜雨足,门外春水生。筠篮浸浅碧,嘉谷抽新萌。
西畴将有事,耒耜随晨兴。只鸡祭句芒,再拜祈秋成。
连日春雨沥沥,溪头的水开始涨起来了,农人看看天气,将上一年的种子小心地从梁柱上取下,将早就备好的木桶放满清水,再将谷种小心地淘洗,依然有瘪粒,必须清除。浸下谷种,就是埋下希望。这些好种子,很快会饱满起来,它们钻出谷壳,那柔柔的嫩嫩的绿芽,惹人欢喜。做完这些,农人的心里稍稍安定下来,他拿出一袋烟,点上,坐在灯下,想着后面的一些事,这些事必须一件件去完成,每一年都这样,已成习惯。西边的那几块田,好好整理一下,特别是那块秧田,过几天就要将萌芽的谷种撒进秧田中。另外,春耕之前,一定要祭拜一下神灵(春神句芒),那只大公鸡,可是养了好几年了,足够肥壮。这一切,都是为了心中那个希冀,期望今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再如第九首《插秧》:
晨雨麦秋润,午风槐夏凉。溪南与溪北,啸歌插新秧。
抛掷不停手,左右无乱行。我将教秧马,代劳民莫忘。
小麦旺,槐花繁,初夏之风习习,而天目溪河谷两岸的田野上,田边人们唱着小曲挑秧丢秧,田间人们弯着腰不停地插着秧,农人虽万般辛苦,劳动场面却也是嬉笑谐侃,玩笑照样开,种的秧却一点也不含糊,笔直不乱行。而这个时候,那楼县令,亲自下田来了,他推着秧马(宋朝发明的如木头船的坐具,上面堆满秧,用手脚滑动退后),告诉农人们说:大家可以使用这种秧马,看看,减少上下田次数,速度也可以加快!
蚕从下种起,一直到织出丝帛,依次有浴蚕、下蚕、喂蚕、一眠、二眠、三眠、分箔、采桑、大起、捉绩、上蔟、炙箔、下蔟、择茧、窖茧、缫丝、蚕蛾、祀谢、络丝、经、纬、织、攀花、剪帛二十四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一幅图一首诗,比如《一眠》诗:
蚕眠白日静,鸟语青春长。抱胫聊假寐,孰能事梳妆。
水边多丽人,罗衣蹋春阳。春阳无限思,岂知问农桑。
沙沙沙,蚕不停地吃着桑叶,饱了,蚕宝宝要睡了,而如同“蝉噪林逾静”一样,暖阳映照,蚕宝宝果真睡着了。鸟在窗外,不时地鸣上一两声,不知道蚕宝宝要睡多久,它们是醒了吃,吃了睡,它们的世界,就这两样事。在这大把的闲暇时光里,人们都会干些什么?农人自然要忙于耕种、忙于养蚕了,而那些闲着的富人贵人小姐,却去闲游了,去水边,去山里,春光无限好,丽人多玩耍。她们有无限充裕的时间,她们根本不会考虑农桑的辛苦之事。
楼璹实在是悯农,否则不会如此仔细地绘出耕织图,还一首首地配上诗,他希望大地与河流,生金生银,他希望他的《耕织图》能对农人粮食生产及丝绸纺织有帮助,他希望天下的百姓靠勤奋地耕织而丰衣足食。
山水默默,田地默默,但它们都尽量配合着守时而勤快的农人,憋着劲在酝酿,酝酿着一场天地间的朝气蓬勃。
四、禁棚户示
清嘉庆六年(1801),浙江巡抚阮元,发布《禁棚户示》,禁令中明确要求,实行计划垦殖,禁止乱开垦,以防水土流失。
“棚”是什么?
明清时期,浙江本就不大的面积,土地利用已是比较充分,但浙东、浙南、浙西,特别是沿江两岸地区,依然有不少的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的客家人涌入。仅就湖州府而言,太平天国战乱后,河南、湖北、苏北、皖南及浙江本省上八府等地客民纷纷迁入湖州府下属各县,至光绪十五年(1889),至少迁入12万人。这些新人浙江地界的移民,有不少就往人口稀少、基本没有战乱的山野里钻。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垦荒,砍树烧炭,开荒种粮,大量种植玉米。
道光年间,有这样的记载:
近来异地棚民盘踞各源,种植苞芦,为害于水道农田不小。山经开垦,势无不土松石浮者,每逢骤雨,水势挟沙石而行,大则冲田溃堰,小则断壑填沟。水灾立见,旱又因之。以故年来旱涝濒仍皆原于此。(见曹树基《清代前期浙江山区的客家移民》,《客家学研究》第四辑)
一户或几户人家,砍树搭棚,就近安家,他们要生存,基本不顾生态保护,伐,伐,伐,只要能卖钱,只要能种玉米、番薯。他们砍树,不间株,只伐不植;他们开垦,不管坡度。这些人,以山为生,他们就称为“棚民”。
夫山水同源,山有草木,然后能蓄水。种苞芦者,先用长铲除草使尽,迨根菱茁壮,拔松土脉,一经骤雨,砂石随水下注,壅塞溪流,渐至没田地、坏庐墓。国课民生,交受其害。且山川灵气,斫丧已尽。(《光绪分水县志》卷一邑人陈景潮《开种苞芦利害论》)
大量垦荒,一些森林,在短时间内消失殆尽,一片片荒山秃岭,在没有植被保护的情况下,一遭雨水冲刷,便泥沙俱下。下流河川因此迅速淤塞不畅,发生水灾的频率增加。另外,大量泥沙,被雨水冲到平原上的良田中,致使耕地缓慢沙化,生产力严重下降。可以这样说,清代的大规模开荒运动,给中国带来了数百年也难以复原的大灾害。翻检史籍,各地都有对棚民开荒伐木的详细描述。
山林是河流的保护神,其实,在阮元之前,各朝政府也是注重保护的,也发布过不少类似的禁令。
比如,明朝嘉靖十五年(1536)五月初一,官府在於潜县西天目山南麓朱陀岭顶红庙边立禁碑,禁止开挖朱陀岭银矿,以免毁坏山林。
山高皇帝远,阮元发布的禁令,作用估计不太大,垦荒者还是我行我素,浙江的山林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嘉庆十九年(1814),嘉庆帝谕告军机大臣:浙江各府属山势深峻处所,多有外来游民租场斫柴,翻掘根株,种植苞芦,以致山石松浮,一遇山水陡发——大为农人之害——不可不严行禁止!
嘉庆帝还特命奕畴察看浙江山情,勒令棚民退山回籍。
结果可想而知,政府抓严了,棚民就会收敛,政府一放宽,山林间照样就会有人去垦荒,这种生存与保护的矛盾,一直持续数百年。到后来,不仅有政府,还有民间的自发保护,因为百姓自己也认识到,如果不保护好山林,那江河就会不听话,而遭殃的就是自己。
杭州市域内,近代最早的民间森林保护组织,出现在新登县。光绪二十五年(1899),该县塔山乡的元村、炉头、东山、阴山四庄,联合成立禁山会。禁山会的作用极大,在这些庄,山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他们还数代人承传。1948年,禁山会更名为四庄联合保护森林作物委员会。在这四庄人看来,山林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一切所需,皆产自山林,自然要保护好。
1915年7月,北洋政府定清明节为植树节。
1915年9月,浙江巡按使公署发布训令:设立森林警察,以重保护。
1917年8月,浙江省立甲种森林学校在建德梅城成立。而森林学校,当时全国仅三所,除浙江外,还有江西之庐山、辽宁之安东。
1924年7月,浙江省政府决定,省立甲种森林学校改组并入杭州农校,在森林学校的旧址上成立浙江省立第一模范造林场,山林、圃地、房产全部划归林场,这就是建德林场的前身。
甲辰三月,陈利群、沈伟富兄,陪我去梅城乌龙山麓、富春江边的建德林场。建德林场从1924年成立至今,刚好100年。建立林场的目的,除首创国有林场外,无非是为科学造林树立榜样,这就如同的黄埔军校,培养军队的种子,以便军队快速发展。
从建德林场的发展历史看,有两大事件值得一说。
一是日军侵华时期,建德林场曾遭受历史上的最大劫难,森林资源与房产物资均严重被毁。1942年5月,日军大举窜扰浙西一带,建德沦陷,日军占据梅城后,在城内外要冲地区,修筑防御工事,所用木材均在乌龙山林区砍伐。林场办公室被日军占用,所有房屋的门窗、板壁、地板等,均遭破坏。同时,日军还在乌龙山顶海拔959米高处,筑一炮台,为防游击队的袭击,他们将山峰周边的大片林木尽行砍去。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时间,有30多万株成年树被砍,建林场以来营造培育的森林资源精华,被严重损毁。
二是富春江水电站建设时期,为保护富春江两岸的水土,水电站库区建德移民的9万多亩荒山林地,划归林场经营管理。而随后,建德林场开展了大规模的荒山造林行动,3.7万亩以杉木为主的用材林迅速生长,为涵养两岸的水源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成了拱卫富春江水电站的生态屏障。
我们坐着观光车,从富春江边的芳草地酒店起步,沿山脚绿道,在森林中穿行。时而遇见行走歇脚的背包客,梅花一大片一大片地开着,梅香扑鼻而来。从林荫道的树缝间,偶尔可以瞥见江中平静的水波,碧绿怡人双眼,七里扬帆,葫芦飞瀑,子胥野渡,人群熙熙攘攘,山峦叠翠,峰岭锦绣。
建德林场的傅国林场长告诉我,全场现有林地面积11.43万亩,其中国家级生态公益林面积7.17万亩,2016年森林蓄积量达到81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89.3%。境内分布有野生和栽培的木本植物642种,构成了现有的植被类型。
在子胥野渡,我伫立观水,遥想伍子胥当年的传奇,然后闲闲地坐在草地上,细观对面的森林层次。那高大的马尾松、笔直的杉树,显然属于乔木层;那正起劲开着花的杜鹃、继木、山茶等,应该都是灌木;江南的森林,自然少不了给山铺底的蕨类植物;还有各种茅草,这些应该都是草木层。再细瞧,岩石下,甚至脚边,都有一丛丛的苔藓,它们是山与土的黏合剂,是森林蓬勃旺盛的标志。
一行人闲聊林场,基本上是我问,傅国林答,陈利群、沈伟富补充。
说起富春江中放木排。1978年,乌龙山采伐松木、杉木3000多立方米,扎成木排,从这里下江,过七里泷,再过水电站的行船通道,一直到桐庐、富阳,再到杭州。那成片的木排,一片一片,将整条江都要盖满,很壮观。
说起索道运木。以前林场伐木,都是通过架设空中索道运送下山的,乌龙山索道全长2300米,两根钢索,如高压线一样架着,顺着山势走,将那些木头,用铁丝捆住,吊在钢索上,然后,一捆一捆滑下山来。
说起以前林区的文化生活。放电影是最主要的,大家赶来赶去看,反复看,放电影的日子,如同节日一般。20世纪七八十年代,林场购置电影放映机,先是8.75毫米,后换16毫米,放映员翻山越岭下林区,每月要放电影20场以上。
说起以前林场的收入。傅国林扳着指头说多种经营:苗圃,家具厂,纤维板厂,养鸡场,汽水厂,茶厂,五加皮酒厂;养蜂,水蜜桃,黄花菜,美国薄壳山核桃。闻此,我们似乎异口同声:靠山吃山。
头上偶尔有飞鸟掠过,白云慢悠悠地走着,山水静静地听着我们的谈话,它们以博大的胸怀容纳着人类的一切。山与水,其实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五、绿树村边合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孟浩然为我们描绘了理想的田园生活,绿树环绕,青山横斜,人行进在郁郁苍苍的绿道中,犹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而富春江两岸,支流的支流,只要有村庄人家,一般都有绿道,就是孟浩然诗意的再现。
七八十厘米宽,塑胶跑道,红蓝相间,人踩上去软软的。或者是条石、块石,甚至鹅卵石铺成的,沿着江,绕着水,与碧波为伴,与青山为伍。人行其间,犹如小船荡漾在平缓的水波上,任意东西。
我在富春庄醒来的时候,常常是天未明,窗外鸟儿就叽叽喳喳闹个不停,我甚至都能听见它们在院子里唰啦唰啦乱飞的声音,枫叶丛中,杨梅树上,喜树林前,它们就这么窜来窜去,毫无顾忌。
晨光大亮,出发早锻炼。我的路线一般有两条。往右,进山,大奇山,行十来分钟,前面就是大奇山国家森林公园门口了,立即往左转。曲折行几百米,豁然一个溪旁水库,伫立一会,看整库碧玉般的水,看山峦倒映碧波中,这个不细说,我专门写过《寨基里的大奇》,大奇山也叫寨基山。
我重点说另一条往左的路线。出停车场,正对着巴比松米勒庄园走数百米,至庄园口,左转上坡,也是往山里去,路边的紫薇花、梨树、葡萄,还有水塘,陪伴着你一直上坡,一只大金牛正对着你,这就到金牛村地界了。
还须再说明一下的是,无论往左还是往右,这里都属于一条大绿道——大奇山风光带,10.17千米,上标“浙江省1号绿道”。我在杭州,住拱宸桥边的左岸花园,出门就是大运河,而运河边的绿道是“浙江省2号绿道”,可以这样说,我的行走,不在1号绿道,就在2号绿道。浙江省有多长的绿道?AI告诉我,有1.7万千米。绿道已如绿带,将山与水与人紧紧相连。
转一个“之”字形的大弯,右边有一大片草地,路旁靠山有“遇见”两个大字竖着。草地遇见你,你遇见草地,都说得通。现在,我还不能停下,还得往里走,穿过桥洞,就是一个村,精致的屋舍,三三两两,在山边上错落,看标牌,有不少民宿,这是金牛村的岩下自然村。岩下,岩没见(大奇山上应该有巨岩),各式古树倒是林立,磡头上那一棵大樟树,显然是岩下村有些年份的证明。
金牛村坐落在大奇山南麓,有童家、岩下、大塘、大元四个自然村,450余户人家,它的历史都写在道旁右边的长廊中。长廊上说,这个村的张姓先辈,明朝正德年间就来此居住了。不过,我相信,大奇山这一带的人文历史其实更悠久,元朝诗人何骥之《咏金牛山绝句》有这样的诗句:“奇峰探古寺,披雾上云程。”“人烟俯视小,禅宇仰观清。一饭同斋牛,时闻钟磬声。”云雾缭绕,古寺深藏,游人三五穿行,寺庙中,一干人正端碗举筷,忽然梵音阵阵,飘进耳中。
穿长廊,就到金牛公园。公园不大,几乎是微型,由一座小山包营建而成。小山脚,是几棵几百年的古樟,晨阳中,树身朝东的一面,虬枝以蓝天为背景,在天空中构建出一具强大的骨骼。往山上行,有数棵松树,精干巴瘦,那些松树的枝条却夸张,几乎不受约束,肆意伸向天空。山顶有一小亭,亭边有松丝落叶,看木栏起皮的座位,坐的人应该不多,我来过数次,没有碰见过其他人。
那边的知青馆,很想去看一看,只是,我每次来时都是清晨,田野里有农人在菜地侍弄,但馆不会这么早开放。我看菜地里那些挥锄耕作的身影,立刻想到知青,那时的知青,就整个桐庐范围来说,有不少都下放在相当偏远的深山里,到金牛村插队的50多位知青,从地理位置上说,应该算幸运。
折回的路上,遇见“遇见”,这片阔大的草地,必须去打个招呼。
所谓的草,全是人工种植,草的学名叫“粉黛乱子草”,株高可达一米,花期在9至11月。此草的花絮,会生云雾状的粉色,成片种植,可呈现出粉色云雾海洋的壮观景色。既然是草,一般都有花语,粉黛乱子草的花语为“等待”。哈,看出种植者的心思了,这里要营造的不是一般的“遇见”,而是爱情,等你,这是以爱情为主题的花园。
粉黛乱子草的田野,几十亩大,有一对相邻的大稻草牛站着。金牛村嘛,必须有牛,“牛”们屏息敛声,它们似乎也有等待。几个取景台的造型别出心裁,“520”“1314”,大家都懂。我想象着,仲秋过后,要不了几天,这里就会人头攒动了。周杰伦在另一头的田边高歌:不要你离开,回忆划不开,欠你的宠爱,我在等待重来。
往回走到岩下村口,每次都看见路边停着一辆三轮车,车上挤着几只大桶,桶中有水、有肥,边上有一菜地,一位老年人,长衣长裤,头发半秃,正躬身菜地,有时除草,有时铲地,有时摘菜,没见他歇手的时候。我知道,白菜、豆角、黄瓜、茄子、秋葵、萝卜苗,所有的菜都在等他培育,他也天天在等菜的成长。
一个多小时后,我回到富春庄,虽一身大汗,却全身通透。几只小松鼠正在C楼文学院门前的雪松上追逐跳跃。我不打搅它们,悄悄进厨房,煮一碗饺子。我将饺子端往D楼文学课堂门前的老樟墩子上,一边吃饺子,一边看树上玩耍的松鼠们,忽然,低头抬头间,它们一闪身,不知蹿到哪棵树上去了。
小松鼠们能闻着粉黛乱子草的花味,去那片大草地玩吗?念头一上来,就暗自笑了,为什么不可能呢?乱子草苍苍,赤雾迷茫,所谓伊鼠,宛在山中央。
富春山水时刻在给予我们恩惠。
古往今来,富春山风,富春江水,治愈了无数焦虑的灵魂,且这种焦虑,经山水的浸染,大多演化成了悦耳动听的诗与文。望峰息心。窥谷忘返。面江,俯身,随手撩起一捧水,都是7000多首诗文碎句的清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