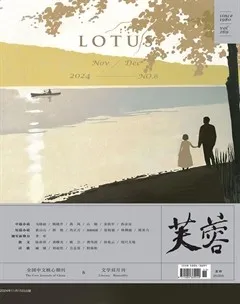曹状元街
冉正万,1967年生,贵州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银鱼来》《天眼》《纸房》《白毫光》等九部。出版小说集《跑着生活》《树洞里国王》《苍老的指甲和宵遁的猫》《唤醒》等八部。曾获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一等奖、第六届花城文学奖新锐奖、第六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长江文艺短篇小说双年奖。
良洪2004年从二戈寨搬到曹状元街,其时武侠小说和电影日渐式微,远不如十年前流行,人们对正在热播的武侠电影多持负面批评,指责它们缺乏精神价值判断,艺术灵魂空洞,只有画面不见故事。这对良洪没任何影响,他要的不是花拳绣腿。曹状元名叫曹维城,是武状元,康熙四十二年(1703)武举殿试第一名。良洪特别仰慕,搬到曹状元曾经住过的地方,仿佛可以得到梦寐以求的东西。良洪的脸圆圆的、憨憨的,像个罗汉,见到熟人先送出谦虚的表情,一副找不到话说的样子。见陌生人时面相有点凶,其实他不凶,是他心头莫名地胆怯,怕被误会,怕被伤害。和陌生人打完交道,总是忍不住暗想,我要是会功夫就好了,露一手。觉得只要会功夫,不管是陌生人,还是想对他不敬的人,都会立即敬他三分。在旧书市场淘得一本《鲍家拳拳谱》,已经悄悄练了一阵,被他的油汗浸泡过的拳谱几近透明。有时觉得套路已经完全掌握,只缺实战。有时觉得问题还不少,尤其连贯起来不顺畅,没有行家指点,有可能是瞎练。他要的是一旦出手,人家就知道他是顶级高手,而不是在做广播体操。周末在万东桥下跟卢老师学习书法,卢老师夸他有天分,有悟性,笔下有味道。说他用笔像宋人用钩镰枪,轻重缓急得当,“别看他跟我学,有时我在跟他学”。良洪一惊,担心卢老师窥破他独自练拳的秘密。当街露两手很骄傲,悄悄练拳却感觉丢人。
搬到曹状元街之前,良洪在一个出版社的仓库当勤杂工。不但承担出库入库装车下库所有重体力活,制作报表替读者找书等零碎活也是他在做。他是临时工,正式工最重要的工作是打麻将。辞去这份工作不完全是心理不平衡,主要是想住在有武术气息的地方。武术气息只有他一个人能感觉到,在其他人眼里,这就是一条很普通的小街,两百多米长,一头是联通商城,一头是富南小吃,中间加一个吃酸汤鱼的快活林。心细一点的还可加上银行、小旅馆、建新小区、爱丝尚造型和家宴食府。
在曹状元街住了两年后,他让妻子也从仓库辞职,来下护国路开粉馆。妻子姓罗,很会做吃食,又热情好客,仓库其他零工的孩子叫她罗姨妈,粉馆于是叫罗姨妈鹅肉粉馆。
粉馆开张后,良洪早上五点起床,步行到油榨街,乘第一班公交车去二戈寨买鹅。二戈寨离城区远,鹅比就近买便宜。每斤便宜三角钱,两只鹅可以省四块钱。他认为没必要,坐公交要一块钱,何必呢。一说出来,罗姨妈气得咬牙切齿,“你的钱硬是多得很”。他不服气,心想罗姨妈就是固执,什么都离不开二戈寨,真是二,二戈寨的二。
出版社仓库在二戈寨一片竹林当中,背后是图云关和龙架山两个森林公园之间的绵绵不断的山脉。他和罗姨妈在这里生活了十年,罗姨妈确实舍不得离开二戈寨,她不光熟悉围墙外面的核桃树什么时候开花结果,连半坡上开荒种菜的农民都认得,和街边旧门窗收购店、旧棉絮翻新店、汽车修理厂的老板娘都是好朋友。来到曹状元街,她一个人也不认识。“二戈寨那些人,以前你也不认识呀。”“是不认识,可是只要你搭白,人家不会不理你。”也是,住在楼房里的人不喜欢和刚认识的人聊天,不像住在地上的人,互相没什么好隐藏,一点不介意自列于众。
罗姨妈认为二戈寨的鹅不光便宜,还没注水。良洪问:“你怎么知道他没注水?”罗姨妈说:“他敢,认识他都十几年,我怕这点人情都不讲。”良洪不想纠正罗姨妈纪年有误,用贵阳话反驳,“熟人整熟人,整起逗得行”。贵阳人把“就”说成“逗”,罗姨妈听着“逗”字就不高兴,这是一种就范,她以极快的速度切蒜苗,“他敢整我,我不把他从上街日映到下街”。
良洪不敢再斗嘴,怕罗姨妈切到手指。罗姨妈辞职来开粉馆,心头挣扎了一年。出版社仓库收入不高,但稳定,住房和水电都不要钱,辞职需要巨大勇气。良洪缩起两片厚嘴唇埋头干活。不多一会,眼前一切消失,他已行走江湖,是世人敬重的武林高手。干到下午三点解下围裙,余下的活留给罗姨妈,罗姨妈要忙到五点才能离开。罗姨妈以为他起得早要回家睡觉,其实是回家练拳。练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罗姨妈。周六和周日下午去卢老师的书法班学习,只有这两个下午才有成人班。
罗姨妈鹅肉粉馆是卢老师题写,遒劲饱满,与其他面馆粉馆相比,多几分文气。吃粉吃面的人不看重这个,甚至连看也不看,只看好不好吃。
当一万多只鹅被良洪拎到下护国路,他和罗姨妈还在卖鹅肉粉。一万多只鹅作为里程碑,记录下来的大事不多。曹状元街建新小区的房子买了下来,去二戈寨不再赶公交,骑电动摩托,卖鹅的人已由儿子接替父亲,卢老师题写的匾额被熏得看不出颜色,“妈”字“鹅”字各剩一半:罗姨马我肉粉馆。
里程碑记下的另外两件大事良洪和罗姨妈都不想说,尽量避免。马航失事那年,他告诉罗姨妈,他要去武当山。失事飞机上有两个贵州人,一对老夫妻,良洪见过他们一面,老先生是书法家。一个活鲜鲜的人,说没有就没有,再不去来不及了。罗姨妈问他去武当山干什么,“你不要管。”他说。“去好久?”“不一定。”罗姨妈以为他要出家,觉得出家极其丢人,又生气又难为情,当着吃粉的客人都哭过两回,“我还要啷个对他嘛!”(“啷个”是“怎么”的意思),面对客人,她已经学会用普通话,伤心时,方言自动打开,“我想不通啊,什么都依他的,他啷个这样对我嘛”。哭过几回后开始质疑,良洪是不是想离婚。良洪一声不吭,连摇头点头都没有,照样去二戈寨买鹅,照样收碗洗碗,像个音频线路熔断的机器人。请卢老师来调解,良洪除了微笑和点头,什么话也不说。罗姨妈多了个心眼,将钱箱看紧,对现金、银行卡和电子支付进行系统化管理,只给良洪必要的零花钱。有一天下午回到家,看见桌子上一张字条:我走了。
行楷,比他平时认真写时写得好。他无钱可带,只带走两套衣服和坐骑,买鹅用的电动摩托。
罗姨妈硬撑着营业,为了避免眼泪滚到汤里面,躲进她的避难所——暗藏在厨房后面只有0.8平方米的卫生间哭够了再出来。但她哪里管得住眼泪,什么时候滚出眼眶都不知道。有客人看见她脸上挂着眼泪,装作没看见,心里嘀咕下次要不要再来。邻里劝她,再这样下去,粉馆会垮掉。一个月后,良洪回来了。是否到达武当山,路上经历过什么,为什么回来,和去之前一样,一概不讲。罗姨妈也不问,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良洪与去之前的区别是,当他想要说点什么,很快打消念头决定不说时,支离破碎的表情多少有点沧桑,以及会在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上表现出敢于顶撞的英勇。他和那些发誓对某事或某人不多言不多语的人不同,后者最长能忍住多久不说值得怀疑,他是真不想说,没必要说,他已经在心头对自己说过了。
另外一件不能说的大事并不复杂,听说建新小区要拆迁,两人装出不爱钱的样子,暗地里却非常兴奋,赔偿款是买房款的五倍。住在二戈寨,平时进城搞装修的朋友找他们借钱给儿子娶亲,他俩毫不犹豫就把钱借给了他。几年后,房子没拆迁,借钱的人不知去向。他们没有埋怨朋友,他们在出版社仓库安家时,所有家具都是他陪良洪从翻新装修人家捡回来,经他修理后送给他们的,有几件搬到曹状元街后还在用。
日子继续,焦虑有一点,忧伤也有一点,日子这么慈祥,却又那么残酷。这些是隐性的,显性的是从开粉馆到现在,良洪胖了15斤,罗姨妈胖了20斤。罗姨妈行动不如年轻时,但身体形成的记忆可以让她不必着急,鹅肉粉的味道和二十年前一样地道。鹅肉粉最重要的是辣椒。将长线青椒沮三下,捞出后炒干,可多少带点煳味,再和大蒜、盐,少许花椒放擂钵里舂成泥。青椒泥在鹅肉汤里释放出清甜的香味,微辣,可以单吃,还可下饭。有人打包回家吃,价钱已从最初的五角钱一袋涨到两块钱一袋。一袋放进饭碗里有半碗。良洪的书法也一直在写,参加过多次国展的卢老师说,他早就可以拿去参展了嘛,但他一次也不参加。有时给朋友写一幅也不署原名,盖一枚闲章:曹状元街散人。内容多是“不许凡尘到”,或横或竖。这是曹状元的诗句:黔山精舍好,相对有名僧。道悟无生妙,禅参最上乘。茶煎涧中水,香霭佛前灯。不许凡尘到,云岚护几层。
良洪练拳二十年才被罗姨妈发现。有一天,罗姨妈感觉不舒服,提前闭店回家。罗姨妈叫他给她捶下腰,她感觉腰快断了。良洪一套拳还没练完,不想半途而废,没说话,继续出拳踢腿。罗姨妈问他这是什么广播体操。他仍不说话。罗姨妈鄙夷不屑地摇头:“噫,鸡死打乱拳,硬是不得了。”鸡被杀后腿要乱踢一阵才死,罗姨妈以此指责良洪不理她,只顾打拳。良洪收拳后去给罗姨妈买药,罗姨妈说揉一下就好了,不用吃药。良洪穿上衣服,睖了她一眼:“鸡死打乱拳不能治病。”走到门外,摇头笑了笑。传了六百多年的鲍家拳被她说成鸡死打乱拳,也太有才了。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派出一支部队,直插尚属元朝势力范围的云南曲靖宣慰司普定路安顺州。不是叫他们去打仗,而是叫他们屯垦,设置卫所。这是洪武皇帝投放在西南边陲的棋子。不过,对于云南王把匝刺瓦尔密,这是比棋子可怕得多的钉子,刺得很痛却又无力拔出。十余年后三十万明军高歌猛进,只用了百余天就将盘踞云南的元朝势力摧毁,和卫所长期以来在灰色地带进行武力威慑,并且刺探情报有关。率领这支部队的人叫鲍福宝。屯垦并非易事,既要提防元军袭击,也要小心地方势力抢夺地盘,村寨里男女老少都得练拳。战争结束后练拳已成一种习惯,鲍家拳一直传到现在。
一辆工程车在施工,良洪以为是临时修补,买好药就回家。第二天早上出门,发现整条街都被铁皮围挡封住,他只能绕道都司桥,再转到下护国路。罗姨妈对此很有意见。绕道让她多走十分钟。一事不顺,事事不顺。罗姨妈心血来潮,要良洪带她去出版社仓库看看,她在梦里梦见核桃树,树下有个小水坑,水坑里全是鱼,她捉了好几条。
罗姨妈相信梦里抓鱼会有好运,但不能说破,说破不灵。仓库背后有一股泉水,泉水下面有半个排球场大小的消防池,可以养鱼,但从没养过鱼。良洪曾把它当游泳池,在月光下裸泳。发现过两次死蛇后,他再也没游过。
电动摩托驮着两个偏胖的人,像一匹瘦马驮着两头大象。良洪不担心摩托散架,他担心被警察拦下。骑到二戈寨原出版社仓库附近,两头大象变成两个小矮人。在建中的房子十几栋,仰头几次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层。良洪知道仓库已经拆掉,也知道这是一个新楼盘,只是没走进去看过,路过和走到大楼跟前感觉大不相同。核桃树下确实有一个坑,比罗姨妈梦里那个坑大。核桃树已被连根拔起,树干截成两米等长。消防池不知去向,泉水不知去向,泉水一带山脚土石已被挖走,山坡变成笔直的石砌堡坎。曾经非常熟悉的东西全都不在,没有一点痕迹。
回到曹状元街,罗姨妈心情不好,失去老家甚至老巢的感觉让她心碎。良洪安慰她:“又不是你家的。”罗姨妈说:“我栽的花,那么好看的花。”良洪说:“挖机又没长眼睛,看不见你种的花。”那是两丛七里黄,橙黄色花朵,鲜艳亮丽,成团簇拥,老远就能看见。
从这天起罗姨妈动不动就发脾气,卢老师叫良洪带她去医院,看看是不是更年期综合征。良洪觉得不是,带她回老家。以前春节才回,并且来去匆匆。这次决定多住几天。请卢老师一起去。卢老师老家也是农村,对去乡下颇有兴趣。
老家的变化也大,村道变宽变硬了,庄稼地变窄变荒了,房子多了,冒烟的极少。树林比过去茂盛,小河里水量比过去小。他们的房子还在,良洪父亲当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做的木瓦房。每次说起建房的辛苦,说不到两句就摇头,太难了太难了说不下去。父亲现在的房子是一堆土,良洪和卢老师去父亲坟上烧纸,罗姨妈在家做饭。为了款待卢老师,良洪特地到镇上买一只旱鸭和两斤荞灰豆腐果。旱鸭把骨头剔掉再炒,在当地是一大特色。做饭很是不顺,如果不是卢老师在,罗姨妈有可能砸锅摔碗。作料和工具提前精心准备,真到用时却发现有的东西多余,有些东西却没有。最让人生气的是柴灶,柴架好,干草塞下面,点燃纸巾,将干草点燃。罗姨妈听见吱的一声,浑身鸡皮疙瘩顿起,一只老鼠几乎是从里面飞出来,肯定受伤了,落到地上还在吱吱哀叫。罗姨妈在二戈寨时不怕蛇不怕耗子,今天却吓得半死。可怜的老鼠一瘸一拐从地脚檐钻出去了,罗姨妈才想起应该给它一火钳。剔骨鸭做好了,罗姨妈觉得内疚甚至耻辱,这是她做得最难吃的一个菜。卢老师是个随和的人,说好吃,至少食材好,原汁原味。良洪也说可以的,可以将就吃。回到老家,他的话明显比平时多。他告诉卢老师,他高中时就辍学去过武当山,走到重庆没钱了,想逃票继续向前,被乘警揪了出来。在火车站广场睡了两天,垃圾堆也没吃的,就要饿死,一架板车运来几千个空饮料瓶,他以其中一个做容器,将其他空瓶里一滴两滴收集起来。收得满满一瓶,一斤半。“那种高兴,那种财富感,一辈子再也没有过。”他决定步行去武当山,走到郊区,饮料喝光了。再次饿饭,幸得一位做布匹生意的老板娘收留,在布店干了半年,因为他字写得好,老板娘说,你回去好好读书吧,给了他路费和学费。读了两年,没考上大学,一边打工一边想当作家。作家没当成,成了出版社仓库临时工。卢老师笑着说:“我真佩服你。”
两个男人聊得开心,罗姨妈则努力忍住不要发火。被子和床单是洗干净放好的,中间还请人晒过两次再用塑料纸包裹,但打开后,总觉得不那么好闻,床上的灰有铜钱厚,蚊帐简直不好意思说那是蚊帐。熟悉的东西太少了,总觉得哪里都不是自己的家,一个人哭了好一阵。原计划住三天,可现在住一天都难,去镇上住又得花钱,何况小镇宾馆只比在家住略好一点。天亮后宣布回贵阳,良洪有点生气,卢老师说怎么都行,没关系。
曹状元街仍然被铁皮围挡封得严严实实。良洪说他不想再洗碗了,请个小工,他决定听卢老师建议,搞个书法培训班。罗姨妈答应请小工,同时提出卖掉曹状元街的房子,去出版社仓库那个楼盘买房。良洪说他哪里也不去,烂也要烂在曹状元街。两人为此争吵,把已经忘记的“寒心事”抖出来复习了一遍,“离婚”两字在心里翻滚,就要像子弹一样射出来。这两个字是两颗子弹,一颗射向对方,一颗留给自己。罗姨妈把金属子弹换成橡皮子弹:“你就是现在去武当山我都不会拦你。”这是有毒的橡皮子弹。良洪失去理智地回击:“你这个蠢鹅、老鹅、臭鹅,你只配和鹅在一起。”
良洪将培训班布置好后,第一件事不是招生,而是搬了套薄薄的被子住在里面。饭做好,罗姨妈像过去一样打电话:“吃饭了。”挂掉电话后补上一句:“管你吃不吃。”良洪在电话里什么也不说,按时回来吃饭,吃饭时不说话,吃完后回培训班。培训班在万东桥下书画市场。站在桥上,有时能看见落日。良洪看着落日,落日完全落下去时,自己也往桥下走。这让他感觉,自己和落日步调一致。人在闹市,心在天际。
万东桥是机场方向进出的公路桥,东西向八车道,桥面很宽,桥下自然形成花鸟市场、书画市场、停车场,与之相邻的两个大单位是省人民医院和社科院,省医在北面,社科院在南面。置身桥下看不到这两个单位,只能看见两个单位围墙外面的小餐馆、杂货店、理发店,有上百家之多。
住在桥下,嚯嚯声连续不断,白天不太引人注意,晚上非常清晰。这是桥上车轮摩擦桥面的声音,像风送雨声,有时大雨有时小雨,良洪一开始就把它当成风声雨声,在风雨声中却不被雨淋,这让他感到惬意。能把噪声当风雨声,和罗姨妈雷霆火闪的对比不无关系。这是一种撩拨,隐藏着无法抹灭的痛苦和忧伤。
来鹅肉粉馆应聘的姑娘很瘦,个子也不高,像小猴子一样东张西望。罗姨妈告诉她工资标准和干哪些活、应该怎么干活,她连连点头,嗯嗯答应。罗姨妈觉得她没听懂,甚至不想听,心思不在,不知道耽于什么。罗姨妈向隔壁烟酒店秃顶大叔抱怨,秃顶大叔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这是废话,但罗姨妈很受用,至少比良洪说话好听。良洪往往一针见血,没有过渡,一开口就指出事物或事情本质,语气和用词总是那么刺耳,罗姨妈虽然早已习惯,却并不舒服。
就这样过下去,两人似乎没什么意见。培训班不好招生,这缘于良洪口拙,不擅长推销自己。他的学生多来自卢老师介绍。桥下房租不高,但培训班的收入也只够房租。罗姨妈说,要不是卢老师,他得吊起锅儿当钟打。意思是凭他自己,一个学生也招不到。良洪对罗姨妈的话一向不爱听,唯有这句,每次他听了笑眯眯的,从不反驳。
罗姨妈想辞退瘦小女工另外找人,这事她不用和谁商量,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可她却一直犹豫,下不了决心。姑娘有空就刷手机,不刷手机就打瞌睡,这让罗姨妈特别反感。姑娘初中毕业辍学,她在城市出生,户口在老家。初中毕业后考上私立高中,父母不愿意出钱,叫她回老家上公立中学,她没在老家参加中考,老家的中学不愿录取。这是罗姨妈下不了决心的原因:她太可怜了。罗姨妈用可怜当她名字,不当面叫。想到她时,“可怜”一词总是随之出现。
同情和不快像跷跷板,跷跷板两头坐着同一个罗姨妈,她享受不到坐跷跷板的快乐,只有被高高翘起的眩晕和重重落下时的轻微脑震荡。这和QzRXQ5bqp/K9CDvhfl+eww==她感受到的人生一样,有一头翘起来,就会有一头掉下去。
良洪没这么多心事,因为心虚而矜持,境况并非现在的一切,而是长期以来就有的一切。
住到桥下后,他不再练拳,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和练字,他不能让跟他学书法的学生失望。手抄了一本《鲍家拳拳谱》,蝇头小楷。示意图用写铁线篆的笔法,纤细刚劲。不给任何人看,很得意地藏在抽屉里,下意识地用指头敲击桌面时,有种富人似的笃定和满足。
“可怜”连续迟到两次,罗姨妈觉得不能再可怜她,必须辞退。正要找她谈这件事,粉馆冲进三个年轻人,拽住“可怜”往外拖,他们很生气。
“看你往哪里跑。”
“你以为找不到你。”
桌子板凳被掀翻,酱油和醋在地上流淌,像血。罗姨妈提着菜刀,凛然道:“你们这是做啥子,要打架不要在我店里打。”
“可怜”用求救的眼光望着罗姨妈。
“放开她。”
菜刀在她手里上下动了几下,像在切菜。其实是害怕,强迫自己不要抖。
三个年轻人悻悻松手,离开时告诫“可怜”:“我们还会来找你,你等着。”
“可怜”哭得很伤心。罗姨妈没管她,将桌子板凳放好,把地拖干净。
“啥子事嘛?”罗姨妈问。
“可怜”又哭,连哭边干活。
收拾好后,姑娘可怜巴巴地问罗姨妈,她能不能住在店里面。罗姨妈说,这里怎么住呀,什么也没有。姑娘说她可以睡板凳。罗姨妈带着优越的神情叹了口气,叫姑娘去她家。在路上知道原委。姑娘的父亲是货车司机,是农资公司签约司机。有一次农资公司老板的儿子押货,非要叫姑娘的父亲让他来开车,没开多远把人撞了,他没驾照,姑娘的父亲负全责。父亲把车卖掉也不够赔,向甘蔗农场借了三十万块钱,把姑娘押在那里打工还债。姑娘不愿意,干半年后跑了出来。
罗姨妈叫良洪回家:“有事情,回来再告诉你。”
良洪没有问回来干什么,罗姨妈怕他不回来,故意不把话说明白。良洪没按时回来,罗姨妈打电话问原因,他说是和朋友在吃饭。
一位收藏家约书画界五个人吃饭,收藏家说要让他们吃一道他们没吃过的菜。良洪对此并不期待,从小艰难,吃什么不重要,有吃就行。神奇的菜端上来,看上去像肉做的菊花。收藏家兴致勃勃地叫大家尝尝。良洪也尝了一块,很脆,糟辣椒爆炒,有股酸味。卢老师笑着说他吃过。收藏家急忙揭秘,说这叫儿肠。特别之处是无论怎么炒都很脆。有人问儿肠是什么肠,收藏家说,儿肠要母猪才有,与生崽有关的肠子,学名叫输卵管,没生过崽的小母猪的儿肠更好吃,不但脆,还细嫩。良洪觉得反胃,咽下去的儿肠在肚子里弹跳。一位画家问切成菊花怎么做到的。收藏家以手掌做刀:把肠子平铺,这样切过去,不切断,半厘米一刀,三厘米再切断,爆炸时收缩就成了菊花。大家都赞叹收藏家懂行,良洪从此看到真菊花都会有不适感。其他人谈书画,谈酒,谈美食;良洪既不说话也不吃菜,只喝酒。散场后回到培训班,蹲在卫生间吐了。酒确实有点多,但头脑非常清醒。他想到母亲,想到母亲的艰辛,想到女性,想到女性的隐忍,想到那截所有生命都要经历的肠子,想到母猪生育后代还要被津津有味地吃,他哭了。酒助思虑,哭得特别伤心,他告诫自己,今后要对罗姨妈好点。罗姨妈催了几次:“到底回不回?”良洪不像以往,很耐烦地回答说:“快了,马上回来。”
罗姨妈急是有原因的。白天找过“可怜”的人在楼下喊叫,叫姑娘“滚”下去,否则他们会让她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他们不但知道她在鹅肉粉馆上班,还知道她已到罗姨妈家。罗姨妈悄悄看了看,楼下七八个人,她越想越害怕。
洗了把脸,良洪觉得特别清醒。他要把手抄本《鲍家拳拳谱》带回去给罗姨妈看,并且从此放在家里面。不是怕放在万东桥下被盗,而是觉得,这里毕竟不是家。
走进建新小区,看见罗姨妈说的年轻人正坐在地上喝啤酒,不时朝楼上吼一声。良洪腋下夹着拳谱,以不大的声音说:“你们在这里吼啥子,要喝酒到街上去喝,不要吵得大家睡不着觉。”年轻人没反应,他提高嗓门说:“我说的是你们,敢到我楼下来吼,讨揍吗?”
几个年轻人从地上爬起来,其中一个靠过来,笑着说:“我们就是来打架的。”说着一拳打过来,良洪没躲,用手腕将来拳格开,同时一个转身贴上去,手肘一顶,正好顶在对手肋骨上。其他人没看见他手肘动作,只看见他摆了一下手,同伴哎的一声弯腰,连连后退,张嘴说不出话来。
良洪不动,两个年轻人左右攻来,一个出拳,一个出腿,都没练过,良洪仍然只凭一只手就把他们弹开。“我打……”一个啤酒瓶劈面打来,这是一个胖子。“我打”还没说完,良洪已转到他身后,反手一拨,胖子踉跄冲出去十几步,啤酒瓶敲在自己膝盖上。
没人敢再挑战。良洪正色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曹状元街。”
他把拳谱递给一个小个子:“给我拿好。”然后摆开架势,打了一通鲍家拳。打完后拿过拳谱,刷卡,开防盗门,就像什么也没发生。
进屋后,罗姨妈抱怨他这么久才回来。良洪笑了笑:“给我煮碗面。”
“你不是去吃饭了吗?”
“没吃饱。”
“专门去吃饭,没吃饱,吃的啥子哟?”
“没你做得好吃,不想吃。”
“看到那帮半截大爷没,讨嫌得很。”
“他们走了。”
“走了?”
“走了,再也不会来了。’
罗姨妈半信半疑,开窗查看确实不在。
“会不会藏在哪个旮旯头?”
“不会。”
罗姨妈去厨房煮面,水还没开,回到客厅对良洪说:“要不,去南横街吃湖南面吧,他们家整个晚上不关门。”
“也行。你和我一起去。”
“我又不吃。”
“你要看看那几个半截大爷不在才放心嘛。”
走到街上,罗姨妈东张西望,没发现异常。反倒是良洪发现异常,刚才回来时没注意。
“那些板板呢?”没有铁皮挡板,街道一下宽了许多。
“拆了好几天了。”
良洪伫立街头,发现铺面全都装修过,对面贵信宾馆旁边小区已改叫“曹状元街小区”。好多店铺都增加了状元元素。经营了三十多年的富南小吃改叫“状元楼”,良洪扫一眼就知道那是著名书法家戴老的字。他一直想要戴老一幅字,不好开口。站着看了半天。除了“状元楼”三个字,良洪觉得变化也太大了,像罗姨妈新做了发型,虽好看,却还有几分不适应。
“整得好,比以前漂亮多了。”罗姨妈说。
“我不想吃湖南面。”良洪说。
“吃啥子?”
“大饼和稀饭。”
“哪里有啊?”
良洪抬下巴指给罗姨妈看,就在对面:津东肉饼王。有树叶遮挡,隐隐约约。饼端上来,罗姨妈掰了一小块,说:“有点干,我去倒杯水。”良洪看着罗姨妈鼓起的肚子,虽然越来越胖,但那里面也有儿肠啊,鼻子一酸。想到在上海读康复专业的女儿,暗想:谁敢动我女儿,我对他绝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