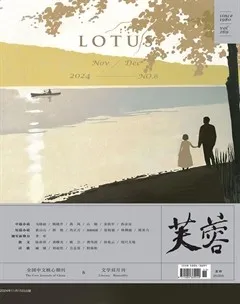时代标签与标签下的心灵图景
郭艳(笔名简艾),安徽舒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文学评论家,作家,中国文联第十届全委会委员,现任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研究员。
《绿挎包》讲述了一个无爱婚姻的故事,叙述者是“我”,叙述对象是“我”的公公婆婆。“我”的婆婆去世后,公公向“我”倾诉了面对家庭责任、个体情感的挣扎与痛苦。小说在“我”帮助公公对于往昔恋人的寻找过程中,凸显出了中国式婚姻的无奈和感伤,同时表达了对于人性的深度考察和内省。
这个故事看似寻常,无爱的夫妻,不亲密的家人,不和谐的家庭……一如叙述者所言,这不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然而却可能是很多家庭的缩影。人被深度植入婚姻和家庭之中,又在其中经历着孤独与冷漠,甚至于忍受着痛苦与伤害。文本的第一个维度写普通人的悲喜人生。作者擅长在对日常生活静水深流的叙写中,表现当下社会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文本叙述者的身份是媳妇,同时又是一个写作者,双重身份带来双重视角,尤其以家人的身份观察婚姻与家庭,如显微镜般成像,细节场景和情绪的把握十分到位。公公婆婆各自以自己的执念对待婚姻与家庭,丝毫没有考虑到子女的感受。这类婚姻中受到伤害最深的是孩子,然而文本中的儿子是孝顺的,媳妇是隐忍的。随着故事内核一层层打开,无法和解的两性关系成为解读人性的注脚,婆婆在无爱婚姻中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性格中的暴虐似乎有了某种合理的解释。对于父亲来说,养家糊口的责任远大于对卞姑娘的遗弃,无爱夫妻养儿育女的生存是现实的存在。对于中国式家庭和婚姻来说,形式上的完整似乎抹平了内瓤里的破碎与败坏。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的忍耐和将就,又成为维系形式完整的途径和方式。对于叙述者“我”来说,一方面质疑公婆对待子女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和丈夫一起用孝顺和忍耐维持着家庭表面的和谐。所以很多人维系婚姻形式完整的责任感远远高于对于婚姻质量的追求,貌似完整的人生实则更多隐忍苟且的日常。
文本的第二个维度则在命运悲剧中层层展开,叙述者温情中带着质疑,同情中带着无声的叹息,显示出作者敏锐却体贴的写作姿态。众生皆苦,有时人会盲目而愚钝。公公背弃爱情,选择现实地活着,原本也是自私的人性使然。然而公公却依然保有某种对于先前恋人的长情,以至于无法给予妻子真正的爱。公公由一个烟火气很重的俗人变成了一个眼盲心瞎的可怜人。卞姑娘因情而死,婆婆爱而不可得,变得乖戾暴虐。这些原本无甚特色的匹夫匹妇转而具有了悲剧性,他们的生活则和叵测的命运相联系,他们的人生成为具有悲悯和恐惧特性的悲剧。美好的青春、热烈的爱情、美满的婚姻乃至人性和伦理层面的完满与和谐等,这些都在岁月的流逝中被摧残。文本在这个层面揭示了普通人情感和婚姻可能具有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往往和人的认知、个性、行动能力等密切相关。公公抛弃卞姑娘、背叛爱情、无爱婚姻等,这些表层是伦理情感问题,实质上公公婆婆的婚姻悲剧更多是公公的懦弱性格和毫无行动能力造成的。而反观婆婆和卞姑娘则都为了自己的爱采取了勇敢的行动,卞姑娘选择不嫁他人,婆婆则努力养大孩子们,甚至于找到卞姑娘的下落。两个有行动能力的女性又都囿于认知的局限,一个为薄情寡义的恋人空付爱情,一个为冷漠自私的丈夫坚守婚姻。然而,这两位女性无回报的付出又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中国传统伦理情感价值判断。小说中并不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依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由此命运悲剧与个体认知、性格特质乃至情感伦理构成了复杂的交集,短篇文本由此获得极为丰富的歧义性,人物也在时光的沉淀中散发出独特的韵味。
与此同时,这个文本呈现了时代的标签与标签之下的心灵图景,这也是小说更为深刻的第三个维度。当下社会流行各种各样的标签,对于不同标签的选择标识着不同的认知和审美,代表着不同的阶层与人群。同时因为当下价值多元,人们对于标签的选择更为碎片化。绿挎包是公公婆婆时代的经典标签,这一标签更为传统和保守,因此它所暗含的认知和判断更为单一和固化,由此也造成了更为持久的张力,以及人与人之间更为直接而强烈的冲突与矛盾。对于那个时代的很多人而言,某种荒谬的认知或价值判断,就可以造成夫妻、亲子、朋友和恋人之间的决裂和背叛。小说写的是凡人琐事,从人性自私和盲目的层面揭示了“我执”对于爱情、婚姻和家庭的侵蚀,表达了对于单一时代标签中人性复杂性的探讨,从而呈现出了时代标签之下一代人更为真实的心灵图景。
总而言之,作者以娴熟的笔触重写朴素年代貌似简单粗暴的感情和婚姻,实则摹写其中生活的个体人的复杂性。小说呈现个体人在世俗生活龃龉中的进与退,爱情与背叛,软弱与固执,苟且与偏执,长情与无情。所谓的爱,往往是陷入我执的某种痴迷状态,没有抵达爱的纯粹,而是以爱的名义纵容人性的自私与愚蠢。在事实和真相面前,孝顺的儿子媳妇最终还是选择了隐瞒真相,维护大家庭形式上的完满。微信头像从绿挎包换成全家福的那一刻,公公也完成了对于自我的虚假救赎,他没有付出任何行动的内疚也终于因为谎言而彻底放下。小说的结尾是多义性的,在温和的叙述中,公公这一代人依然靠着自欺欺人获得伦理和道德上的某种满足,这种满足是真实的,同时又是虚妄的。一代人似乎错乱的人生,在某种严整有序的伦理道德中进行到底。叙述者是悲悯且善解人意的,带着和解的眼光面对娑婆世间;同时作者又是锐利且深刻的,带着清醒理智,冷眼旁观人性的复杂与幽暗。作者以平静的叙事腔调重新叙写过去时代的爱情与婚姻,以回溯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家庭、婚姻以及伦理的剖析与内省,完成了对于当代生活经验多层面多维度的解读和书写。在极短的篇幅中,小说将人放置在显微镜下细致观察,又推入时光的长聚焦中纵深考量,对于一个时代伦理道德标签以及标签下的心灵图景做了精彩的摹写和呈现。这个文本对于当下短篇小说创作的深度和广度都极具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