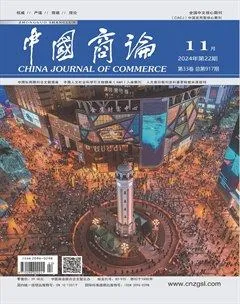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空间效应研究
摘 要:本文运用甘肃省县域2012—2022年的面板数据,采用ESDA(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增长理论的内容,对甘肃省县域经济的差异和增长情况进行了空间分析。结果表明,甘肃省县域经济存在空间关联性,既会受到本县域的影响,也会受到周围县域的影响,并且经济发展情况存在稳定的两极化发展趋势,经济整体水平受第一和第二产业影响较大,与工业化水平、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等因素呈正相关。据此,本文建议: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施积极的、可持续提质增效的财政政策;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人力资本结构。
关键词:甘肃省;ESDA;空间计量;县域经济;人均GDP;城镇化水平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4)11(b)--05
就经济运行实际情况和生产要素的流动而言,地理空间是其重要载体,明确经济活动的个体之间空间上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对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区域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机会和人口流动都有重要意义。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最基础单元,县域经济扮演着基础性、支撑性的角色,其健康发展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甘肃省位于中国西北内陆地区,是“一带一路”重要枢纽,近年来在技术、文化、生态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甘肃省对比全国相对来说贫困程度深、贫困范围大,研究甘肃省县域经济空间关联性的重要性对于推动全省协同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地方经济的韧性和可持续性,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1.1 县域经济发展
19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在《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之关系》一书就提出了农业区位论的概念[1]。20世纪20年代后,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一些学者开始探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详细说明运输成本、市场、资源可用性等因素如何决定企业工业设施位置[2]。Berechman使用由1990—2000年的州级、县级和市级数据证明交通投资会产生强大的溢出效应[3]。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县域”一次出现高达13次。宋林飞(2019)重点关注了苏南地区模式创新的可行性[4]。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测度方面,往往多集中于省际、中国东、中、西部或者西北、西南等几大区域之间,任保显(2020)发现东部的发展质量高于中部和西部省份[5]。付瑞等(2023)对新疆79个县建立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体系[6]。县域经济发展同样存在问题和困难。吴友仁(1985)[7]就提出对县域经济的发展需要提前以及合理的规划。随着实证分析方法的进步,缪小林等(2014)[8]发现云南省地方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呈现出倒“U”型关系。近期,学者们更加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与县域经济的结合,吴茂祯等(2022)[9]基于区域协调发展与碳减排的双重背景进行研究。
1.2 空间计量
由于地理空间的特殊性,需要加入空间效应的分析,国外对于这一部分在理论和实证上起步更早。Moran首次提出了空间自相关测度,Paelinck在会议上首次提出“空间计量经济学”这一名词。Tabuchi等(1986)[10]发现在资本增加模型和均衡模型中人口密度都会产生空间上的集聚效应。Debarsy(2012)[11]通过房价预测捕捉到了回归因素和个体效应之间空间的相关性。
国内初期学者使用基尼系数等指数分析和量化地理空间内的经济不平等问题。赖增牧(1986)[12]在集聚经济的研究中发现经济会向着城市集聚和积累。另一类方法主要以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为主,张英浩等(2022)[13]研究了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溢出效应。在不同尺度的研究上主要分为国家层面、省级层面、县级层面等。潘文卿(2006)[14]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曾建中等(2023)[15]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15]。
1.3 文献评述
本文主要从县域经济和空间计量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文献的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本文从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测度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和困难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在空间计量学方面,国外相对来说起步较早,国内大多是依托和吸取国外研究理论的精华来进行实证分析,由于中国区域差异以及发展情况的多样性,从基于不同测算方法的研究和基于不同尺度的研究进行梳理。
国内对于经济和空间效应相结合的研究主要基于省级层面,或者长三角、珠三角、长江流域等经济发达地区,而省内层面的研究也停留在较有代表性的如山东半岛地区,对于相对来说发展较慢地区县域经济研究较少。本文从甘肃省县域经济层面出发,希望通过ESDA等方法探究经济的集聚和溢出效应,并研究其影响因素,旨在促进甘肃省经济发展。
2 理论基础
2.1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领域的一个分支,由保罗·克鲁格曼等人创立,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兴起,主要关注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中的分布、演变和影响。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了地理空间上经济活动的不均衡性,这引导研究者关注地理空间对经济的影响。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了产业在地理空间中的集聚和分散现象。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地方政府和规划者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总体而言,新经济地理学试图通过对地理空间中经济活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对经济发展和地方发展的新理解,丰富了传统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2.2 新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是美国经济学家罗默。他在1986年提出了知识“外部性”的概念,强调技术创新对整个经济系统的积极外部影响。罗默模型将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引入,认为知识是可积累的,并且通过投资于研发和教育,社会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同时,其他经济学家如卡尔·斯文和罗伯特·博尔迪格也探讨教育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了对知识和技术创新的关注。不同的学者在理论中引入了如生产链、制度环境其他元素,以全面解释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
3 甘肃省县域发展现状
3.1 甘肃省发展总体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以来,甘肃的经济迎来了飞速发展,全省在经济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保障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甘肃省全省GDP从2000年的1052.9亿增加至2022年的11201.6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3%。产业结构逐渐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比重从2000年的19.6%,44.8%,35.6%变为2022年的13.5%,35.2%,51.3%。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2000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916元和1292元,而2022年增长为38720元和12118元。
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人才流动等因素,与其他地区相比仍有明显差距。2022年全国人均GDP为85724元,而甘肃省仅为44986元,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52.4%。2022年甘肃省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甘肃省2022年财政收入为907.6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从2000年的1.31%降低到2022年的0.83%。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中,近几年甘肃省综合实力始终处于末位。
3.2 甘肃省各个县域GDP概况
通过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对甘肃省2012年、2016年、2020年、2022年的人均GDP进行分析,甘肃县域经济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县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弱。发展水平位与第一层级的县域较少,2012年仅有1个,2020年最多也仅有10个,大部分都处于第三和第四层级;第二,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集中聚集在陇东和陇南地区。陇东南地区主要收入来源于传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较落后;第三,西北部和东南部县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且有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西北部地区得益于很早就确立了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定位,发展水平高,东南发展水平低;第四空间分异格局较稳定,且兰州和陇东地区有明显进步。近几年,得益于政府“强省会”战略,兰州附近的一些县域经济发展较快,陇东地区交通便利且依托西安的大市场同样得到了充足的发展。
4 甘肃省县域经济空间相关性分析
4.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县域是指甘肃省的县级行政区域,覆盖了整个甘肃省全境,一共有87个行政区,其中包含58个县级行政区、17个市级辖区、7个自治县和5个县级市(因为嘉峪关市下辖没有区县,因此将其作为一个单元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12—2022年《甘肃省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嘉峪关市相关数据来源于《嘉峪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部分2022年的数据来源于各地区政府网站。
4.2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在空间计量模型中,空间权重矩阵是一个关键概念。它用于表示地理空间上观测点之间的关系,通常用于建立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的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需要考虑地理空间的特征,选择合适的权重分配方式,以及确定观测点之间的空间距离度量方法。根据甘肃省县域的分布以及县域经济发展情况,本文使用Queen邻接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
4.3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ESDA的方法来研究空间自相关问题,首先使用Moran’s I来证明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是否在整体上存在自相关以及自相关的程度如何,若存在则可继续向下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使用Lisa集聚图来探究局部莫兰指数,该图可以帮助分析局部区域是否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或分散现象,揭示地理数据中的空间模式,帮助理解自相关在空间上的分布趋势。
4.4 空间自相关分析
4.4.1 全局自相关分析
本文首先对2012—2022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全局自相关检验。从表1可以看出,研究期内Moran’s I 指数均通过了假设检验且都为正值,甘肃省县域经济始终存在空间自相关,适合下一步进行空间计量的分析。具体来看,甘肃省全局 Moran’s I 指数从2012年开始呈上升趋势,2016年达到最高值为0.622,从2016年到2022年先下降再上升再下降,但总体变化较小。分析其变化的原因,持续上升期处于甘肃省“十二五”的关键时期,基础设施、交通和物流等建设不断完善,地区合作不断加深。从2016年开始Moran’s I 指数虽然有下降趋势,但此时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各个地区把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本地建设,地区间的生产要素流动缓慢,而且地缘性经济明显,总体上始终呈现一个较高水平。
绘制并观察甘肃省2012年、2016年、2020年和2022年的Lisa集聚图进行局部空间关联分析:第一象限是高-高聚类区域,甘肃省的西北部肃南县、高台县等发展水平高的县域落在这一象限中,并且与之相邻的区域同样是高发展水平。第一象限内县域的个数也在逐年增加,说明这些县域本身的发展状况较好,并且与附近的县域形成了良性的生产要素交流。第二象限的区域也就是低-高聚类区域,这一区域内的点较少,仅仅在2016年和2022年有榆中县、景泰县和敦煌市等,放眼全国第二象限的点形成原因是经济发展情况较好的地区对周围进行了削弱,并主要集中于省会城市或者主要城市附近的县域,由于甘肃省普遍的发展程度较低,因此这种现象不太明显。第三象限是低-低聚类区域,这种区域与第一象限相反,本身的发展程度比较低,附近县域的发展水平也比较低,甘肃省内这种情况主要位于陇中陇南地区。第四象限是高-低聚类区域,自身的发展水平较高,但附近县域的发展水平较低,类似于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体现了对周围县域的虹吸现象。
5 甘肃省县域经济空间效应分析
5.1 模型选择
在进行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时,通常要先进行模型选择。首先进行LM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LM检验结果显示统计量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变量之间存在空间关联性,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是合理的,此外LM、Robust LM检验都是显著的,说明本文适用于SDM模型。其次进行了Wald和LR检验,结果显示所有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了原假设,最后说明SDM不会退化为SAR和SEM,应该使用空间杜宾模型。
本文进行了豪斯曼检验,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应该选择固定效应,继续进行似然比检验,且均通过了检验,说明本文应该选择个体与时间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
5.2 空间效应分析
首先以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固定资产投资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城镇化水平、普通小学中学在校生、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工业化水平为解释变量,以Queen邻接矩阵为基础,使用甘肃省县域2012—2022年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4列(1)和列(2)所示。
首先,空间误差系数和空间自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检验,说明县域人均GDP增长在邻接矩阵上存在溢出效应。固定资产投资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通过了检验,说明市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强烈的正向关系,经济的发展需要依赖居民的储蓄存款。其次,工业化水平也通过了检验,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工业化有利于产业的集聚,与城市化的协同对经济增长具有有效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也通过了检验,城镇作为吸引人才、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中心同样能缩小贫富差距。
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对经济作用显著为负,财政收入的弹性系数较小,而支出的弹性系数较大,这拒绝了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的假设,与传统的新增长理论相悖,主要原因在于县域单位的财政体系可能存在问题,财政支出的效率较低,反而会抑制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并没有表现出空间上的相关性,主要原因在于甘肃省县域地理上跨度大。普通小学中学在校生没有通过检验,主要原因在于甘肃省发展水平较低,部分地区没有成熟的教育体系。
为了探究甘肃省县域经济的影响因素以及空间关联,进一步对空间效应进行分解,可以分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其中,直接效应指区域内影响因素的作用,间接效应指周边区域对本区域的经济影响程度,总效应是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
结果如表4列(3)-列(9)所示,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都通过了检验,直接效应系数为正,即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本县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间接效应同样为正数,说明不仅仅是本县域的投资对本县域起到了影响,临近县域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也会对本县域的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作用。
工业化水平、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农村人口占比通过了检验,且直接效应显著但间接效应不显著,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工业化水平往往带来更大的市场、生产效率的提升,但甘肃省的特殊在于可用土地较少,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买房、买车等可能会增加了支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通过了检验,间接效应同样显著,且系数大于直接效应,说明区域之间的经济往来比较频繁。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直接效应为正,通过了检验,间接效应为负通过检验,加总之后总效应为正。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两个变量不显著,联系甘肃省实际情况,相对来说这两者在经济发达地区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普通小学中学在校生通过了检验,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为负。
6 结论、政策与建议
6.1 结论
县域经济是国家宏观经济体系的基础。作为地方经济的基层单元,县域经济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随着西部大开发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甘肃省目前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不断增强,空间分异格局较稳定,兰州和陇东地区有明显进步,但县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弱,而且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集中聚集在陇中和陇南地区,同时西北部和东南部县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且有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为了进一步探究哪些因素影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本文使用甘肃省县域2012—2022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普通小学中学在校生、城镇化水平等10个变量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从结果可以看出区域内固定资产投资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城镇化水平、工业化水平等对本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临近县域对本区域还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等对经济发展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型、内部运行模式存在问题。
6.2 政策与建议
6.2.1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发展县域经济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是一种灵活的发展战略,要根据甘肃省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适宜的措施。酒泉等地区坚持工业主导发展,做大做强实体工业,同时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新能源产业;对于土地资源丰富的陇南地区,发展特色农业,种植经济类作物;兰州、金昌等高素质人才较为集中的地区,依托政府的政策,坚持新材料、大数据产业,打造创新创业高地。
6.2.2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甘肃省每个区域甚至每个县域都要制定明确的区域发展战略和规划,确保各个地区在整体发展战略中有明确的定位和任务。同时,通过财政、税收等合理的资源配置和投资引导,鼓励各地区发挥自身优势,推动各类资源的合理流动。各级政府要加强政策的协同,避免因政策差异导致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6.2.3 实施积极的、可持续提质增效的财政政策
合理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实现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避免采取过度激进或短视的政策,以免导致财政不稳定或债务水平过高。采取灵活的财政政策,根据经济变化和外部环境作出及时调整。及时考虑不确定性和风险,应对各种可能影响财政状况的因素。
6.2.4 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人力资本结构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作用远大于物资资本,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教育体系、鼓励多元化发展;推动职业教育,发展适应市场需求的课程,推动终生学习体系、提供灵活的就业机会,强调创新能力的培养。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改善人才流动机制,鼓励人才在不同领域和行业间流动。加强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设立科学的人才评价标准,配套激励机制,激发人才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M].商务印书馆,1986.
韦伯.工业区位论[M].商务印书馆, 1997.
Berechman J,Ozmen D,Ozbay K. Empirical Analysis of Transportatio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State,County and Municipality Levels[J].Transportation,2006,33(6):537-551.
宋林飞.苏南区域率先发展实践与理论的探索: 从“苏南模式”“新苏南模式”到“苏南现代化模式”[J].南京社会科学,2019(1):1-10.
任保显.中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实现路径: 基于使用价值的微观视角[J].中国软科学,2020(10):175-183.
付瑞,刘林.共同富裕视角下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研究[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4(6):28-35.
吴友仁.市、县域规划的任务、内容和方法[J].经济地理,1985 (4):260-266.
缪小林,伏润民,王婷.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来自云南106个县域面板数据的证据[J].财经研究,2014,40(9):4-15+37.
吴茂祯,马雯嘉.区域协调发展与碳减排双目标驱动下的政策效果研究: 基于县域数据模糊断点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22(S1):108-120.
Tabuchi,Takatoshi.Urban agglomeration capital augmenting technology, and labor market equilibrium[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86,20(2):211-228.
Debarsy N.The Mundlak Approach in the Spatial Durbin Panel Data Model[J].Spatial Economic Analysis,2012,7(1):109-131.
赖增牧.我国城市聚集经济效益和体制改革[J].江西财经学院学报,1986,25(3):6-11.
张英浩,汪明峰,刘婷婷.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与影响路径[J].地理研究,2022,41(7):1826-1844.
潘文卿.地区间经济影响的反馈与溢出效应[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6(7):86-91.
曾建中,李银珍,刘桂东.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和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县域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国际金融研究,2023(4):3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