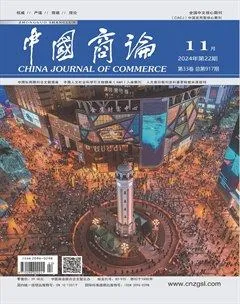数字金融监管的法律逻辑与创新路径
摘 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我国数字金融强国,离不开数字金融监管。如何对创新特性数字金融进行有效监管,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也是对我国金融监管提出的重大挑战。本文基于数字金融监管的本土实践,借鉴域外有益的监管经验,在厘清数字金融监管法律逻辑的基础上,围绕构建全新的数字监管框架,针对我国数字金融监管存在的困境,提出构建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制度、革新传统的监管方式、搭建数字监管平台、完善细化“监管沙盒”制度与消费者保护法规等数字金融监管创新路径,促进数字金融创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关键词:数字金融;法律逻辑;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方式;数字监管平台
中图分类号:F8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4)11(b)--04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认为,世界当前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是在数字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以数字新兴技术与经济的融合,产生了数字经济,这也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又是数据密集型行业。因此,数字科技革命与金融的创新融合,催生出一个生态系化、系统化的数字金融。如今,数字金融已成为全球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毋庸置疑,数字科技对整个金融业具有强大的推动与变革作用,但同时也潜藏着更大的破坏力。今后,如何促进数字金融创新与发展,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稳定,是世界各国监管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1 数字金融监管的法律逻辑
1.1 在法律语境下对数字金融的再界定
目前,世界各国尚未达成统一的数字金融概念。当下,国外以金融科技(Fintech)概念为主导。在国内,数字金融与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等几个概念混用。在理论界,数字金融代表性的定义有三类:一是认为数字金融同于互联网金融,基本上是混同使用。二是认为数字金融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融资、支付、投资和其他新型金融业务模式。相较而言,数字金融更加中性,涵盖的面更广泛[2]。三是数字金融必须以数字资产为核心[3]。就监管层而言,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出台的相关文件及监管部门的监管规则中,在2017年之前主要使用的是“互联网金融”概念;在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 年)》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中,使用的却是“金融科技”的概念。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使用了“数字金融”概念;2023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立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明确了法律概念,进而才能实现法律的首要目的,即将人的行动与行为置于某些规范标准的支配之下[4]。如果概念模糊不清则难以厘定法律的边界,从而更难以明确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金融机构的权利义务。因此,非常有必要从概念入手来分析法律制度。对数字金融的法律界定,应采用“归纳概括+不完全列举”的方式,即围绕数字金融的核心本质,列举其主要业务模式,并给后续发展的业务模式留有空间。具体而言,可将数字金融归纳概括为:持牌的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运用数字技术,在金融数据和数字技术的驱动下实现融资、支付、投资和其他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精准化、智能化与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形态。其业务形态不完全列举为:第三方支付、数字货币、数字信贷、互联网贷款、数字保险、数字证券与互联网保险等新型业态。从而,能使国家立法、监管者执法、司法和守法等层面保持高度一致;在国际监管合作层面,保持相对、主要方面的协同。综上,互联网金融着重于互联网公司从事的金融业务,金融科技更突出技术特性,而数字金融更加中性、范围更加广泛,既包括互联网金融各业态,又涵盖了金融科技的内容。
1.2 数字金融监管的法理
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离不开契约精神和法治保障。数字金融借助于现代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于金融业,极大提高了金融效率,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同时,数字金融也伴随新的风险。数字金融最大的风险挑战是系统性风险,其源于数字金融系统内部的高度互联性和对复杂技术基础设施的依赖性[5]。此外,还会产生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风险、算法风险、“共债风险”[6]。总之,数字金融的风险更为隐蔽、更易扩散和更为复杂[7],这亟须法律监管规则的到位。第四次工业革命需要建立一个抗风险力更强的监管体系和立法体系[1]。金融市场运行的基础规则就是法律,法律制度的健全程度决定着金融的公平性和开放性[8]。建设数字金融强国,则须以法治化的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秩序、促进数字金融的创新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2 数字金融监管的困境
2.1 系统性重要机构识别机制缺失,影响金融系统稳定
金融与生俱来就伴随风险,其核心就是进行风险管理。数字金融也存在着系统性风险问题。数字金融监管的主要职能就是确保数字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防范及化解金融风险。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有关银行、保险行业的系统重要性评估办法与机构名单,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目前,对于数字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重要机构的评估办法与重要机构的名单尚无。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管规则去识别数字金融系统性重要机构,那么这些机构一旦发生风险,就会对整个金融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2.2 传统分业监管不契合,易形成监管套利和空白
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是按照不同行业的机构监管,即“牌照”基础下的“分段式监管”,运用的是刚性的监管思维。但是,数字金融天生就是混业经营,例如蚂蚁金服、京东金融、陆金所等都是混业经营。数字金融的跨业务、跨市场、跨区域等特性,所带来的金融活动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分业监管的范围,显而易见机构监管不契合数字金融的需求。同时,数字金融大量的金融业务活动突破了机构监管的范围,容易造成监管空白。一些金融机构利用数据信息不对称,通过数字技术法规监管,甚至产生行业内、跨行业和跨地域等模式的数字金融监管套利问题[9]。
2.3 数智化监管不到位,监管效能受抑制
目前,发达国家都在积极推进监管数智化转型。尽管数字金融监管主管部门提升了数智化的监管水平并取得了很多成效,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数据驱动的监管理念不到位,数智化的监管平台建设尚未完全到位,监管数据的采集、存储、应用和管理规则与体系还不完善;监管的关键在于人,只有监管者懂技术了,才会知道风险所在。数字监管人才亟待加强培养,必须解决懂数字技术的不熟悉金融监管业务、熟悉金融监管业务的不掌握数字技术的问题;数智化的监管工具有待丰富,例如数字化嵌入式监管工具的开发与运用。
2.4 监管沙盒制度不完善,妨碍数字金融的创新
针对数字金融创新及引发的新型风险问题,数字金融领域推广使用“监管沙盒”制度,其体现的是一种实验型的规制思路。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了央行版监管沙盒的监管试点,它具有阶段性与临时性的特性[10]。尽管我国“监管沙盒制度”成功试行,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例如,监管主体的单一性、试点范围较窄、参与的机构、相关政策不明确性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地方监管沙盒制度的完善等方面还存在着问题[11]。
2.5 保护数字金融消费者的法规不完善,影响市场稳定
在数字科技革命与金融的创新融合发展浪潮中,中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战略,启动了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由国家金融监管局承担全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工作的职责,原来的中国人民银行与证监会的消费者保护工作并入金融监管局。G20根据数字时代的新变化,对数字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又做了新的阐释,即完善法律与监管框架、公平公正地对待消费者、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等方面的内容[12]。目前,我国已经指定了多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证券法》(投资者保护专章)《数据安全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等。但是,数字金融消费者亟待解决身份界定、数字化的金融服务导致的信息披露与公平公正的问题。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构筑良好金融秩序、实现金融为民的基础性工程。
3 数字金融监管的创新路径
数字金融是借助于先进的数字技术进行金融产品、服务甚至金融工具的创新,其本质仍然是金融,仍然要遵循金融的逻辑与规律。“监管和立法生态应具备灵活性和责任感,既要鼓励创新,也要把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繁荣。”[1]这一全新业态的数字金融,应从其金融本质与数字化的技术禀赋上进行监管路径的创新,构建与完善一个能平衡进入创新与稳定的适配的数字金融监管的框架。
3.1 构建数字金融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制度,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从中吸取的教训与经验是破除单一的微观监管,而是在金融监管体系中强化与突出了宏观审慎监管的地位和作用。换言之,世界各国均设立宏观审慎监管机构,并确立中央银行在宏观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重点加强风险隔离和系统性风险防控要求。其中,对系统性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是关键。数字金融随着数字技术与金融的融合创新发展,其中必然会产生对金融稳定具有重大影响的金融机构。例如,世界前列的数字金融公司包括蚂蚁金服、腾讯、字节跳动、京东数科等国内知名公司。一旦这些机构运营产生问题,势必会影响金融稳定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基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念,监管部门应构建数字金融系统重要机构监管制度:一是出台数字金融系统重要性的机构的监管办法,可参酌银行、保险的相关指标,诸如资本金、流动性与业务范围等设置相关的监管指标与要求,建立识别数字金融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制度[13];二是可基于监测分析和压力测试结果,强化事前风险预警,引导机构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三是设置对数字金融系统重要性机构处置制度,即包括加大数字金融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违法成本、制定相应的具有系统相关性服务的恢复计划与有序退出的重组和清算监管制度。总之,通过构建数字金融系统重要机构监管制度,可以有效降低这些机构出现重大风险的概率,并在必要时提供支持与帮助,以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
3.2 秉持“同样业务、同样风险、同样监管”的理念,革新传统的监管方式
监管理念决定了监管者采取什么样的监管方式。数字金融在金融创新与大型金融机构的业务多元化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产品法律属性的界定问题成为机构监管的难题。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最大区别是:在功能监管中,按照金融业务类型,由监管机构分段、各司其职负责。而在机构监管中,即使金融机构涉及多种类型业务,仍然由所属监管机构对其实行并表监管或全面监管。如果采用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必然适得其反。但同时,数字金融的金融本质不会改变。基于此,应该基于“同样业务、同样风险、同样监管”的理念,一是依法将所有的数字金融活动纳入监管之中,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牵头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减少监管空白,消除监管套利空间;二是实施功能监管打破传统机构监管的壁垒。在功能监管下,以数字金融业务的功能来确定对应的监管归属;三是对于数字金融某些业务具有混业跨界、交叉与嵌套的复杂特性,则需要以“实质属性”为原则,判定业务性质与功能,融合功能监管与穿透监管进行全方位的、有效监管;四是强化行为监管与功能监管的协同。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家保险协会在《市场行为检查手册》中正式提出行为监管(Market Conduct Regulation)的概念。何谓行为监管?泰勒认为行为监管(Conduct of Business)是确保金融机构在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时候遵守商业行为规范,最终目的旨在让消费者能在一个公平、透明的环境中交易,防止欺诈。新加坡在数字金融领域采用行为监管是最好的佐证。新加坡的经验是对数字金融活动采取基于行为或风险而不是基于机构的监管方法。只要是发生相应的金融活动,就会按照业务性质被纳入相应的监管框架,而不在于机构采取了何种技术。
3.3 搭建数字监管平台,形成数据驱动型监管
数据驱动型监管是数字金融发展的新型监管要求,也是世界各国大力发展数字金融的监管新保障。数据驱动型监管以数据能力建设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方式。针对数字金融的新模式,搭建数字监管平台,具体包括:一是构建数字化监管平台,实现监管数据一网通。首先,完善监管数据治理规制体系,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数据的采集、加工、存储、应用、流转等管理环节。其次,按照数据分级管理要求,保障数据安全。再次,建立不同监管部门的数据协同互通机制,即通过不同金融监管部门数据互联共享与市场监管、税务、司法等相关部门数据的互联,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数据资源库,形成监管合力。最后,加强金融法治人才的培养,提升监管水平,即通过高素质的监管人才,运用数字技术激活和分析机构报送的数据,对关联交易和复杂产品以及股东身份、入股资金等进行穿透分析,提高防控金融风险能力,实现数智化的穿透监管。二是建立风险处置数字化监管机制,规范风险处置流程与操作程序。三是开发嵌入式监管工具。嵌入式监管实现全链条的监管,要求机构通过 “了解你的客户”和持续的尽职调查,监管数字金融机构监管的合规性,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监管,并能提升嵌入式、穿透式监管的效能。
3.4 完善细化“监管沙盒”制度,促进数字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沙盒”体现了以“试错”为核心鼓励金融创新的试验型规制的理念。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属于制度初建之期,尚需多方面完善。反观,新加坡、我国香港的金融“监管沙盒”建设的实践,不难发现其成功的经验体现了改变监管理念,真正做到鼓励新产品创新的作用。新加坡成功的经验在于:在不可放松的核心要求(比如用户隐私、诚信正直、第三方托管客户的资金和资产、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等项目不可测试等项目不可测试)的前提下,按照真正的促进金融创新的逻辑,明确市场主体和业务范围的准入规则即建立负面清单[14];香港的经验在于,香港的证监会、金管局与保监局建立了各自领域内的“监管沙盒”制度,并在其主管的领域内明确制定了准入门槛、测试流程、退出机制等规则,并相互协同合作[15]。针对我国“监管沙盒”实践的不足,在借鉴新加坡、中国香港经验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完善细化我国数字金融“监管沙盒”制度:一是进一步明确坚持金融创新与“容错”理念,改变是“命令—控制”的监管方式,创建回应型的监管。二是可借鉴我国香港地区以业务准入而非以机构准入为导向,鼓励业务较为成熟的机构入盒创新,完善金融监管局、证监会等机关主导的“监管沙盒”制度,逐步建立新加坡式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允许合规不确定的项目在入盒创新过程中逐步明晰业务和监管的边界[14];三是可探索建立地方“监管沙盒”制度,即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牵头地方各金融业务主管部门,在中央政策和行业标准的制约下,制定“监管沙盒”的具体细则和运行机制,设置科学合理的测试评价模型,对“监管沙盒”的项目测试进行日常管理,延伸“监管沙盒”的监管深度和广度[11]。
3.5 完善数字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规,构筑良好的金融秩序
金融消费者是金融市场的基石与关键性因素。在我国实行新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新体制下,应遵循我国基本法律的规定,借鉴G20等国际组织适应数字化时代要求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原则,再结合数字化时代金融的产品与服务方式等,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数字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规。具体而言,一是可统筹制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明确金融消费者内涵与外延、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义务、金融机构的权利义务、监管部门的职能职责与纠纷解决等基本问题;二是国家金融监管局可进一步细化制度《数字金融消费者保护实施办法》,结合数字金融领域的权益保护问题细化规定;三是省级监管部门结合上位法律法规的规定,再进一步结合并细化规定。如此一来,形成了一个系统化、全方位的保护法律法规,实现金融法治、金融为民。
4 结语
在金融数据和数字技术背景下,世界各国争相发展数字金融,并与时俱进的改进数字金融的监管。由于“监管将对技术的适应性和传播力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且大多数技术并未在现有的监管框架中得以合理规范[1]。因此,建设数字金融强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数字金融监管需要适时创新、不断修正与改进,构建一个数据驱动型、常态化的数字监管框架,力求实现数字金融效率与稳定之间求得良好的平衡。同时,数字金融监管创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
参考文献
[德]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 转型的力量[M].李菁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6.
黄益平,黄卓.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 现在与未来[J].经济学(季刊),2018(4):1489-1502.
姚名睿.数字资产和数字金融[J].清华金融评论,2019(9):95-99.
[美]博登海默·E.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王忆辰,陈双.数字金融研究: 理论渊源、风险挑战与发展展望[J].市场瞭望,2024(8):25-27.
王海军,杨虎.数字金融渗透与中国家庭债务扩张: 基于房贷和消费的传导机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 114-129.
欧阳日辉.中国数字金融创新发展报告(2023)[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何德旭,苗文龙,张晓燕.新时代的普惠金融供给与人民金融需求: 基于创新发展的视角[J].中国发展观察,2018(7): 33-35.
黄行健.数字金融监管套利规制探析[J].河北金融,2024(2):3-8.
宋科,傅晓骏.监管沙盒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应用:兼论我国“监管试点”与“监管沙盒”的异同[J].金融监管研究,2021(9):100-114.
谭雪,邢伊凡.金融科技监管的完善: 地方“监管沙盒”的机制构建[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55-65.
肖翔,丁洋洋,王龙.数字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金融与经济,2021(5):92-96.
黄益平.数字金融发展对金融监管的挑战[J].清华金融评论,2017(8):63-66.
黄益平.如何建设数字金融强国[R].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报告,2024.
谭钰婷.金融科技创新与监管: 以中国香港监管沙盒为例[J].金融科技时代,2024(4):4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