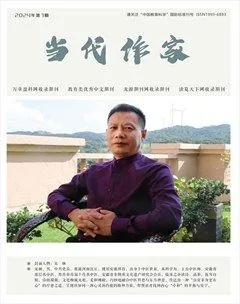父爱如土永留我心
谨以此文,怀念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然十二个年头。时光洪流未曾冲淡我对他的思念,那思念恰似醇厚老酒,在岁月的窖藏中愈发浓烈。每至寂静夜晚,我仰望星空,繁星闪烁如父亲关切的眼眸;在喧嚣尘世中偶然瞥见似曾相识的背影,那微微佝偻之态、迟缓步伐,父亲的音容笑貌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令我感慨万千。
在我记忆深处,父亲与土地紧密相连。他宛如古老坚实的大地,沉默、朴实,却承载起我们兄弟五个生活的全部重量。父亲生于乱世,成长于苦难,他的一生是充满艰辛与奋斗的传奇,而土地是这部传奇永恒的背景。
父亲出生于梅坞里一个祠堂的戏台底下,那是动荡不安的年代。他刚满七岁,父亲便离世,母亲也很快改嫁,张氏家族只剩他孤苦伶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命运的残酷并未将幼小的他打倒,反而铸就其坚韧不拔的性格。他给地主人家放牛,无论寒冬酷暑,天尚未破晓,第一缕微光还在云层中挣扎,他便出发。他身着破旧单薄衣衫,寒风如刀割肤,可那小小的身影在晨雾中自如穿梭。夏日蚊虫嗡嗡乱飞,叮咬得他满身是包,他只是随手挥一挥,目光始终不离牛儿;冬日手脚冻僵,近乎没了知觉,他仍咬牙坚持。牛背上的他,随牛儿步伐轻轻晃动,在与土地的亲密接触中,他不仅学会犁地、种地这些庄稼本事,还对土地脾性了如指掌。从那时起,土地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依靠,他对土地的热爱,如种子深埋土里,随岁月生根发芽。
父亲二十岁那年,农村土地改革,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他分到土地、房屋,拥有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雇农成份,还被按排去学堂学习文化。那时,我仿佛能看到父亲眼中闪耀的光芒,如夜空中最亮的星。他像虔诚的信徒,站在自己的土地上,缓缓蹲下,粗糙大手轻轻抚摸土地,感受其温度和质地,久久端详每一寸土地,口中不停念叨:“好地,好地。”这是他对土地最深沉的赞美,也是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的宣告。在他心中,土地不仅是生产粮食之地,更是他尊严和梦想的寄托。他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要用双手在这片土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
农业合作社时期,父亲风华正茂、朝气蓬勃。虽刚开始对交公土地有些想不通,常坐在门槛上,望着自家地默默抽烟,但他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心,让他很快适应形势,坚决跟党走。在漫长岁月里,父亲成为山村“大集体”的主心骨。有一年大旱,庄稼几近渴死,土地干裂出大口子,仿佛大地干涸的嘴唇。父亲带着社员到处找水源,翻山越岭,脚下草鞋磨破一双又一双。几日几夜未合眼,父亲双眼布满血丝,却依然坚定。找到水源后,他带头挖渠引水,手上锄头挥舞不停,很快磨出血泡,血泡破了,血水和着泥土,他也不停下。白天,他和社员在田间劳作,种田、锄草、掰玉米、拖毛竹,他总是冲在前面。烈日下,他弯腰插秧,汗水湿透衣衫,顺脸颊滴落在田;掰玉米时,玉米叶子在他手臂划出血痕,他也不在意。那勤劳的身影成为田野中亮丽的风景线。晚上,他组织大伙学习文化、提高思想,昏暗灯光下,他拿着书本认真讲解,声音洪亮坚定,用知识为这片土地注入新活力。
父亲最擅长犁田和糊田塍。小时候,我曾随父亲到离村几里地外拾田螺、抓黄鳝,亲眼目睹他干活时的专注和精湛技艺。他用一把四指扁扁的竹柄铁耙,熟练地掏向泥水里,铁耙入水瞬间,泥水溅起,在阳光照耀下形成一道小彩虹。然后他用脚在铁耙上用力踩几下,挖出一大摞田泥,那田泥散发着独特气息,他小心翼翼安放在田塍上,再用铁耙慢慢安抚、夯实、耥严。有时,他甚至弯下腰,双手深深插入泥巴,捧出泥巴,用双手抚平,手上青筋因用力而凸起。他糊弄出的田塍光滑如镜,恰似现今水泥浇铸的村道,严丝合缝,从不渗漏。母亲常抱怨父亲下田干活弄得一身泥浆,邋遢不堪,泥浆溅在他脸上、头发上,衣服上布满泥点,一天要换洗两次衣服。可父亲从不以为意,他干活憨厚老实,不懂“刁滑”,他只知道土地是神圣的,不容丝毫马虎和亵渎,常说:“这是欺负地哪!”
父亲对土地的热爱,不仅体现在辛勤劳作,更体现在对土地的呵护与改良。为使新分土地由瘠薄变肥沃,父亲挑起多年未挑的粪框,开始拾粪生涯。他像寻宝者,熟知猪狗、没栓牛犊排便之处,一有空就拾粪,不放过任何一次顺手拾粪的机会。哪怕从县城丈母娘家回山村,看见车路边有牛粪、狗屎,他都如获至宝捡回家。一次大雨,雨滴如黄豆般砸下,路上泥泞不堪,父亲看到远处有堆牛粪,毫不犹豫跑过去,溅起一路水花。他捧起牛粪,脸上露出满足笑容,雨水顺脸颊流下,浑身湿透也不在意。在父亲眼中,粪不臭,非肮物,特别是发酵的粪肥,有醇厚酒味,是土地的滋养品。在他辛勤努力下,山上飘荡着竹叶清香,村庄周围因他的粪框变得清新、明净,原本无人问津的山地变得黝黑肥沃、充满生机。
我还记得,生产队散伙划分责任田时,父亲用自己抓到的分外肥壮、隐隐有咸味的上等地,跟不愿要的人家换了一块山地。那是位于猫鼻子弯的山地,杂草丛生,高的杂草几乎没过膝盖,在风中沙沙作响,却被父亲视为珍宝。刚分到这块地的头天晚上,父亲兴奋得一宿未睡安稳。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映出他眼中光芒。他坐在床边,仔细磨柴刀,磨刀石与柴刀摩擦的沙沙声在寂静夜里格外清晰。他又整锄头,磨平锄头把上的毛刺,拧牛套时手指灵活穿梭,编筐编畚箕时柳条在手中飞舞……他把农具收拾、整理一遍,仿佛在为盛大庆典做准备。他那高兴劲儿,就像孩子得到心爱的玩具,他是在向世界宣告,将以全新面貌和姿态,投入心仪土地的怀抱,开启新生活。
第二天清晨,天还未亮,父亲叫醒酣睡的我,要带我去猫鼻子湾。他大步流星走在前面,我在后边紧赶慢跑。晨光洒在路边草叶上,把草叶上的露珠染成金豆豆儿,露珠滚动,折射出五彩光。竹枝在微风中摇曳,竹叶摩擦发出沙沙声,仿佛向我们招手致意,还不时洒下几滴含着竹叶香馨的水珠,像是对我早起的慰劳。到了那片山地,父亲引我在一块呈梯形状、长满杂草还有几株玉米的地头转了一圈,他目光坚定,眼神透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那眼神仿佛在告诉我:儿子,你要记住这片地,将来要接我的班,永远耕种下去。他不时弯下腰,捡起小石子,手指在石子上摩挲,感受质地后扔到一边;拔掉柴梗杂物,用力一拽连根拔起;拔掉杂草,甩净根上的土扔到一边。他撮起一把土,放在手心,手指轻轻捻动,感受土壤颗粒感,看看、闻闻后放下,喃喃自语:“这地瘦啊,不浇粪,咋能壮?地和人一样有良心哟,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你尽心伺候它,它就尽力给你出粮食。”
父亲说到做到,他起五更睡三更,贪早贪黑,彻彻底底把地修理一遍,连种植的玉米也不放过。他把阳光晒死的杂草连同周边割来的嫩草和家里担去的粪尿集中堆积,在上面压上厚土,四周糊得严严实实,活像山里人给祖辈砌的坟茔。父亲用锄头把土拍得紧实,每一下都带着力量,边拍边说:“这样肥料才不会跑。”那片不大的山地,父亲花了十几天深耕细作。有个夏日傍晚,至今仍历历在目。无风、闷热,霞光似火,把天宇烧得通红,把地皮烤得炙人。父亲头戴笠帽,笠帽有几道磨损痕迹,赤膊上身,古铜色皮肤上满是汗水,裤脚卷得老高,在酷热中犁地。只见他一手扶犁杖,犁杖木柄被他的手磨得光滑,一手一会儿挥动竹枝,竹枝在空中“呼呼”作响,“哞哞”吆喝几声,一会儿狠压犁辕,腰弯如弓,豆大汗珠从头上掉下,掉在地上瞬间烤干,背上汗水如溪流般淌下,汗水被阳光涂成血红。他身后翻起的土疙瘩,好似三级风刮起的深水波浪,反射着殷红的光。隔一天,他又去耙地,为把板结泥块弄平,他整个人站在耙上,任凭水牯牛托拉。水牯牛低着头,喘着粗气,热气从鼻孔喷出,溅起的泥浆沾满全身,而父亲全然不顾,一心只想把地耙得细腻均匀,那地面在他精心打理下,像新娘子刚梳过的头,平整光滑。那时我刚念完高中,差一点没跨入大学门槛,我一边自学,一边帮父亲照看牲口,还能坐在毛竹窠蔽荫处远远看父亲犁地。每当看到父亲耕垄上汗流浃背,被太阳灼烫成古铜色的背部反射出炫眼光泽,我的心就酸酸的,一阵紧似一阵。那画面中,父亲、犁、牛构成一组剪影,在展开的黑土地上缓缓移动,背景是天似穹庐,赤云峥嵘;翠竹环抱,绿海波涛;山涧青泉,涓涓流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无限亢奋的热力红光,那画面既充满希望,又充满无奈,时隔四十余年,却依然清晰鲜亮、沉郁于心。
在父亲心中,土地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他常对我们说,祖上是朝廷命官,一代忠良,在绍兴是大户人家,因得罪奸臣引来杀身灭族之祸才四散奔逃,田地、家产都被霸占。逃亡途中,族人有的冻死、饿死,有的被抓回去砍了头颅,只剩下我们这一脉。太太婆带着三个儿子落魄流浪到临安,可没过几年,太太婆和两个儿子相继暴病没钱抓药客死异域,幸亏我的爷爷是秀才,会书画琴棋,也会庄户人家的篾匠活儿,才勉强把亲人安葬入土,并在好心人的撮合下定了门亲事。父亲的故事,让我深刻感受到家族兴衰与土地的紧密联系,也明白父亲对土地近乎痴迷的热爱背后,是对家族传承的坚守和对稳定生活的向往。
然而,岁月无情,父亲渐老,疾病开始侵蚀他的身体。接到父亲病重电话那一刻,我的世界仿佛崩塌。我心急如焚赶回家,一路上心乱如麻,脑海中不断浮现父亲身影。却未在熟悉家中找到父亲,忽而想到猫鼻子弯那片山地。当我赶到时,看到父亲脸色蜡黄,如枯黄树叶般毫无血色,额上渗出豆大汗珠,晶莹汗珠顺着皱纹滑落。他一手吃力拄着拐杖,拐杖在地上留下深深印记,一手紧压腹部,身体微微颤抖,站在地角,凝视着颗粒饱满、沉甸甸、密匝匝略已泛黄的麦地,眼神中满是不舍。我心疼地挽扶住古稀之年的父亲,情不自禁脱口而出:“爸爸,身体要紧嘛,麦穗儿我差人收割,以后这地您别操心了,荒就荒了呗!”父亲听罢,一脸惊愕,眼中闪过一丝愤怒,狠狠瞪我一眼,嘴唇颤抖着说:“不孝子,你这是糟蹋地哟!”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土地对于父亲来说,比生命还重要,他对土地的眷恋,已深入骨髓,融入灵魂。
在那之后的日子里,父亲身体愈发虚弱,但只要稍有好转,他仍会往地里去。
清晨,第一缕阳光尚未穿透晨雾,父亲便戴着那顶破旧草帽,缓缓走向心爱的土地。他的脚步不再矫健有力,每一步都带着几分蹒跚,但眼神坚定如初。他扛着锄头,锄头木柄因多年使用已磨得油亮,仿佛诉说着岁月故事。到了地里,父亲先蹲下,仔细查看农作物生长情况。他粗糙的手指轻轻拨开叶片,查看颜色和纹理,就像医生为病人把脉。哪怕发现一丝病虫害迹象,他都会皱起眉头,眼中满是担忧。
接着,父亲开始劳作。他举起锄头,一下一下翻着地,每一次锄头落下,都带着对土地的虔诚。只是动作比以往缓慢许多,每挥动一次锄头,都要停顿片刻,喘几口气。汗水很快湿透衣衫,从额头不断渗出,沿脸颊滑落,滴在土地上。中午烈日高悬,父亲只是坐在地头树荫下稍作歇息。他从布袋里拿出干粮,就着水壶里的水,简单吃几口,目光却始终未离开土地。
午后,父亲继续忙碌。他弯着腰,为农作物除草,动作轻柔精准,生怕伤到庄稼。遇到顽固杂草,他便用手去拔,手上青筋暴起,用尽全身力气。他对待每一株庄稼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细心呵护。傍晚,夕阳余晖将天空染成橙红色,父亲的身影在余晖中被拉得长长的。他收拾好农具,一步一步慢慢往家走,走几步便回头看看土地,眼神中满是眷恋。
播种季节,父亲更是一丝不苟。他会提前选好种子,在灯光下,一颗颗挑选,把干瘪、有瑕疵的种子挑出。然后带着种子来到地里,用锄头挖出一个个小坑,再小心翼翼把种子放进去,用土轻轻覆盖。他一边播种,一边嘴里念叨着什么,仿佛在和土地、种子交流,祈祷它们茁壮成长。他的身影在土地上穿梭,像伟大艺术家创作绝世画卷,画卷里是他对土地满满的热爱和对丰收的期望。
如今,父亲已离开我们十多年,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心中。他像巍峨山峰,屹立在我人生道路上,为我指引方向;又像广袤无垠的土地,默默滋养我的灵魂,让我懂得生命价值和意义。我赞美山庄竹林,那竹林在风中沙沙作响,竹叶相互碰撞,仿佛诉说父亲的故事;我为父亲的精神感动,他的勤劳、坚韧、对土地的热爱,将永远是我前行的动力。我要向世人呐喊:我们要像竹子那样高贵坚韧!我们不能欺负土地,不能糟蹋土地!因为土地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灵魂的归宿,就像父亲对土地的深情,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
在这片承载父亲一生心血的土地上,一幢幢农家小别墅依山而筑、拔地而起,别墅墙壁在阳光下反射出温暖的光,唯一通向外面世界的“扬灰路”如今已“油光满面”,路面平坦干净,满山遍野的毛竹林从自生自灭作薪材到风光无限成为农家“聚宝盆”,竹叶在风中摇曳,发出悦耳声响,而今又轮回到自生自灭少有人问津。这片土地在时代变迁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父亲对土地的热爱和眷恋,永远不会被时间磨灭。我知道,我不仅是父亲生命的延续,更是他对土地那份深情的传承者。我会带着父亲的梦想,向着未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