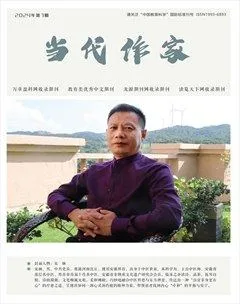血海风云(第十七、十八章)
十七、大婚
街心,东亚商行的牌子新挂起来了,从今儿开始,这里就开始营业了,总经理办公室比较大,装饰豪华,蛋黄流苏的窗帘,吊饰的大灯,真皮沙发,沙发前一个透明玻璃的茶几,紫檀木的老板台,后面的真皮转椅,这里无不是在向人们展示主人的阔绰。许云飞迈着轻快的脚步进了屋,喊道:“小何,小何。”
小何是一个瘦削的小伙子,个头中等,虽说瘦了点,但是可结实,国字脸上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挺阔的鼻子,嘴角分明,倒也干净利落,他听见喊声应声进来来,道:“经理,什么事?”
许云飞看着他,说道:“昌盛隆米行的票子送来了吗?”
小何答道:“经理,还没有。”
“这不就送来了嘛!”走廊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窦静芳一件绿色的连衣裙,头上戴着凉帽,胳膊上戴着防晒的白色蕾丝手套,拎着一个小巧的手提包,袅袅婷婷进来了。
许云飞朝小何摆摆手,小何出去了,他说道:“哟!
这位是……”
窦静芳看着他,道:“窦静芳。”她从包里掏出几张票子递了过去。
许云飞看着她,接过票子,看了一眼,道:“哦,窦小姐,幸会幸会!想不到这么快你就把票子送来了,我能问一句,你和这个昌盛隆米行是什么关系?”
窦静芳微微一笑,道:“你有必要知道吗?”
许云飞点头,道:“也是啊,一会儿,你拿走定金,等我们装完了货,你再来取剩下的尾款。”
窦静芳看着他,轻描淡写地道:“好吧,告辞!”
许云飞道:“我好像……”没等他说完,窦静芳已经消失在门口,他愣住了,又敲了敲头。
顾东一个人在河边坐着,他后悔极了,要是那天他拦住大哥顾大风,可能他就不会牺牲了,他揪着旁边的草,在手里拧扯着。过了一会儿,他拿起旁边放着的酒瓶倒了一杯酒,举起来说道:“大哥,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在这里玩耍,现在你却先离开了,大哥,你放心,只要咱们老顾家还剩一个人,就和鬼子斗争到底,义勇军那边三伯父已经接手了,你不必挂念,大哥一路走好!”
他举起酒杯慢慢地把酒倒在了地上,李光军和钟启明来了,李光军接过他的酒杯也倒了一杯,道:“大哥,我和顾东从小一起长大,是好朋友更是好兄弟,我们同年不同时,他的大哥就是我大哥,当初劝你成立义勇军我也和顾东说过这事,没想到队伍拉起来不长时间,大哥就永远地离开了,不过请大哥放心,我们一定会坚持打鬼子,直到把鬼子赶出中国。”李光军把酒倒进了河里。钟启明接过酒杯也倒了一杯,朝天敬了敬,道:“大哥,你是英雄,一路走好!”
顾东擦了擦泪,道:“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能来和我大哥道别。”
三个人站在河边,望着远处,波光粼粼的河水。
一架飞机从天空掠过,钟启明沿着飞机的方向比划了一下,道:“是日军的飞机,去北城?”
李光军道:“莫非马震庭在北城?”
几个人朝路上跑去。
等他们到了北城的时候,已近中午,城里到处是残垣断壁,刚刚经历了一场浩劫的城,浓烟滚滚,四处惊慌躲避的人们,街上一片狼藉。一个小女孩还在满是碎片泥土的地上蠕动,钟启明上前把她托在怀里,叫了她几声,她还活着,睁开了稚嫩的眼睛,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小女孩在他的怀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不远处,一个女人躺在地上,肠子都出来了,半边脸已经如焦炭,剩下半条腿露出瘆人的骨头,钟启明搂紧了小女孩,把她的脸扳在自己怀里,不让她看见。
李光军和顾东跑了回来,道:“没看见几个活着的人,那边广场,被日本人枪杀了不少,血都成河了。”
顾东道:“他们把全城的人赶出来,逼他们说出马震庭藏在哪里,没有人站出来,所以鬼子就朝人群开枪了。”
“作孽!这个孩子跟我回家吧。”钟启明打定主意,说道。
顾东和李光军看着他,又对视一眼,谁都没说话。
回到自己东三里屯,他把孩子放到家里,李东山看着,他去了宋三毛那,欧阳晨远刚好在前面,她买了几根麻花,转身走的时候,看到钟启明瞪了他一眼。钟启明掏出钱要了三根麻花,宋三毛低声道:“上级要你启用电台。晚上12点,波段233。”钟启明记好了,拿着麻花走了。他心里想着事,没走出去多远,就听见前面的的欧阳晨远说道:“你跟着我干什么?”他还一愣,不假思索道:“你们中学的老师都喜欢侍候日本人是吗?”欧阳晨远一听火冒三丈,指着他说道:“你跟踪我?”钟启明怒道:“侍候日本人是不是感觉很好?”“啪”一个嘴巴落到他的脸上,他皱着眉头,刚要说什么,就听见欧阳晨远喊道:“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下次就不是一个巴掌的事了。”
钟启明望着她的背影,摸着自己火辣辣的腮帮子,朝地上啐了一口。
顾家家里静悄悄地,除了顾文山在东屋,顾东在西屋,今天没有人来打麻将,都知道顾大风新丧,大伙就暂时不来了。顾东在门外听见父母在商量小时候给他定的娃娃亲的事,他就没进屋。
今天的会就改在钟启明家里开了,李光军和顾东进屋,三人刚坐定,孙九风风火火进来了,道:“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马震庭在双岔河消灭了300多小鬼子,又在通肯河和日军的松木师团打起来了,击毙日军200多人呢,真是个大好的消息。”说完了,再看大伙都面无表情。他又道:“是不是你们都知道了?合着就我知道的最晚是吗?我这在大山里,和你们的消息慢半拍啊。”
李光军道:“还好,知道晚总比不知道的强。”
大伙都坐好了,钟启明道:“省委通知我们,七月准备发展一批党员入党。”
李光军激动道:“太好了!入党可是我们每个人的理想,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那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啊,我当初入党的时候别提多高兴了。”
顾东道:“入党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
孙九搓着手,没说话,这里就他文化水平最低。
钟启明道:“这次李光军和郭振华推荐的顾东同志正式通过了,孙九同志五月份的时候刚加入了共青团,最近表现也很突出,省委也决定吸收他为正式的共产党员。”
孙九很激动,道:“真的吗?太好了,我一定更加努力地干工作,打鬼子。”
傍晚的时候,顾东去了林丽家,开门的是肖月,听见说话声,来到门口,问道:“你来有事吗?”
顾东看了她一眼,道:“我……我有一件事想要告诉你。”
肖月在屋里说道:“找林姐姐呀,怎么不进屋说话?
你们两个一个门里一个门外的,真新鲜!”
林丽嗔怪,道:“去去去,你去吃饭去吧。”
肖月扮了一个鬼脸朝后屋走去。
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顾东和林丽站在树下说着话。
林丽道:“最近,学校里忙吗?”
顾东道:“又来了一个新老师苏凤友,能忙的过来。
你们妇救会这边怎么样?”
林丽:“妇救会正准备游击队和周边的抗日武装做过冬的衣物,能给部队准备多少就准备多少,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总不能让战士们挨冻打鬼子吧。”
顾东道:“战士们有你们做后盾真是无后顾之忧,他们的冬装也算有着落了。”
傍晚的夕阳从树的缝隙里投射到林丽光洁的脸上,她的眼睛清澈透明,顾东不禁看着。
林丽不好意思捋了捋腮边的头发,道:“你看什么?
真是。”
顾东赶忙收回目光,道:“行了,我有事先走了。”
林丽道:“诶,你不是有事要告诉我嘛!”
顾东站住,没回头,低声,道:“没有了。”
林丽看着他的背影,道:“神经!”说着,自己却笑了,她捋了捋头发,揪了一片树叶迈着欢快的步子进屋了。
顾东回到家的时候,家里大门敞开着,院子里一片狼藉,他赶忙跑到东屋,屋子里很乱,衣服被扔了一地,椅子倒在地上,茶杯碎了一地,零碎的东西散落到处都是,他爹和顾久正在收拾东西。顾东怒道:“爹,这是怎么了?”顾文山轻描淡写道:“还能有谁?狗腿子呗。已经来过了。”他拉着顾文山的手,看着他爹,问道:“爹,你没事吧?”顾文山道:“孩子,爹没事,他们就说你大哥顾大风是义勇军,说咱们家藏有武器,什么都没搜到,能把我怎么样?”顾东道:“爹……我和你们一起收拾。”
收拾完了以后,顾文山拉着他朝后院走去,他爹拿铁锹挖着,旁边放着油布。当啷一声好像铁锹挖到了什么,顾文山扔下铁锹,伸手扒出地里的东西,几把长枪和一些子弹,顾东扯过油布,包好长枪,两人拿着藏到了老屋的椽子上。
忙完了这一切,顾文山拉着他坐到炕上,意味深长地说道:“爹和你娘想把你的婚事办了。”顾东喝的一口水差点喷出来,顾东道:“爹,我都这么大了,这事您老……”没等他说完,顾文山拦住他,继续说道:“你知道你小时候定的娃娃亲,就是西头老张家的闺女,现在我估计那孩子也十八九了。”顾东道:“爹,我的事您就别操心了啊。”顾文山还不死心,道:“爹也不想管,可是咱不能说话不算数,辜负了人家,定亲的事乡里乡亲都知道,街坊邻居都说人家姑娘早晚是咱们顾家的人,咱不能坏了人家的名声。”顾东道:“以后再说吧,我下午还有课,我先走了。”说完,他逃也似的出了家门,顾文山在后面喊着:“还没吃饭呢。”顾东头也不回地说道:“不吃了。”
钟启明傍晚回到家的时候,还没进家门就看见胡毛毛在屋门口朝他招手,他迟疑了一下,进了院子,胡毛毛朝屋子里看了一眼,轻声道:“叔叔,有个阿姨找你,在我姑奶这屋呢。”
他拉着胡毛毛进了屋子,向梅梅也在,就是他在北城大爆炸中救回来的那个小女孩,她比胡毛毛小一岁,两个人还真能玩到一起去。一抬头,他发现欧阳晨远在炕上坐着,正和胡大娘说话,这就是胡毛毛说的阿姨,他转身就要走。胡大娘招呼道:“启明这不回来了,呵呵,今晚就在我这屋吃晚饭吧?正好这个姑娘说是找你的。”他本打算不理欧阳晨远,但是一听胡大娘这么说,自己就算有再大的气也不能薄了人家老人家的脸面不是,他笑道:“胡大娘,这个姑娘找我有点事要商量,我们去那屋,晚饭就不在您这吃了,我把梅梅也领过去吧,这一大天的多亏您给照看着,谢谢您了。”
回到自己的西屋,他哄着梅梅,给她弄了点吃的,欧阳晨远在屋子里坐着,他一句话都没和她说,欧阳晨远也不想和他说话,可是她还是开口了,道:“你这个住址是顾东告诉我的,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吗?我没有时间闲的看你做家务。”钟启明正在看着梅梅吃饭,头都没抬,道:“那你可以走,不送!”欧阳晨远拿起自己的包站起来,朝门外走了几步,又站住了,转身回来坐到了炕上,道:“我告诉你,省委派我和你一起掌握敌人的电台。”钟启明心里失落到了极点,前几天从宋三毛那传过来的消息,说要给他派个懂通讯技术的一起和他工作,此时,他才明白,这个人就在眼前,一点波澜不惊都没有,还是自己的冤家,他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可是又不能赶她走,他一想起那一巴掌心里觉得别扭的很。
梅梅吃完了饭,李东山带她出去玩了。
屋子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不愿意面对的人也得硬着头皮应付,还得共处在一个空间里,这世界有时候真是奇怪,他边洗着衣服边想到。
欧阳晨远估计也在揣摩他的心思,站了半天,她一声招呼没打拎着自己的包走出了门。
清水一正在办公室里看着什么,小野敲门进来了。清水一正看了他一眼,道:“都安排好了。”小野道:“报告大佐,人是送进去了,只是这两天没有消息传回来。”
清水一正把文件合上,道:“不要着急,告诉他,让他站稳了脚跟,注意隐藏自己。”小野站直了,道:“哈衣!”
窦公馆里,窦静芳正一个人坐在床边发呆,她今天下午从东亚商行出来的时候,看见清水一正带着伊藤进了许云飞的办公室,她的心里“咯噔”一下,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疼的要命。春梅送进来她最爱的酸梅汤她也无心喝,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她脑海里又出现清水一正和伊藤的身影,她皱着眉头,嘀咕道:“难道这个许云飞是给……”她不敢往下想,索性起身,到窗口透透气,本来就热的天,她感到自己更烦躁了。
这几天,欧阳晨远也不和钟启明说话,反正就是每天下午准时到他的家里报到。这天,她和梅梅在屋子里玩,就听见门响,钟启明回来了。
她拎着包刚要走,梅梅拽着她的衣角,喊道:“阿姨,别走别走!”
“阿姨还有事!改天陪你玩!阿姨还有事,要是误了正事可不行哦!”
“电台装好了!你跟我来吧!”钟启明知道这话是说给他听的,也是,人家天天来报到,也是尽到责任了,自己如果再不分配工作,就是自己的问题了。
地下密室里,欧阳晨远在电台前小心翼翼找着波段,电台里发出滋滋滋嚓刺耳的杂音,她把耳机往耳后移了移。钟启明正在翻阅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日文,通过前一段时间的自学,简单的他还能看懂,复杂的他就全凭猜了。
转天下午,在顾东家里,钟启明、李光军和林丽都在干活,订的订,印的印,很快一摞宣传材料眼看就要弄好了,李光军看着顾东,笑道:“诶,顾东,你说你这么能干,西头张家的姑娘嫁给你真是有福气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林丽手里的订书器差点订在自己的手指头上,她“哎呀!”叫了一声,钟启明道:“怎么了?我看看。”林丽面无表情,道:“没事。”顾东停下手里的滚轮,看着她。李光军毫无察觉,继续说道:“听说那个女孩长的不错呢,你们见过没有?”林丽把手里的小册子一推,道:“我订完了,我还有事,先走了。”钟启明道:“诶,一会还有呢。”林丽扯过凳子上自己的小菜篮,转身就出门了,由于用力过大,凳子翻倒在地上。顾东拿着滚轮,刚要说什么,嘴巴张了张没说出话。钟启明看看林丽消失的方向,又看看顾东,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乡村的小路上,傍晚的夕阳斜照在树木、草地上,一切都显得那么悠然自得,要是没有战争这该是多么美的一副画面。钟启明和顾东默默地走着,谁都没有说话,过了很久,钟启明说道:“我们是有信仰的人,信仰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海上的灯塔,是黑暗里明亮的光芒,指引着我们前行,为了信仰纵然粉身碎骨也不怕。有时候,我们就要管住自己这颗如脱缰野马一样的心。”顾东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天边的夕阳,他想去告诉林丽,可是那么做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要违抗父母之命?置另一个无辜的女孩于水深火热之中?
无形之中,他觉得自己的心在疼。
曾经,钟启明的心也疼过,只是他自己在竭力控制着自己,让自己火热的心的温度一点一点降下来,因为,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有时候有些人的梦已经开始了却不得不结束,而有些人的梦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百天以后一个吉利的日子,一辆马车稳稳当当地朝顾东家驶去,车上坐着一个身穿学生装的女孩,头上扎着两个长辫子,车夫一身干净的短衣长裤赶着马车,顾东穿着一身学生制服跟在车旁。顾家门口聚集着乡里乡亲,有人在悄声嘀咕着:“噢,新娘子真新鲜。”
一个女人低声道:“怎么没穿红?”
另一个女人接道:“是啊,连红盖头都没有。”
来到门口,顾东伸出手扶着车上的张玉秀下车,两人站好。
董汉池从屋里跑出来,大声说道:“乡亲们请安静!
我叫董汉池,是新郎的同学,今天是他大喜的好日子,我也没准备稿子,就即兴说几句,父老乡亲们,同学们,今天这个婚礼是新式婚礼,现在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提倡男女平等,中国妇女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是受人压迫和奴役的对象,她们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尊严,头顶戴着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恪守着“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依附在男权社会的男性威严之下,受人欺侮,是受人宰割的下人,我们要改变这种落后的思想,我们要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所以,今天这场婚礼大家看到了新娘新郎的面貌是全新的,仪式也是不一样的。”
刚才还在小声议论的人们开始热烈鼓掌。正当大家高兴的时候,郭景山慢慢地走近新娘盯着她看,人群静了下来,他又移步到顾东面前,盯着他,道:“哟!今儿个挺热闹,怎么能少了我的祝福呢?”郭景山话音刚落,身后闪出一个人——二狗,他手里端着一个盒子,道:“这是郭团长送给顾先生的贺礼。”
顾东把张玉秀拉到自己身后,道:“郭团长的贺礼我怎么能随便收呢?”
郭景山不紧不慢,道:“别人的贺礼都收了,单单不收我的贺礼岂不是不太好吧?”
顾东想了想,道:“那好吧,顾顺, 把贺礼拿进去。”
顾顺接过贺礼,转身要进院子。郭景山道:“诶,你不看看是什么?”
顾顺转身停下,看着顾东,顾东挑开盒子一角,里边是两颗子弹,顾东冷笑,道:“我真希望这样的礼物你能多送些,我很喜欢。”
郭景山由刚才的嬉皮笑脸换了一副凶狠的嘴脸,道:“哼!恐怕今天你要跟我们走一趟了。”
他朝后面一挥手,上来两个伪军。
十八、酒吧
郭景山正要带走顾东,突然,一声断喝传了过来:“慢着!谁在这里撒野?”
众人皆转头看去,黑雕带着自己的弟兄从人群里走出来,把郭景山的人团团围住。
郭景山看看了自己被围在中间的人,嬉皮笑脸道:“哟!雕爷也在呢?”
黑雕目不斜视,冷冷道:“我兄弟的婚礼,谁要是闹事别说我手里的这杆子枪不答应。”说着,他举起枪咔咔咔拉起了枪栓。
郭景山点头哈腰道:“雕爷,没人闹事,有您在谁敢呢?兄弟我还有公事先告辞了,告辞了。”
郭景山转身灰溜溜地带着他的伪军钻出了人群。
钟启明在火车站放出了一列火车后,走回到办公室路上遇到了商海潮,他才知道,原来商海潮也来车站工作了,而且是接替石师傅调度的位置,跟着陈师傅熟悉工作环境去了。两人约好,晚上下班后一起喝酒,好久不见了,叙叙旧,趁着天还大亮,他先要去顾东新搬的家和他见一面,二人聊了几句就相互告别了。
永和隆后院就是顾东新住址,这是一溜平房,中间有一条小路将两边的房子分开。永和隆是一家珠宝典当行,门前天天有达官贵人进出,偶尔也会有穷人去典当。钟启明到的时候,李光军和孙九也在,屋子里南北各有一铺炕,一张桌子,几把椅子,陈设简陋。
李光军朝四周看了看,说道:“我说顾东,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住处?”
顾东道:“这所住处可不好找,没听说过嘛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这时,门外外屋地一阵门响,钟启明透过门缝朝外望去,一个警察从东屋里走了出去。
钟启明道:“你这胆子可是够大的,和警察东西屋住着。”
几个人落座,李光军道:“今天,我来这是有件事和大家商量。孙九带着西南乡红枪会的沈建业联系了城东红枪会谢堂主,想跟鬼子干一场漂亮的仗,只是弹药不足是个问题。”
顾东道:“我家还有一些,给你们送去。”
孙九道:“顾东的老爹已经送了好几次弹药了,可是总这样也不是办法。”
几个人陷入了沉默。
过了一会儿,钟启明道:“我有办法。”
李光军抬头疑惑地看着他,道:“你有什么办法?”
钟启明道:“孙九把你的游击队借我用一下,保证明天我让你见到弹药。”
孙九看看李光军又看看顾东,道:“噢?你真这么有把握?”
钟启明点点头,他又说道:“马震庭前一段在北城天兴泉烧锅、广信当和平贺旅团、思贤大尉打的好,出了一口恶气,最近在罗圈店和松木大佐打了一个漂亮仗后,部队要去东边和李杜汇合,在路上遭遇了日本鬼子的袭击,损失惨重,已经向东北退到了苏联境内。”
屋子里很静,大家都知道,和敌人的斗争是残酷的。
街上行人行色匆匆,街心一个拿着吉他的苏联人在孤独地在弹着。
东亚商行,总经理办公室里一阵电话铃声响起来,许云飞拿起电话,道:“喂!东亚商行,什么?烟土?这个东西太敏感了,还是算了吧。”他放下电话,把小何喊进来,问道:“新来的王副经理每天都干什么?”
小何道:“也没见他干什么,就是晃来晃去的。”
许云飞走近他,低声道:“给我盯着点,他是不是安插他的人进来了?你把我这屋的钥匙收好了。”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做了个圈的形状。
小何意会,点头,高声道:“经理,您是要我沏茶吗?”
许云飞高声道:“每天都沏茶你不知道吗?还问。再记不住,我就辞了你。”小何开门出去了,许云飞朝对门副经理办公室看了看。
小酒馆里商海潮有些微醉,道:“我爹不让我出来,让我在他的庇护下干活,我就是一个闲人,我……不喜欢。”
钟启明道:“对,男子汉就应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安逸那是属于女人的。”
商海潮笑笑,道:“女人?你知道白露吧,她结婚了,和……那个小白脸,叫……秦一天。”
钟启明没说话,他拿起自己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又给自己倒上。
商海潮没发现他的变化,接着说道:“秦大公子……
光接亲的车就……就占满了整条街……整条街。”
钟启明端起酒杯一口喝了下去,烈酒在他的五脏六腑里燃烧,他想忘的那个女人,商海潮又给他带来了消息,只是这个消息不是他想听见的,他知道,从此,两人各自天涯,永无交集。
商海潮伸手过来抓他的酒杯,道:“你别光顾……光顾自己喝。”
晚上回到自己的家,钟启明拿出上次给白露拍的还没寄出的照片,他一张一张地看着,那个身穿白色大衣,扎着红围脖的女人,永远属于另一个男人了,酒劲上来,他拿着照片睡着了,照片一张一张掉在地上,他都没察觉。
欧阳晨远一个人在地下室,一阵叽哩哇啦的声音从发报机里传来,她皱着眉头细听,那声音仿佛一下就消失了……
小岛酒吧里灯火透亮,摇滚乐震耳欲聋,夜,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一天的开始。
窦静芳一身白色衣裙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发呆,面前放着一杯红酒。
吧台上有三个喝的醉醺醺的男人东瞅瞅西看看,一个穿着西装,其他两个人,一个穿着花短衫,一个穿着黑短衫。。
许云飞被桩子、独角兽、狮子头、小何拥着进来了,他扫视了一圈屋子里,捡了一个宽敞的位置坐下了。
小何喊道:“老板,威士忌加冰。”
老板答应一声,侍者很快上了酒。
许云飞觉得角落里的人影有点熟悉,嗨,管他呢,爱谁谁,现在可是休闲的好时光。
小何换下了白天的长衫,穿着西装,虽说个头小了点,还挺精神,端着自己的酒杯晃了晃,道:“听说这里今晚有节目。”
桩子道:“我也听说了,不知道真假。”
独角兽不屑一顾,道:“管他真假呢,有酒,先喝足了再说。”
狮子头笑道:“我说独角兽,你娘咋给你起名字的,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字?”
独角兽冷笑,道:“哼!我看你的名字也不怎么样。
还狮子头,一听就是个下酒菜。”
狮子头道:“我呸!你拿老子下酒试试?”
许云飞抽着烟,听着他们几个的对话,笑了。
独角兽道:“你看大哥都笑你呢。”
狮子头喝着酒自己笑了。
吧台上的西装男盯着角落里的窦静芳半天了,他端起酒杯摇摇晃晃朝她走去,两个短衫男看着他,没动地方。
窦静芳拿起酒杯,与眉平齐,透过酒杯望着里面紫红色的液体。
西装男一只手搭在她的肩头上。
窦静芳头也没抬,冷声道:“把你的狗爪子拿开。”
西装男的手没有拿开的意思,窦静芳使劲一甩,居然像粘上了一般,没甩开,她厌恶地看了一眼西装男,喊道:“把你的狗爪子拿开。”
西装男嬉皮笑脸,道:“哎呦!小姐的口气好重啊,火药味真大。”
窦静芳用另一只手将他的手打开。
西装男晃晃手,道:“没事,今儿大爷我心情好,我都看你半天了,是不是一个人寂寞了,走,跟爷走,爷带你去个好地方玩玩。”
“哗”西装男的脸被窦静芳的酒泼了一脸。
西装男大声道:“妈的!还是这样的女人有味道。”
两个穿短衫的男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从椅子上起身,摇摇晃晃朝角落走去,许云飞寻声望去,小何也望向角落里,他要起身,许云飞按住了他,朝他摇摇头。
窦静芳拎起自己的小包朝门口走去,花短衫男挡住了她的路。
窦静芳道:“滚开!”
黑短衫男朝窦静芳脸上摸去,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的手要碰到窦静芳的脸蛋时,一只手抓住了他在半空中的手,扔到一边。
许云飞不紧不慢坐进椅子里,跷起二郎腿,道:“这样以多欺少不好吧?”
黑短衫男道:“关你屁事!滚!”
许云飞喝了一口威士忌,悠悠地道:“今天还真就关我的事了。”
挡路的花短衫男朝他扑过来,许云飞抬起一脚,只见那个男的扑通坐到地上滑溜出去好远。咚!一下撞到了墙上。
许云飞抖抖自己的西装,又喝了一口酒。只见黑短衫男和西装男朝他扑来,他拧过黑短衫男的胳膊,一用力,只听见“咔嚓”一声,那个黑短衫男杀猪般叫唤着,西装男拿着酒杯本来想砸许云飞,哪成想整个人砸了过来,许云飞起身,西装男扑进椅子里,许云飞抬脚踩到他的背上,只听西装男喊道:“大哥,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大哥,你放了我吧。”
摔出去好远的花短衫男拎着椅子扑上来,许云飞一闪,椅子砸在西装男后背上,许云飞踹他一脚,他趴在西装男的后背上,西装男在下发出惨叫。
花短衫男哀求道:“大爷,你是哪方大爷?饶了我吧。”
许云飞朝两人各踢了一脚,道:“滚!”
三个人踉踉跄跄朝门口而去。
窦静芳也朝门口走去。
许云飞看着她的背影道:“人家给你解了围,怎么连句谢谢都不说。”
窦静芳站住了,不回头,少卿,她又朝门口走去。
小何从后面上来,道:“你认识她?”
许云飞酌了一口酒,没说话。
夜已深,茶楼上欧阳晨远和顾东在说话。顾东手里攥着茶杯在思考着,欧阳晨远看着他。
欧阳晨远道:“我觉得那张日本人手里的海城军事城防图对于我们来说会有很大的用处。”
顾东道:“但是要弄到它风险很大,况且你上次不是在清水一正的家里遇到女杀手了嘛,这证明他那表面上好像就住着他们兄妹两人,其实,还是另有守卫的。”
欧阳晨远道:“上次那个女人应该没认出我来。”
顾东思索着,道:“再等等,等个合适的机会下手,不可着急,你千万不要一意孤行。”
欧阳晨远道:“那好吧。”
顾东道:“诶,你今晚发现电台联系不上省委,还有电台里出现的日本人的声音你告诉钟启明了吗?”
欧阳晨远一脸厌恶的表情,道:“你都不知道他今天喝的那个样子,睡的跟死猪似的,叫都叫不醒。”
顾东笑道:“你这是偷窥了人家睡觉,我说你们两个真是有意思,受伤吧都是同侧的胳膊,位置也不相上下。
哎呦呦。”
欧阳晨远一指他,道:“诶,我说你可别瞎说啊,那就是巧了,我走了。”
已经很晚了,店里要打烊了,顾东也要起身离开。
顾东出了门,墙角里闪出一个戴礼帽的黑衣人跟了上去。店小二看见了,朝路边的乞丐招了招手,他从兜里掏出几个铜板给了乞丐,和他耳语几句,又朝地上的泔水桶指了指,乞丐接过铜板,拎起泔水桶朝黑衣人追去,在背后从头到脚把泔水浇了上去,黑衣人吓了一跳,怒道:“妈的!干什么你?”乞丐朝他傻笑着。黑衣人再一看顾东和欧阳晨远已经没了踪影,店小二上好了门板,从门缝里朝外望着,偷笑着。
川崎一郎今天才感到痛快一点,前一段,广信当的日本兵被马震庭和鲁军长他们给杀的血流遍地,那个惨呢,墙都染红了,在北城除了他们屠杀了一些老百姓,连马震庭的影子都没看见,东罗圈店一战又让他损失了上百人,自从进了海城自己一直就处于被动的局面,松木师团追的马震庭朝东北跑去,围追堵截,虽说没消灭马的队伍,但也把他们赶到苏联去了,自己终于有时间腾出手对付地下党了。
山泉是一个小地方,孙九带着沈建业到了红枪会寨子门口就被门口守卫的红缨枪拦下了,就听得一声喊:“口令!”
孙九看了一眼沈建业,沈建业道:“红缨枪,红缨枪,枪缨红似火,枪头闪银光。”
二人才被带了进去。
谢堂主早已等候在正堂,三人见面,他抱拳道:“这不是沈堂主吗?近来可好?”
沈建业抱拳,道:“谢堂主,好久不见,自从小鬼子进了咱们这十里八乡的,哪里还有好日子过,别提了。”
他指着孙九说道:“这是海城游击队的孙九,孙队长。”
谢堂主抱拳道:“孙队长,幸会幸会。”
孙九也抱拳道:“早就听说谢堂主的大名,今日有幸相见,是我孙某人的福气!”
三人寒暄后落座,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给三人上了三杯盖碗茶。
孙九道:“东三省沦陷了,现在哪里的日子都不好过,到处都是日本人。”
谢堂主怒气冲冲道:“这日本人欺压百姓、烧杀抢虐啥子都干呢,现在我一看见那一身黄皮子,我的牙恨的痒痒的慌。”
孙九道:“那谢堂主有没有想过怎么对付日本人?”
谢堂主叹口气,道:“我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要枪没枪要人没人,真想跟小日本干上一仗,可是拿什么跟人家较量?唉……”
孙九一拍桌子,道:“好,有你谢堂主这句话就够了,咱们三家联手,狠狠地揍小日本一场。”
谢堂主很惊讶,道:“孙队长,此话当真!”
谢堂主看了一眼孙九,又看看沈建业,沈建业朝他点点头,他喊道:“好,就这么定了,备酒!”
大白天的郭景山又去了顾家,顾家院子里正晾着土豆、豆角的干菜,郭景山带着伪军一顿乱翻,掀翻了院子里的东西,干菜散落一地,他还不过瘾,喊道:“给我搜!”
顾文山从屋子里冲出来,喊道:“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郭景山一脚将他踹倒,恶狠狠地道:“老不死的,你乖乖地把你家的共党给我交出来,我不会为难你,否则……”他举起枪朝顾文山的头上比划着。
顾文山从地上爬起来,不紧不慢,道:“我们可是守法的人。哪里来的什么共党?”
一个伪军从屋子里跑出来,道:“报告团长,什么都没有。”
郭景山围着顾文山转着圈,道:“我说老不死的,你以为我是个傻子?哼!”说完,他朝屋里奔去。
屋里已经被翻乱了,郭景山在屋子里转悠着,他的目光落到了房椽子上,朝一个伪军喊道:“给我上去看看。”
伪军找了个梯子爬上椽子,仔细看了看,道:“什么都没有。”
郭景山朝顾文山喊道:“你儿子呢?”
顾文山打扫了自己的衣服,不紧不慢道:“儿大不由娘,我怎么知道他去哪了?”
郭景山怒了,指着他道:“你……好,好,你给我等着。早晚有一天,我……”郭景山咬咬牙,恨恨地带着人走了。
顾静从屋子里跑出来,扑到顾文山的怀里,喊道:“爹……”
顾久一掀帘子出来了,道:“爹,刚才可把我吓坏了,东西呢?”
顾文山拍着顾静的后背,道:“早让我送走了,送到游击队去了。”
三个人谁都没有说话,怒目而视着郭景山消失的方向,等那个可恨的身影消失了很久,三人才开始收拾屋里屋外被翻乱的东西。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