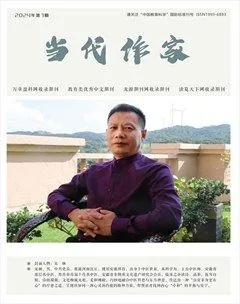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王永江,是一位坚韧而朴实,老实厚道,默默勤劳,正直平凡而伟大的老农民。父亲诞生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年代,岁月在他脸颊上雕刻出深深的皱纹,皮肤经风霜晒得黝黑粗糙,那双粗糙,厚实有力的双手,布满了老茧和裂痕。父亲的身影,饱经风霜的脸庞让我记忆犹新,至今在我的脑海里萦回。
父亲是在不惑之年当上了屯子里的官—吉林省洮儿河北岸七棵树屯的生产队队长。父亲的官是靠成熟稳重,为人厚道,吃苦耐劳,凭他一把好农活被社员们投票选出来的。那时能当上生产队长,确实是个美差事,用老百姓的话说,得“根正苗红”、祖上有德,才能干上这个角色。
生产队长是队里的一把手,很有实权。封建帝制时,朝廷最大的官是皇上。而生产队长就是当地的小“土皇上”。一个几十户人家的生产队队里的生产,社员的生活,都由生产队长统管。母亲为此而感到骄傲,我们兄弟也感到脸上有光,全家人都很高兴,因为当生产队长不仅是个官,主要是一年可比其他社员多拿两三百的工分,生活能宽裕一些。毛泽东时代的村官都是两袖清风,没有人请客送礼,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到年头只是按工分多分一点钱。然而父亲自己且并没有多么大的荣耀和自豪,认为这是责任,不但要带领社员们干好农活,侍弄好庄稼,还要让社员们不再吃返销粮,多分点钱,于是农林牧副渔都纳入了父亲“执政”统筹规划之中,要干的事儿实在太多太多,一干就是八年。
记忆中的父亲,从上任起就没好好睡过一觉,好好吃过一顿饭,好好休息过一天,总是起五更,爬半夜,经常要比太阳早起一杆子多高,匆匆忙忙地扒了几口饭,就“当—当—”敲响了挂在我家园子那棵榆树上的用炮弹皮做的大钟。那清脆而又洪亮的钟声,划破了晨空的寂静,在屯子的上空回荡,飞进每一个农家,它像出征的号角,男女社员听到钟声,拿起劳动工具纷纷来到生产队。这时父亲便开始调兵遣将、分工调配:出几台车,干什么活,南下洼地出几副犁;北大坑地由谁领工铲苞米;西岗子出多少妇女薅谷苗;东大排出多少劳力给葵花打丫枝……,积肥的、喂猪的、放牧的各执其任。一时间,浩浩荡荡的男女社员,奔赴劳动场地,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劳动。于是,田野里、小道上、积肥场上,清脆的鞭哨声,吆牛喝马声,笑语声此起彼伏,汇成了一曲迷人的乐章。各项农活安排好之后,生产队的大院子里才渐渐平静下来。这时父亲便深入到各劳动场地,走走看看。是否有偷工减料和误工现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然后,便来到农田干大帮活的社员中检查质量。比如,春天刨茬子时,便在刨过的垅上检查质量:看看有没有打茬管的,有没有连筋倒的,有没有大搬家的……,发现哪个社员劳动质量粗糙,便记下来……。父亲是原则性强,不徇私情的官。
生产队长这个官儿,是上挤下压受气的夹板,是最不好当的官儿。天天和社员打交道,都在一个屯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老少爷们,沾亲带故,扯耳动腮,牵一发动全身,软了不是,硬了也不是。再说了,偌大一个生产队,瓜子里嗑出个臭虫——啥仁都有:老实巴交的、不惧硬的、爱耍嘴皮子干活儿瞎胡弄的……,总之,无论是“龙”还是“熊”,都得让他们吃碗饭。那时的生产队里还有一名政治队长,专门负责“抓革命,促生产”、抓阶级斗争和社员的思想工作,但是派工安排活还得生产队长说了算。父亲既是生产队里的“一把手”和“主心骨”,又是十足的“受气筒”。清晰的记得:表叔家的孩子,我叫他哥哥,不爱读书,辍学去生产队里干活,因为对农活还不熟悉,父亲安排他先当半拉子和妇女们一起踩格子。他嫌工分低,当半拉子丢人不去干,还去我家和父亲大吵大闹,抢了父亲饭碗不说,还掀翻了饭桌,幸好母亲在中间调节劝说,才得以平息这件事。
父亲是一位合格的共产党员,更是一位合格的村官儿。他对他的官职极其负责,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了生产队。把家里的事情全部交给了母亲,我们家里兄妹7人,母亲起早贪黑,忙里忙外操碎了心。
清晰的记得,在我十六岁那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妹妹突然呕吐不止,母亲要求父亲派马车到十华里外的公社卫生院去给妹妹看病,父亲却说天亮了,正是秋收时候,队里太忙没有车,没有时间,就上工了,谁能知道这病是当时最厌恶的流行流脑病,因没能及时治疗而夺走了年仅八岁,我们唯一的妹妹的生命。几年后,母亲因积劳成疾,思念妹妹悲伤过度,突发疾病离开了我们。
父亲以家庭付出为代价,和生产队里的领导成员一道,充分利用洮儿河水和肥沃黑土地的资源,带领社员们实现了既定的目标,建立鱼量子, 泥瓦盆窑, 成立了砖窑,栽培了一片苹果树,,买了一台东方红28拖拉机,实现了既定的目标,被公社评为劳动模范。
父亲走了,是带着遗憾和收获走的。
父亲的一生,是对家乡这片黑土地深沉的热爱和无私的奉献的一生。他用默默无闻的汗水和勤劳诠释着生命的真谛。他那苍劲有力的身影是岁月积淀出来的宝贵财富,是一首关于奉献和坚韧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