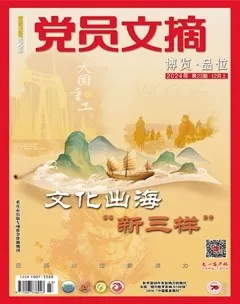为原子弹装上“心脏”的人
一张膜,不到0.05毫米的厚度,能有多重?如果它承载了一代人的心血、一辈子的坚持,或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又有多重?
2024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这张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重回20世纪50年代的核工业第八研究所,寻找那些被时光掩埋的秘密。
代号:真空阀门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沉寂已久的戈壁荒漠发出一声巨响,随后,欢呼声、掌声、广播声如决堤潮水般涌向全国各地。全国沸腾了,全世界也被震得摇晃。
但有一群人没有欢呼雀跃,只有心如鼓擂,因为他们的工作需要保密。他们的心跳,向来和原子弹研制事业的心跳同频,他们就是为原子弹装上“心脏”的人。
“没有铀235,原子弹就是天方夜谭,分离膜则是浓缩铀235的核心部件。”原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研究员柳襄怀说。
当时只有美国、苏联和英国掌握分离膜的制造技术。然而,苏联突然停止了对中国分离膜的供应,有人扬言,中国的浓缩铀工厂将成为一堆废铜烂铁。面对这样紧急又严峻的情况,党中央立即作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原子弹的“心脏”——甲种分离膜的研制和生产,各方面要为这项任务开绿灯。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曾言:“我们哪怕少活几年,也要把这个东西攻下来!”
1962年,60多名攻关人员在上海冶金研究所集结,成立了代号为“真空阀门”的第十研究室。夜以继日的艰苦探索和反复试验终于在1963年秋天有了结果,符合要求的分离膜元件试制成功!
上海材料金属加工厂
没时间缓一口气,更紧张的挑战随即而来。
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建立分离膜的专业试验厂,主要任务是中间性试验甲种分离膜,并研制确定工业化生产设备和工艺。最终,该厂取名为“上海材料金属加工厂”,厂址选在上海宝山,这就是核工业第八研究所前身。
原上海材料金属加工厂厂长张毅还记得他接到任务的那天,时任上海市“真空阀门”领导小组组长的许言把原上钢五厂党委副书记史久源和他约到办公室谈了一个下午。许言激动地说:“这件事要按中央的决心和市委的部署,我会用毕生的精力与你们一起投入这场新的战斗。”两人顿时觉得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了身上,办公室里只剩下喝水的声音。往回走的路上,张毅对史久源说:“看来我们俩这后半辈子都要放在这个事业上了。”
很快,宝山的一个废弃瓦砖厂就迎来了一群年轻人。这里只有一片荒草地、四个窑洞、两栋宿舍、一个车间、几间平房和唯一一条通向镇上的小路。此外,就是异常艰巨的使命。他们自己动手设计制造大量设备,解决了制粉、调浆等一系列工艺问题。

核工业第八研究所原所长陈绍廉就是其中的一员,那时候的他才25岁,被分到粉末组。“我觉得能干这份事业,很光荣,责任也很重大。”陈绍廉说,“金属粉末有毒有害,接触空气就燃烧,同志们做这项工作其实是面临着生命危险的,部分同志还中过毒。”实验人员全副武装,白大褂、手套、防毒面罩……一站就是一天,除了吃午饭,都不外出。
“856”的岁月
1964年2月,上海金属材料加工厂由宝山迁移到嘉定,新厂址代号“856”。
为了尽早成功,全厂一刻不敢停,边施工、边试制、边生产,终于在1964年5月成功生产出甲种分离膜,并马上装配到专用工厂。由于出色的性能,分离膜于1965年开始批量生产。这项成果在 1984年被授予国家发明奖一等奖,1985年又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边基建、边试制、边生产,在现在看来可能是不科学的,但是我们工作严谨细致,这样做赢得了时间并且没有造成返工浪费。”张毅回忆。
再紧迫,安全永远是他们心中一根绷紧的红线。谈到这里,曾担任过核工业第八研究所所长的梁明信想起一件小事,那时候厂外一带还是土马路,但是为了给分离膜的研制和生产提供防尘、清洁、安全的环境,工厂窗户不仅设计了双层玻璃,附近也全部改铺了柏油马路。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消息传到厂里时,由于生产还在进行,工作还需保密,大家只得悄悄庆祝。陈绍廉和梁明信回忆起工作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不约而同地提到研制分离膜就是中国举全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典型。他们其实早就笃定这一天一定会很快到来,“因为我们早就有一种信念,那就是干不成就一直干,直到干成为止”。
(摘自《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