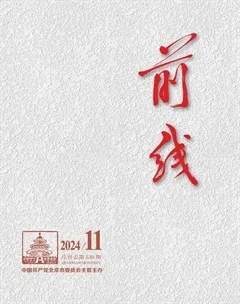关口连内外 要塞变通衢
在中国历史早期阶段,长城主要作为中原王朝的军事防御建筑工程而存在,长城各关口要塞在巩固边防、保卫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长城内外各民族的往来不断深入,长城军事防御功能逐渐弱化,其作为农业与游牧两种文明交流渗透、交融汇聚重要通道的功能日益增强,作为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融合纽带的功能也愈发凸显。与这一历史过程相对应,明清时期长城关口也经历了从军事要塞到贸易枢纽的转变。
明代长城关口商贸的发展
明朝建立初期,中央政府对蒙古各部颇为戒备,双方经济往来主要依托朝贡贸易。朝贡贸易主要是明蒙统治阶层间对奢侈品、马匹、土特产等少数种类商品的交换。在双方关系相对融洽的时期,明廷允许蒙古使臣中未被批准进入北京的朝贡者和随行商队在长城关口与汉人交易。据明政府规定,拱卫京师的居庸关是鞑靼与瓦剌朝贡所必经,喜峰口则是兀良哈入关的唯一通道。这些入贡必经的长城关口军镇的沿途贸易(或称贡道贸易)因之有所发展,但程度非常有限。在双方关系紧张、边境局势动荡时期,长城关口的互市贸易则极不稳定,“土木堡之变”“庚戌之变”等事件直接导致朝贡多次中断,古北口、居庸关等长城关口的沿途贸易也随之停闭。
明穆宗时期,明蒙关系迎来转机。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因内部矛盾,把汉那吉率部下十余人投明,而把汉那吉的祖父正是当时已经统一蒙古多部落的俺答汗。以此事件为契机,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俺答汗遣使与明朝达成隆庆和议。其后,明廷将长城沿线大同、宣府张家口、山西水泉营等部分长城关镇作为明蒙互市场所,每年定期开放。自此,长城地带迎来一段稳定和平的时期。
最初得到发展的是在明朝政府监控下,于前述指定地点进行贸易的官市。因为长城关口的互市贸易很好地满足了农牧业经济间的交换需求,前来贸易者日众,而官市开放频率低、交易物资种类数量限制严格,难以满足需求,所以很快出现了“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以弥补官市不足的民市,每月一次、在指定地点由各部牧民与边民、商人自行贸易的月市,以及在指定或商定的地点,月内多次开市的小市。最初以马、牛、羊等牲畜交换粮食的简单品类贸易,很快发展为以多种畜牧产品换取农耕地区各类生产生活资料与小商品的多品类贸易。
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等北京地区的长城关口虽然因为靠近京师、与京畿安全密切相关而未开放互市,但经此出关与蒙古人互市的内地商人却络绎不绝。居庸关通道北端的岔道城逐渐发展为南北商旅货物往来交汇的一个中转站,居庸关南口也设有抽分官向往来商货征税。据《万历会计录》载,该关每年商税额为二千五百两白银,闰年则增至三千余两。长城南北的经济交往不断深化,原本作为藩篱而修筑的长城,反而在客观上日益发挥着农耕与游牧物质文化交流通道的重要作用。
清代长城关口商贸的兴盛
明后期长城关口成为农业与游牧业经济贸易往来的枢纽后,不仅受到明廷和蒙古诸部的重视,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也同样将目光投向了这里。明末辽东发生严重灾荒,粮食、马匹等各类经济物资紧缺。为了摆脱困境,后金汗皇太极开始以归化城和张家口为中心,分两线积极向长城沿线拓展势力。这既是为了与蒙古诸部交易获得马匹,也是意图利用明蒙互市贸易,以蒙古部落为中介,从明朝获取粮食、布帛等物资,满足其社会经济物质需要,并增强军备力量。
明清鼎革,长城作为多民族文化、经济交往融合纽带的功能进一步增强。清朝初年,西北诸部局势未定,长城内外商民贸易往来、西北诸藩部入贡,都需要在长城关口查验票照凭证、稽核人员货物,长城关口继续成为这一时期的互市之所。顺治初年朝廷便派官驻古北口和张家口,“凡外藩贸易者”,要求驻防官“照常贸易,毋得阻抑”。康熙年间朝廷曾谕令理藩院,“厄鲁特部落,如噶尔丹等四大台吉,应令来京互市”。乾隆时期,清廷基本完成了对蒙古诸部的统一,长城内外商业贸易更加活跃,沿线也开辟了更多市场。
由于京师汇集四方商旅,具有消费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因此在蒙古各部前来互市的同时,北京许多商号也开始向库伦、乌里雅苏台等地贩运商货。卫戍京师的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等,以及北京通往西北、东北要道上的张家口、杀虎口、山海关等,作为各类贸易开展的通道,纷纷从军事重镇转变为互市市场,其中许多还成为清朝的重要税关。康熙年间居庸关就设立了税口。古北口虽然未立税关,但一直设役巡查往来商民和载货车辆。乾隆年间,从关外进口的木植多由潮河运输,古北口为必经之路,故政府规定在密云县对从古北口进口的木植征税。道光年间规定,古北口南部的穆家峪设税局,专门对从古北口贩运入关的各类物资进行收税并发给照票,由此继续进京贩卖的商人可以凭照票在之后的税卡免税。
清代长城关口还成为中俄贸易的枢纽。中俄之间早有零星贸易往来,但数量有限且缺乏监管,多有偷税漏税走私的情况。随着双方一系列条约、市约的签订,中俄贸易得到官方承认并逐步规范,双方约定在尼布楚、恰克图、祖鲁海图通商,其中恰克图很快发展为中俄大宗贸易的中心。嘉道以来,众多北京商号和活跃的晋商纷纷前往恰克图进行贸易,而俄国商团也源源不断来到北京进行皮毛、呢绒等商品贸易,沿途长城关口因之成为中俄贸易通道上的重要枢纽。清人记载居庸关关沟“为南北冲途,蒙部之朝贡,台站之转运,俄商之贩茶,皆取道于此往来”“茶市以张家口为枢纽,货物辐辏,商贾云集”。由此,长城关口不仅在国内民族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将商道延伸至欧亚大陆。
明清长城关口商贸的管理
与明清不同阶段长城关口及其商贸活动的功能、性质、特点等相呼应,政府对长城关口的管理也不断调适改变。明代长城沿边互市由明朝政府主导,互市场所均依托于长城沿线的重要军事营堡,市场空间、人员进出管理等方面带有很强的军事防御色彩。
明代对沿边互市的管理以镇为单位,市场由守边将领负责管理,市场指挥多以各镇巡抚或总兵兼任。为防备蒙古军队借互市攻占关城营堡、入边抢掠,官市通常与关城保持一定距离,市场旁边多建有瞭望墩台和护城壕,市场则以高墙封闭。护送商队的蒙古军队被禁止进入市场,市场内由明军全权负责维持治安秩序,市场周边也会布置更多明军,以备随时调遣。
清朝对长城关口的管理亦经历了由紧到松,从以军事为重点到以商业为中心的转变。清初,中央政府对长城以西、以北的蒙古诸部仍颇为戒备,中央特派勋戚重臣,统禁旅数千,驻扎杀虎口等地。靠近京师的古北口与张家口专设满洲章京驻防,以便管理前来互市贸易的外藩蒙古。随着清廷与绝大部分蒙古部落统属关系确立,长城关口互市常态化,清廷对各类货物在长城关口镇市的贸易时间进行了规定,并通过部票、印票等凭证控制蒙地出入人数和交易往来物品的种类数量。清中期以来,长城内外贸易日增,长城关口管理模式从军镇向税关转变。居庸关另设税课大使以监督税收,康熙年间规定其税额为每年白银三千两,居庸关北作为军事藩篱的岔道城也从军镇转为民村。古北口百余年来人民安居乐业,关城市肆商贸日益繁盛,有“工商万室辏鄽阛”之景。为了不阻滞商民货物往来,长城关口的稽查政策进一步放松。《清高宗实录》记载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北京东北方向上的柳条边西段“自法库门起至明水塘十边地方”,商贩出入需按惯例由地方发给印票,长城关口官兵验票通过后放行。然而,这一线作为北京地区与广大东北地区联系的交通孔道,清河门、九官台等边地“进口车辆,盈千累万”,时任山海关监督的高诚认为,如果一一验票,势必“行旅壅滞,内地商贩,亦必畏难不前”,而且官兵稽查虽可避免偷税漏税、走私等情况,但也会出现稽查者借机滋扰商旅的弊病。因此,在他的奏请下,乾隆帝同意免除这些地方对载货往来商贩的验票,只令官军认真督察巡防。
综观明清,长城关口商贸在功能、性质、形态、规模、政府管理方式等方面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是明清政权与长城以北各少数民族关系的历史映射。长城关口商贸活动的发展繁荣是人民之需、历史之需,在推动长城内外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提高长城内外各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长城关口从军事要塞到商贸枢纽的转变和发展繁荣,生动地体现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积极互动,汉蒙满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
(本文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青年课题“明清长城关口商贸与北京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袁钰莹,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