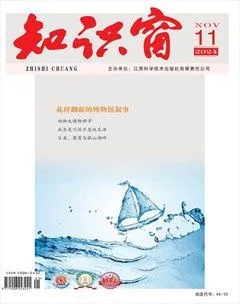父亲、莺莺与微山湖畔
我自幼随父亲寓居微山湖畔,几间仓库改成的矮破木屋,两艘飘摇的小船,再加一袭旖旎湖光,便构成我童年记忆的全部。
父亲时常披着夜色撑船去检查地笼,提前烧一壶开水,烙两块饼子充当早饭。他总是蒸上两颗鸡蛋,临走前悄悄放在我的枕边,蛋壳上的温度直烘得我的脸颊烫乎乎。五六点钟天蒙蒙亮时,我醒了,鸡蛋也刚好晾凉了。
父亲总能控制好时间,他携地笼里收来的新鲜虾蟹,去与鱼贩接头,再撑船返回小木屋。睡眼惺忪的我一开门,便被挂着露珠的红荷与莲蓬塞个满怀。
微山湖万亩荷塘,野生的红荷生命力顽强,往泊子里随便一丢,它也能长出来。隔壁邻居家有只小羊,顶稀罕啃这红荷的花瓣,而我顶稀罕那只小羊,父亲便每天为我砍红荷带回来,给我去哄那只小羊。父亲说,他小时候也爱寻这些稀奇古怪的花果喂牛羊。
我替小羊取名莺莺,因它的叫声跟湖畔一种名为莺的雀儿相似。在莺鹭成群的草甸里,不大好分清是谁家鸟鸣,有时鸟妈妈们也都被莺莺的叫声迷惑。
有一阵子,村邻们打趣父亲纵容我这个“小兔崽子”糟蹋那些红荷。父亲面露窘态,似是勾起了自己顽劣的童年回忆,便不再为我带回红荷。眼见莺莺没了零食,我另寻他法,央求父亲到湖里割苲草时捎上我,再趁他不备,悄悄将莺莺掳到小船上。
父亲坐在船头磨拖刀,磨到锃亮时将它抛进水底,小船动起来,拖刀就晃晃悠悠开始工作,嫩绿的苲草飘摇着浮上水面。在荒年里,人们舍不得给螃蟹喂玉米,苲草便是最鲜美的饲料。只可惜我的莺莺不吃这个,它只爱娇艳欲滴的花瓣。当小船摇到近处时,莺莺就开始享用自助餐,所过之处,徒留一片光秃秃的莲秆儿。
莺莺啃花瓣,我便扒莲蓬,我俩分工协作,都十分繁忙。莲子被吞进肚里,莲芯儿则晒了泡茶,一趟下来,“小兔崽子”和小羊羔子都肚儿浑圆,父亲看了笑得直摇头。如此几番来回,溽暑便也接近了尾声。
当禾黍卷轻霜之时,旱季随之来临,泊子里耗水越来越快,我没法再带莺莺上船了,只能眼巴巴看着满湖的红荷自然凋零,莲蓬与荷叶都由青转黄,最终在视线里枯萎。我时常蹲在月色下,遥望那些孤零零的莲秆儿,莺莺挤在我的腿边,也发出辛酸的哼哼声。
熬过了大雪漫天的寒冬,我仍是个小孩儿,莺莺却已是成年羊了。我心想,它的童年可真短暂,对红荷花瓣也爱得不够深沉。
父亲去湖里割苲草时仍带上我,可长大了的莺莺不好掳上船了,我只得坐在船头自娱自乐,父亲便开始拿苲草种子哄我。苲草种子约巴掌宽,绿茸茸的,屁股后面还有根一米多长的尾巴。尾巴像是烫了大波浪卷儿,在我的眼前一弹一弹,我立马就被吸引住了。父亲还带我去泊子里看那些红荷,莲子萌发得不好,他又买了许多藕栽进湖里。经过几十日疯长,水面上露出了密密麻麻的嫩尖儿。
我向父亲说起,莺莺长大了,不再喜爱花瓣了,父亲也跟着神色黯淡下来。我俩都为泊子里的新生而高兴,却又对莺莺已逝的童年万分怀念。
后来,我因读书离开了微山,留父亲一人守着青绿湖面和两艘小船。父亲时常打电话给我,聊起小羊一批接着一批出栏,也时不时会有只小羊像莺莺那样爱啃红荷花瓣,莲蓬、莲藕结了一茬又一茬,泊子里一派生机盎然,还有小渔村的变化、村邻们越来越红火的生活……聊到兴头上,我们对着一方窄窄的手机屏幕大笑。恍惚间,我俩都回到了那蛙声乍起、花开沸沸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