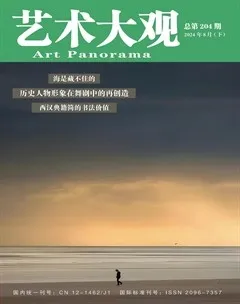蒙古族英雄史诗的传唱者:江格尔齐的技艺要素
摘 要:《江格尔》是蒙古族英雄史诗的代表,也是蒙古族文化宝库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以口头传唱的形式流传于蒙古族民间,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本文从《江格尔》史诗的传唱者江格尔齐入手,通过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总结了江格尔齐所具备的三个代表性的技艺能力要素,并讨论了在《江格尔》史诗艺术发展中江格尔齐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江格尔齐;《江格尔》;技艺要素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357(2024)24-00-03
《江格尔》是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杰出代表,这部史诗讲述了英雄江格尔及其勇士们在宝木巴地方与邪恶势力斗争的故事。史诗中不仅展现了蒙古族的英雄主义精神,还融入了蒙古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自然环境等元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它以口头传唱的形式流传于蒙古族民间,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部史诗不仅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和信仰,还体现了蒙古族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能够流利演唱并传承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艺人也被称为江格尔齐。作为史诗的传承者,江格尔齐肩负着将这部古老史诗代代相传的使命,是蒙古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江格尔齐的分类与内部辨析
(一)江格尔齐的分类
常见的《江格尔》说唱表演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无曲调,以叙述表演为主的表演形式,另一种是有固定曲调,以说唱表演为主并常伴有乐器伴奏的表演形式。因此,按照江格尔齐的演唱形式作为区别,一般将江格尔齐分为吟诵类和曲调说唱类两大类。目前常见的江格尔齐都为后者,本文主要讨论的对象也为曲调说唱类的江格尔齐。
(二)江格尔齐的内部辨析
江格尔齐作为《江格尔》的传播主体兼具人与传播媒介双重属性,“齐”也是对说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的尊重[1],因此并非所有能够演唱《江格尔》的人都能被称为江格尔齐。
加·巴图那生在调查报告中表示,只能讲五个章回以下《〈江格尔〉传》的人不被人们认为是“江格尔齐”[2],同样的,仁钦道尔吉在其专著《〈江格尔〉论》中也有相同的观点:“由于过去新疆的江格尔齐很多,因而仅会演唱三五部的人就不被当作江格尔齐;只有懂得许多部,而且演唱技巧高超的人才会被人们称为‘江格尔齐’”[3]。例如,和丰的朱乃能讲26部《江格尔》,同为和丰的冉皮勒会唱21部,乌苏县的洪古尔能演唱10部,这些都是新疆著名的江格尔齐。
但由于老的江格尔齐相继去世,加之《江格尔》表演活动减少,江格尔齐在20世纪末数量骤减,于是仁钦道尔吉在研究中将能演唱完整的一到两部《江格尔》的艺人称作江格尔齐[3]。
笔者通过对当今江格尔齐的访谈调查发现,以演唱篇章数量来判定艺人是否为江格尔齐的标准,在江格尔齐的内部认同中得到的结论是不尽相同的。被访谈江格尔齐有的认为一名合格的江格尔齐需能完整表演三四部《江格尔》,也有的认为《江格尔》的学习难度较大,至少需要能够完整表演一部《江格尔》的章节。如和静县的满都来能够演唱20部《江格尔》,焉耆县的巴音孟克可演唱4章,博湖县的岱日曼能够演唱3章。
由此看来,对江格尔齐的界定,在江格尔齐的内部认同中,演唱的篇章数量尚未得到一致判断,尤其是在当今《江格尔》说唱艺术受到空前重视,学习《江格尔》说唱的人数逐渐庞大,对于江格尔齐的内部认同却变得清晰,并不是所有能表演《江格尔》的艺人都能被称为江格尔齐,笔者结合对多名江格尔齐的访谈总结为:一名江格尔齐除能完整演唱《江格尔》章节外,还需具备多样的表演能力,换句话来讲,除了系统地学习完整的《江格尔》篇章,还需要具备技艺要素。
二、江格尔齐技艺要素
(一)记忆能力
史诗艺术作为口头文学艺术,口传心授是其最主要的学习模式,被采访过的几位艺人均有青少年时就学习过《江格尔》的经历,并且在当时就发现了自身远超常人的记忆力。
仁钦道尔吉通过句法结构分析模型得出《江格尔》史诗具有并列复合型结构特征,即《江格尔》各篇章节之间没有故事情节上的连贯性,各个篇章在结构上具有完整独立的特征[4]。因此由许多独立的章节组成,每个章节都可以独立成篇,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宏伟的史诗体系。《江格尔》的演唱就是以篇章为单位进行表演的,一个独立完整的章节包含了该章节的《〈江格尔〉赞》和随之其后的《讲〈江格尔〉》正文,一场完整表演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四个小时以上,如此大篇幅唱词文本,需要江格尔齐强大的记忆能力。
那么,《江格尔》的文本内容有无记忆技巧呢?研究《江格尔》史诗文本可以发现,《江格尔》的文本具有固定的程式化词汇和语句。例如,“英明盖世的诺言江格尔”“残暴的希拉·莽古斯可汗”“铁臂的萨布尔”等[5]。这些固定短语或语句不仅点出了被修饰者(名词,人或物)的某些特点、属性和品类,还渲染和修饰了史诗凝重、宏伟和肃穆的诗品特征,使得表演者可通过程式化的语汇来辅助记忆。
可见,江格尔齐能够记忆长篇史诗内容,这种记忆力不仅涵盖了史诗的情节、人物、事件,同时他们能够长期保持这些记忆,即使经过多年,也能准确无误地复述史诗的内容。这种强大的记忆力还兼具了长久的稳定性,这是江格尔齐最为显著的能力特点之一。
(二)唱奏能力
除了少部分吟诵类江格尔齐外,大部分江格尔齐都是以说唱形式表演《江格尔》,可见《江格尔》的音乐表达也是江格尔齐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同焉耆县江格尔齐巴音孟克的访谈中,他给出了一个很经典的学习范本:第一个阶段是先学唱《〈江格尔〉赞》,第二个阶段为故事情节的背诵,以《洪古尔迎战莽古斯》这一章节为例,故事情节大致分为人物介绍环节、展开战斗环节和胜利归来环节三个部分,能够将故事情节记牢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将故事用说唱的形式演唱出来。用他的原话说是:“故事背下来后要‘变’,这个和说的话不一样,这个是艺术,得配着音乐讲述出来。”可见,除了记忆史诗文本,史诗唱词转化同样需要江格尔齐高超的演唱能力和依据行文韵律改编唱词的编创能力。在这个模式中,学习《江格尔》是由文本过渡到说唱的转化,音乐的关照同史诗文本的韵律和程式是相辅相成的。
另外,具有说唱表演能力的江格尔齐通常都配有乐器伴奏,乐器多为新疆蒙古族传统乐器托布秀尔。托布秀尔为主要流传在新疆蒙古族的弹拨类乐器,音色清脆、悠扬,两根弦,常由一个扁平的共鸣音箱和一根较长的琴颈组成,共鸣箱有个小孔,方便声音的传播,同时扁箱长柄的设计便于演奏者进行各种演奏技巧的展示,同时也便于携带。
过去,许多著名的江格尔齐都能弹奏托布秀尔演唱《江格尔》,如博尔塔拉的宾拜、道尔巴,和布克赛尔的阿乃·尼开、额尔赫太、加甫,尼勒克县的达瓦等。但随着《江格尔》说唱的落寞,加之诸多江格尔齐相继去世,在贾木扎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报告中记录了现在除了朱乃、巴桑—哈尔、普尔布加甫等江格尔齐外很少有人会弹着乐器演唱《江格尔》[6]。观之当今的《江格尔》学习者多数都延续了表演《江格尔》时演奏托布秀尔伴唱的特征。巴音孟克的原话为:“江格尔说也可以呢,厉害的就能唱,再劳道①的就可以弹着托布秀尔唱了。”同时在访谈中他还为我们介绍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以前的国家级传承人满都拉老师,托布秀尔弹一个地方,唱一个地方,不配合,(托布秀尔和《江格尔》演唱)合不到一块去,后面好不容易才学会了,能在一起了。”综上可见,托布秀尔和《江格尔》的演唱是高度绑定的,并在表演环境中不断去熟练和打磨技艺。
(三)综合表演能力
《江格尔》史诗说唱因其史诗文本的庞大,演唱一部完整的章节时间较长,因此在《江格尔》的演唱中有很多需遵守的传统,如表演时必须在夜晚,以表示对英雄的赞颂和尊重,还有《江格尔》的表演不能随意终止,表演者要完整地唱完一部方可结束。仁钦道尔吉对此解释:“演唱一部长诗,就得完整地演唱,不能随意终止,听众要坚持听到演唱结束,不能随意离开等。违反了这些规则,会被认为是罪过,会遭受灾难。[4]”但现如今,听众快节奏的审美已不再适应《江格尔》长篇的表演节奏,再加之现如今的表演场域已经从庙会和祭祀场所变更到了诸如艺术节、文化展和比赛的舞台场域,对《江格尔》的表演时间和空间进行了进一步的压缩。这样的表演环境,江格尔齐的表演能力也有了相同的适应性。
从表演内容选择上,表演者在有时间限制的表演中通常会选择《〈江格尔〉赞》,问及什么是“江格尔赞”,巴音孟克回答:“‘江格尔赞’是一个段落,少得很,‘江格尔赞’紧接着江格尔的故事篇章,已经是缩减完了的了,把简单的部分都拿到前面来了。”我们把《江格尔赞》通常理解为相对应《江格尔》篇章故事情节中人物、景物和情节的赞颂,是《江格尔》篇章中的高度概括,也是学习《江格尔》的基础。接着巴音孟克又说:“《江格尔》可以缩短,如说马怎么样跑的这一段,这个样子跑,那个样子跑的就不说了,直接说骑马跑过去就行了。”这是对史诗文本情节中对人物形象、事物特征的具体描述的缩减,相反,史诗的内容文本也可以增加上述的描述来扩充表演的内容。在江格尔齐岱日曼的访谈中也有此类表演技巧的表述:“《江格尔》唱骆驼的时候,毛、腿、鼻子、嘴巴、眼睛、耳朵、尾巴都是可以描述的。”由此可见,能力强的江格尔齐可以通过增加或删减史诗人物或事物的具体描述内容来达到控制表演时间。
此外,在表演过程中,因表演环境和高压以及长时间的演唱难免有唱错情节或忘词的情况,据巴音孟克回忆:“以前在蒙古包里,江格尔齐很放松,中间断了喝杯茶就想起来了。”可见表演环境对《江格尔》的表演也至为重要。笔者观看《江格尔》的比赛时发现,舞台上的表演者因忘词被迫停止表演的现象也屡见不鲜。面对这样的情况,艺人也有应对的策略:“有一次我在和丰比赛,要唱20分钟的江格尔,中间我忘掉了,我会用托布秀尔代替旋律,在这个空当回忆,如果想不起来,就把这一段节再唱一遍,将其顺下来,只要我保持连贯,对江格尔不熟悉的人是听不出来的。”可见,成熟的江格尔齐拥有较强的抗压能力,以及在表演中能够运用同观众的互动因素或自身对表演内容的重复运用来巧妙化解演出的失误,当然这也离不开此部分江格尔齐熟练的技巧和丰富的表演经验。
以上是笔者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对江格尔齐艺术能力的总结,这些记忆要素共同构成了江格尔齐的艺术特质,使他们能够在蒙古族史诗文化中扮演重要的传播角色,并确保《江格尔》史诗得以世代相传。
三、江格尔齐之于《江格尔》艺术的重要意义
(一)文化传承与创新
《江格尔》艺术虽经低迷,但从未断绝,蒙古族的英雄史诗也在一代又一代江格尔齐的传唱中得以延续。《江格尔》说唱艺术不仅是艺术表现,更是文化记忆的传递,对于保持蒙古族的文化特色和民族认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传承的基础上,江格尔齐不断进行艺术创新,使得《江格尔》史诗的内容和形式得以丰富和发展。《江格尔》因其口头史诗的文本特点,江格尔齐在说唱表演中也不拘泥于固化的唱词和旋律,并在表演中持续再度创作,使《江格尔》说唱艺术呈现了江格尔齐的个人创作风格和特点[7],这也是《江格尔》说唱艺术独具魅力且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江格尔》的表演实践过程是在吸收、学习并创新,实质上属同步发生、同步实践和同步运行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英雄史诗包含的丰富道德观念、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在江格尔齐的演唱过程中被民众所接纳,并产生了深远的教育意义,传递了正义、勇敢、忠诚等价值观。而《江格尔》史诗中的人物和故事往往成为蒙古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象征,在江格尔齐的演唱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共同体意识。
(二)学术价值与意义
《江格尔》作为蒙古族历史悠久的口头文学,包含了历史、文化、语言、民俗等领域的宝贵资料,对于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江格尔》史诗是蒙古族早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珍贵的史学价值,对于研究蒙古族远古时期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若是将《江格尔》比作蒙古族历史文化的宝库,那么江格尔齐就是手握宝库钥匙的守护者。丰富的文化历史在江格尔齐的口口相传中得以延续,江格尔齐在《江格尔》的学术研究中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下,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江格尔》的研究已发展成专门学科,逐渐形成了国际性的“江格尔学”[8]。
四、结束语
在现代社会,江格尔齐已成为蒙古族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不仅在国内各地展示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强化了各地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同时《江格尔》也逐渐走出国门,通过江格尔齐的传唱向世界介绍这一独特的史诗艺术,增进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蒙古族文化的了解,展现着我们的艺术精神和文化自信,《江格尔》的史诗故事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参考文献:
[1]道·道图那.《江格尔》在新疆的传播与传承研究[D].西北大学,2022.
[2]加·巴图那生,王清.《江格尔传》在和布克赛尔流传情况调查[J].民族文学研究,1984(01):42-54.
[3]仁钦道尔吉.江格尔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
[4]仁钦道尔吉.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N].中国民族报,2004-03-05(010).
[5]朝金戈.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6]特·贾木查.王清,乔伦夫,译.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传》调查报告[R].新疆民族文学,1982.
[7]哈斯巴特尔.英雄史诗音乐的风格构成与结构程式——以史诗《江格尔》五首曲调为例[J].中国音乐,2022(03):118-124+185.
[8]郝苏民.中国江格尔学的建立:认识与实践[J].西域研究,1992(03):1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