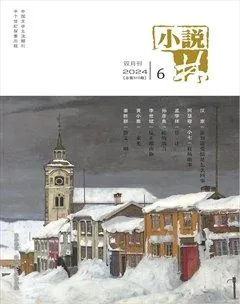寂静和它的美学回声(评论)
展卷一气读完小七的作品,颇有涤我尘襟、净化灵魂的感觉。因工作关系,八月份到过小七的“解忧牧场”,已然多了较深对其人其文的印象。在绿荫环绕的院子里品尝各种果蔬,聆听叫不上名字的鸟类鸣唱,兴致勃勃地观赏小七四处搜集来的少数民族牧民旧年物件。一桩桩往事听后,有人忘忧而哼唱,有人唏嘘而击掌。《小说林》要刊用她的作品,嘱我作论,还未动手呢,近期又与小七一道参加了一个读书活动,借助知人论世、知人熟文的加持,画中山川与真实山川迅速映入脑中,遂能成文。
陈毅有诗《幽兰》云:“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求逐“幽兰”者多仰望远方,习惯高喊“诗意在远方”而贬损当下,但远方也未必有诗意,正如李白、杜甫醒来依然不能为当代病症开出一剂药方。灵山不必远方求,小七更注重于当下生活里寄托身心,她的笔下从不故作恬适,也不特意展现西域之美。借物写心而形诸笔端,这恰恰是小七作品的精魂。让遣词造句听凭内心的需要,在文字行走之间叩问历史的回声、复现当代的脉跳,小七的创作是深思熟虑的,其创作自觉如黄侃《讲疏》所注:“夫极貌写物,有赖于深思;穷力追新,亦资于博学。将欲排除肤语,洗荡庸者,于此假途,庶无迷路……不悟规摹古调,必须振以新词。”多年来,她拒绝在作品中走“傻白甜”的温情路线,绝不复刻“你好我好他好大家都挺好”的单一歌颂腔调。她以“有赖于深思,亦资于博学”作为“极貌写物,穷力追新”的必要条件,融韵味、意境、情趣于一体,竭力传达出“我”的声音。强调“我”在自然中的观察,标举我之为我的体验与感受,小七的作品就是生命美学的铺展。
看山如玩册页,游水如展手卷,小七早已拥有云心月性,故而文字中汩汩而出的是自然之美。艺术家罗丹认为“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他号召艺术家“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小七倾心低首大地、端详自然的十六年,是她搜寻美、发掘美乃至塑造美的岁月累积。当小七观看自然时,阿勒泰青山秀水时刻追随她,美景胜境让她觉得“物上心来”,心间全是美的涌动;而当她清理杂物、栽花种草、修建鸟舍时,因心中葆有无限之美,以主观而艺术地改造客观,事物都焕发了本性,心与物和谐的“心到物边”因之而生。
发现原始的野性美、原生态的纯美,对于作家来说是初步的观察,极易做到,又非常重要。毕竟古人抬抬眼动动手就能做到,而在庞杂多变的现代背景下,作家不能纯然地简单描摹它,更要树立全新的生态文学观。赞颂自然并不是要人类退场,克服以人类为中心的惯性,恢复人与动植物的关系,才是小七作品要重塑的重点所在。《牧场趣事》里的花草、蔬菜、羊驼都有着平等的对话关系,唯有足够耐心、心藏慈悲的人,方能做到与万物笙磬同音。世界的巨憝元凶,是以高频快闪为代表的现代性后果。有了足够的耐心,小七的文字就可以远离喧嚣,生出一种不疾不徐的静气。心静下来才会入定,寂静才生智慧,进而可扫“客尘烦恼”。换言之,《牧场趣事》就是小七创制的寂静和它的美学回声。
遇见知己,说起生活的艰辛与坎坷,小七悲从中来、不能自克,忍不住落泪。光阴似箭,专职劳作(写作)忽忽十六年,她与俗世的战斗像是无声的精神斗争,何尝有一刻停息过?沉痛之人,内心必有痛彻心扉处。而一旦拿起笔来,她就像变了一个人。在牛粪堆下挖掘马绊子、在路上拖拽马槽子、网红羊驼四处惹祸撒欢,三个短场景的复述,充满了令人解颐的谐趣、使人惊艳的奇趣和发人深省的理趣。小七标举的“趣”,首先是生机,是一位接近遗世独立的作家在讲述世界的无限生机,这源自作家内心对世界的无限热爱。只有胸中不断奔涌热爱的人,笔端才可能洋溢着风趣、幽默。照实描摹自然与生活,一般作家动笔亦能做到,但“能谐所以能在丑中见处美,在失意中见处安慰,在哀怨中见处欢欣(见朱光潜《诗论》)”,当是一块试金石,决定着作家是否优秀。尽管小七话语不多且声音不高,但其作品洋洋盈耳的是西部人特有的幽默,类似阿凡提式的自嘲式幽默。从最平常的事物身上发现新鲜的诗意,找到抚慰生命的光亮,小七注重打造文字表达中的“谐趣”,试图为苦难孤寂的生活寻求“缓释剂”,拿来轻松紧张心境和解脱悲哀于困难。孤寂如铁,夜夜如年,小七爱世之情如丝似海,任风华自布的机趣绎之不尽……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但不怨恨世界,小七践行着鲁迅“减除恶草,浇灌佳花”的教诲,不断诉说着本真的心理需求。
“或者帮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使它重返它的巢穴/我便不枉虚度年华。”狄金森的名诗《如果我能让一颗心免于破碎》确证了心思坚定的诗人对残忍世界要温柔以待的决心。小七无疑也有这样的心思,以文字对抗喧嚣、远离绝境。小七作品总在彰显对抗外物的意图,在解忧牧场劳作思索,希望自己能够“丧己于物,失性于俗”。以文为经、以理作纬,小七遵循文质均衡的文艺观,既选择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照着讲”,又以生态主义的理念“接着讲”,避免“积微成损,积损成衰”,为自己也为他人寻找生命快乐的答案。作为意义世界一切实践活动的主体,文学是在用普遍价值提升人生意义的关切。如此,作家才能将“牢骚”变为“离骚”,写作的意义因此不彰自明。
张继千年前写就的《枫桥夜泊》余音不绝,那夜半敲响寒山寺的钟声深入每一个灵府,成为一种召唤我们放下内心执着、解脱苦痛的清音。阅读完毕《牧场趣事》,我觉得小七正在将人们于世俗中的热望,点化为一种类似寒山寺钟声的清凉。
作者简介:姜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26届学员,黑龙江省作协创研室主任。在《诗刊》《当代文坛》《文艺报》《作家》《电影评介》《名作欣赏》《星星》等报刊发表诗作、学术论文400余篇,著有文艺理论集《用一根针挖一口井》、诗集《借来的星光》《时光书》,曾获黑龙江省政府文艺奖(文艺评论)、第十届诗歌春晚十佳评论家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