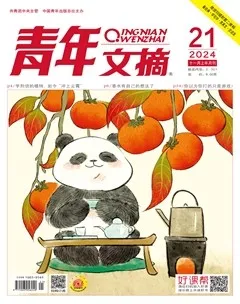15粒来到且末的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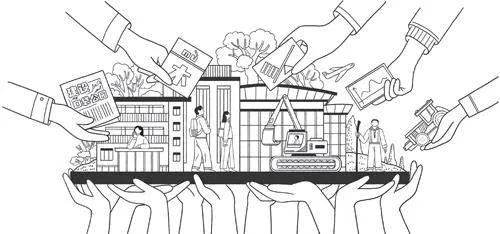
为看沙漠与胡杨而来
“在我们且末,你可以看到沙漠温柔的落日,是粉橙色的,看到胡杨,是金黄色的。月工资能有600多元,比留在河北教书多两倍。”
2000年,且末中学的校长段军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走出来,向河北保定师专的毕业生们描绘且末对人才的渴求。他很焦急,初一年级7个班,班主任只有1个,各学科都缺人。
应聘面试是以“沙漠的标准”来衡量的。且末县深埋于中国最大的沙漠与昆仑山脉之间,扎根沙漠,老师必须和当地植物梭梭一样,有坚韧、“耐旱碱”的品格。校长偏向招聘多子女家庭的农村孩子,知道他们能吃苦,也有兄弟姐妹可分担家中的养老任务。为了让会打拳的体育系女生王建超安心,另一名招聘的体育老师换成了她的男友王伟江。
这些年轻教师坦言,鼓动他们去应聘的,是初出茅庐的勇气和对世界的好奇。1999年起,国家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颇有侠气的王建超在电视上看过宣传片,她想:在新疆看不到头的油菜花海打个滚,一定很美。也有的老师是为了替病弱父亲还债,决定“往高工资的地方走”。
2000年8月6日,火车把15个年轻人带出了太行山,走了3天才到达库尔勒,接着,换汽车,又在沙漠里走了2天。沙丘绵延不断,车子“像一叶扁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
第5天黄昏,且末的绿意涌入眼帘。欢迎他们的初一新生,带着害羞与懵懂在校门口等待,每人手上拿着一只脸盆,为了泼水压住操场上的沙尘。老师的宿舍经过突击粉刷,被褥用品一应俱全。但王建超没有见到校长承诺的塑胶操场,段军拿出设计图纸安慰她:“莫急,马上就要建了。”
2001年秋天,新的教学楼竣工,师生们搬进了有暖气、饮水机和电脑教室的楼里。但直到2017年,王建超心心念念的塑胶操场才建成。
教“普通学生”的幸福
听说且末的冬天经常断电,蔬菜也很难买到。上班没多久,新老师就备了蜡烛,买了辣椒、茄子和豇豆,煮熟后晾在房顶上,准备过冬吃。没想到,沙漠的狂风说到就到,精心准备的蔬菜一夜间被大风吹得精光。沙尘叩打门牙,无论你怎么包紧头巾、紧闭口鼻,口腔里也有一股“微微发麻的砂砾味”。
等新鲜劲儿过了,教育的艰难才呈现出来。这里的孩子基础薄弱,到了中学,一些学生连拼音还没完全掌握。他们相当顽皮:课堂上说话的,扔纸条的,不交作业的,理直气壮说“我笨,我不会”的,应有尽有。但孩子们本性善良,上着课,一个男孩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一团黑皱的卫生纸,对着侯朝茹说:“老师你流鼻血了。你擦一擦。”
这些来自内地的新老师用了24年,去探索怎样栽培且末的学生。所有的教师都要给字词注音,从教孩子们读题目开始……历史老师这样做,数学老师也这样做。
这批老师带出的第一届学生,中考排名在全州靠前,维吾尔族家长都学会了“老师”的汉语发音,见了老师就施礼。
2019年,且末中学的高中部迁入新校址,独立为且末一中。这批老师后来陆续进入高中部教学。新校园已经有投影仪,随时可以上网,但孩子们认知的盲区,依旧需要老师苦口婆心地扫除,考题里的“共享单车”“口袋公园”“民宿”……究竟是什么东西,庞胜利不得不把报纸上的新闻图片剪下来给学生看。
孩子们上北大的也有,去香港的也有。但老师们不得不思考:考出去的优秀学生不一定再回来,他们的主要任务,恐怕是“培养建设且末的普通劳动者”。教育理念的转变,使教育的视野为之一宽。在这里,成绩不好的学生也可以当课代表。丁建新要求学生识得科学原理,未来种地、放牧,也能够理解和适应农业机械化。侯朝茹的学生殷勇志,开着挖掘机参与了且末火车站、新机场的修建。
令老师们欣慰的是,20多年过去,这里超市的收银员、菜场老板、交警、医生、财政局和气象局的公务员……都是他们教过的学生。这就是教“普通学生”的幸福——“环绕在身边的,都是敬重你的熟人”。
教育的效果,或许要等到10年、20年以后才能显现。有人用“15粒来到且末的种子”来比喻他们的扎根奉献。20多年过去了,他们谁也没有离开。
爱、友谊与默契
“为什么没有走?”这些老师提到了爱、友谊与默契。这种默契包括:几乎每个人都动过离开的念头,但谁也没有告诉过对方。
15个人,全是老乡,周末骑着自行车去爬沙漠,找个最高的沙丘,仰面躺下,彼此聊学生的发展,教学的志向,也叹息在广袤的沙漠里,每个人都如“沧海一粟”。没有浮尘的时候,沙丘的夜晚能看到透亮的星星,此时,一些微妙的情愫,也在这些年轻人心中浮现。庞胜利攒了几个月工资,买了一台胶片相机,拍下侯朝茹的笑脸与在沙丘上挥动丝巾的身影,他们恋爱了。2002年,庞胜利与侯朝茹领证结婚。在他们之前结婚的还有王建超和王伟江。从保定先后到且末的二十几位老师里,“成了7对”。
除了爱情,友谊也在延展。且末县在21世纪初没有血库,为防万一,王建超临产时,同是A型血的辛忠起陪着王伟江在医院走廊里候了一夜。
沙漠筛选了一群人,又通过24年的隔绝,把这些简单的心志保留至今。辛忠起说,他与同事到现在都是理想主义者:如大山一样脾气刚直,舍得奉献,“择一条路走,不试其他”。这种笨拙,却也在人生路上少很多纠结与彷徨。
因为回家的路过于漫长,这些年他们有个传统,一人回家探亲,要去看看其他同事的父母。丁建新就是这样发现庞胜利家的老屋失修的。寒假结束时,他回来提醒庞胜利,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县城给老人买一套房?庞胜利立即计划起来,“老丁给我拿了10万元,同事们慷慨解囊,凑了40多万元”。庞胜利父母得以离开危房,住进了有暖气、独立厨卫的新房。
庞胜利全家都很感动。每次探亲离家前,父亲总要给庞胜利写点字,让他带上。“替祖国争光,为人民服务。”庞胜利跟老爸开玩笑:“您写的像领导题词。”
2019年,庞父因病离世。庞胜利一直珍藏着他参加工作后父亲的第一封回信。父亲写道:“以后不要提‘不孝’二字,你这是到了祖国需要你的地方。望你不要想家,不要凄凉,那里有你同去的同学。你要努力工作……为建设新疆美好将来,栽上万朵鲜花。”
自古忠孝难两全,人到中年,送别父母离世,是他们近几年的隐痛。今年年初,辛忠起昼夜不停地开车,终于赶上给父亲送了终。10年前,由于工作繁重,辛忠起免疫功能下降,患上了一种叫“毛发红糠疹”的皮肤病,“像一层糨糊刷在身上又干了”。亲友劝他到湿润的地方去生活,在南方旅行时,他确实感觉身上的“盔甲”软和了很多。但他坚称,这不是且末的问题。在他奉献了24年黄金时光的地方,他反而能忘掉自己是个“病人”。
辛忠起曾梦见过,2000年的自己向今天的他缓缓行来,并露出欢喜又惊讶的笑容——一个有些自卑的农家青年,看到了未来的自己,那么爽朗、自洽,眼中有光。他在且末被学生需要,被无数少数民族老乡需要,这令他心中浮现庄严的使命感,宛若沙丘的落日,那么辉煌、温柔又醉人。到这个年岁,他才懂得老校长段军的话:“跨越3300公里,与沙漠里的少年相遇,你才会知道自己的价值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