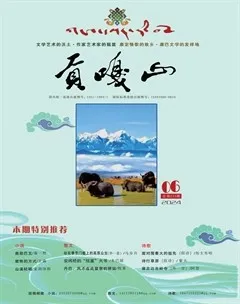幺奶奶
母亲说,昨晚她梦见幺奶奶了。我说哦。母亲又说她看见幺奶奶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声若游丝。我没再吭声。这让母亲有些诧异,以往只要谁提到幺奶奶,就准能打开我的话匣子。
我没告诉母亲,昨晚我也梦见幺奶奶了。我见到的幺奶奶面色红润,神清气爽,一头短发乌黑发亮。她站在自家门前,正眉飞色舞地和邻居聊着天,像极了我初见她时的模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十岁左右。从年龄推算,幺奶奶大约五十岁。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端着小板凳在门口乘凉。一位陌生女子站在我家门前和我母亲有说有笑。她穿着淡蓝色短袖衫,套蓝底白花的半身裙,头发短短的,身材偏瘦,脸上已有了岁月的痕迹,看上去却很精干。母亲让我叫她幺奶奶。我打小出生在小镇上,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的面孔全都熟悉,这啥时候空降一个幺奶奶?我低声叫了她一声。她从衣袋里摸出一颗水果糖递给我,摸摸我的头说:“我孙女一看就挺乖巧,常来奶奶家玩哈。”
我没有见过亲爷爷,奶奶离开那年,我年纪尚幼,完全不谙世事。长到这么大,第一次听到有人唤我“孙女”,我心里顿时涌出一种异样的感觉。
幺奶奶一离开,我就缠着母亲打听她的来龙去脉。这才得知幺爷爷是我爷爷最小的弟弟,早年在外地教书。难怪我不知道家族里还有这一房。母亲说幺爷爷为人忠厚善良,可命运对他却不公。第一位幺奶奶二十七岁就因病离世,幺爷爷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年幼的儿子,尽管有同事亲友帮衬,日子仍然举步维艰。
几年后,第二位幺奶奶进门了。她带着七八岁的养女来到周家,和幺爷爷一起打理这个家庭。
好日子才没几年,那位幺奶奶也突发疾病而去。她带来的养女留在周家,我们后来叫她大姑。
两任幺奶奶都因病去世,坊间传闻幺爷爷属于典型的“克妻”,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人敢给他介绍伴侣了。
幺爷爷和第三位幺奶奶是怎么认识的,我不得而知。后来听大婶说,她的这位婆子妈还挺有勇气的。幺爷爷一个普通教师,拖着四个未成家的子女,她这一进门就得接手一大摊子事。
我后来问过幺奶奶为啥不信传闻,那是拿自己的命在做赌注。“我就觉得他人朴实可靠,跟他在一起,值。”说这话时,幺奶奶已年过花甲,脸上却露出少女般的娇羞。
幺爷爷和幺奶奶结婚后不久,就因身体不适提前办理了病退。幺奶奶随她一起调回我们老家小镇中学工作。
幺奶奶还带来一个女儿,在邻镇读高中,母亲让我叫她小姑。小姑随幺奶奶姓叶。她一直很亲热地叫幺爷爷爸爸。
后来听大人说,小姑的亲生父亲是城里的下乡知青,当年他和幺奶奶在插队的时候好上了。后来那男人返城后再无音讯,幺奶奶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幺奶奶生下了小姑姑,母女俩相依为命。
那个男人可真坏,我小声骂着。母亲说大人的事很复杂。她说幺奶奶以前吃了很多苦头,和幺爷爷一样饱经风霜。难怪他俩组成家庭后一直相亲相爱。
幺奶奶被安排在镇中学从事后勤工作。她性格随和,爱说爱笑,很快整个校园都知道住在校门口那间小屋的是姓叶的老师。小屋不足二十平方米,每天都有教职工排着队来串门。有些年轻老师离家较远,一到周末,幺奶奶在镇上的家就成了他们蹭吃蹭喝的地方。幺奶奶厨艺不精,她经常叫上我母亲去操刀,准备满满一大桌菜。这周末去几个人,下周末又换另外几个人去。我也自然每次跟着一饱口福。
那些年轻老师谈恋爱了,都会第一时间带上对象去拜见他们口中的“叶妈”。
幺奶奶嫁进周家不久,就张罗操办了大叔、大姑的婚事。他们对幺奶奶的称呼从最初的“姨”变成了“妈”。叔叔和婶婶都在偏远乡镇学校工作,带堂弟小宇的任务自然就落到幺奶奶身上。小家伙睡觉最爱说梦话,经常在梦里喊“奶奶,奶奶”。
小宇三岁那年,在家里的影集里翻到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年轻女子,梳着长长的辫子。他好奇地指着照片问他爸:“这阿姨是谁啊?”大叔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好一阵说:“这是你qetLXrB74Kh93cVAIw5cvGZg84M9L+FHbPNPp99egH8=亲奶奶。”
小宇拿着照片飞快地跑去找到幺奶奶说:“爸爸说这是亲奶奶。”幺奶奶看着照片一下怔住了。婶婶赶紧冲过来,对幺奶奶说:“妈,您别介意,孩子不懂事,他只知道您是她奶奶。”
幺奶奶的脸上又绽放出笑容:“奶奶哪会跟孙子计较呢?”说完她又去削苹果,那是孙子小宇最爱吃的水果。
大姑的女儿出生了,逢年过节都会带回小镇。小表妹每次离开都要哭很久,说是舍不得外婆。
90年代初期,小叔从山区学校调回小镇中学。小叔二十六七岁的年纪,在当时也算大龄青年,别人介绍过好几位女子都跟他无缘。这成了幺奶奶的一块心病,她四处托熟人帮忙张罗。不久,小叔和同校的女老师处上了对象。幺奶奶乐坏了,跟我妈一起为小叔操办了婚礼。
幺奶奶的家离我家只相隔几间屋子。那些年我除了上学,其他时间几乎都在她家度过。暑假坐在她家客厅看书、剥瓜子、吃水果,和来访的客人聊天,寒假围着火炉一坐半天。我上大学期间,每年开学前,她都会给我些零花钱。
幺奶奶在小镇生活了十多年,比那些在小镇生活一辈子的人更有影响力。街坊邻居都说叶老师跟好多有工作的女人不同,她随和热心,平易近人。
2000年左右,小姑在离小镇较远的城市买了房。幺奶奶和幺爷爷随她去了城里,帮小姑带小孩,料理家务。几个叔叔和大姑逢年过节去城里小姑家,他们说妈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幺爷爷后来突发一场疾病,被医生宣布医治无效。听母亲说起这事,我赶紧给幺奶奶打了电话。幺奶奶一接起电话就哭个不停。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哭声。
又过了好些年,小姑的婚姻突然发生变故,日子艰难起来,这让幺奶奶心力交瘁,脸上再也难露笑容。她开始刻意疏远一些从前的老友。
大概在十年前,我们一家人开车去城里看她。她的身体渐渐虚弱,见了我不再像以前一样问个不停,只反复说一句:“孙女,喝茶。”她想努力挤出几丝笑容,脸上却全是阴郁。
五年前,年过八旬的幺奶奶随小姑又回到小镇生活。听小姑说,她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度过。
去年元旦,我和婶婶、大姑等一起回小镇看幺奶奶,她已经卧床不起。
我俯下身子将脸靠近她。她拉着我的手,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孙女,奶奶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奶奶,您一定会长寿的,我还等您给我做饭呢。”
她的眼睛顿时变得清亮起来,苍白的脸上有了一丝血色。
一个月后,我正在电脑前赶一份材料,手机嘀嘀声响起,点开看到一行字:叶妈走了。这是二叔发在家族微信群的信息。我早有心理准备,脑子却还是嗡嗡作响。
在幺奶奶的葬礼上,我见到好多当年来她家串门的老师,如今他们也都年近花甲。好多老街坊也相约着冒雨赶到城里的殡仪馆为她送行。
幺奶奶只生了小姑一个孩子,却有五个儿女为她送终。考虑到小姑还有债务在身,几个叔叔和大姑主动承担葬礼费用。他们在老家山上为幺奶奶选了一块墓地。山坡上也长眠着他们的生母。叔叔们还是统一了意见,将幺爷爷和嫁进周家四十年的继母合葬在一起。
幺奶奶曾说过,她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是和幺爷爷在一起的二十一年。如今她又回到幺爷爷身边,这下她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