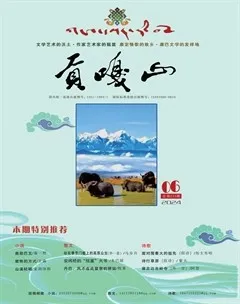塬上


一
小满时节,老家塬上一棵开满白花的高大海棠直立在田野中央,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海棠树的脚下是一条贯穿东西,通向远处的硬化路,此路将整个塬分成两部分,一边是禾本科的庄稼种植区域,另一边生长着木本科的苹果树和梨树。梨树和苹果树的树龄并不是很大,哪怕是最高的树木,高度超不过三米,树冠的直径也不会超过三米。而海棠是继苹果花、梨花悉数落尽之后唯一一棵开花的树,且满树细小的花朵将整棵树包裹成一个硕大的花球。因此在午后阳光里空无一人的塬上行走时,我将这棵树连同树上的鸟鸣声一起分享给远方的友人。
“塬上几乎就我一个人,很享受。”我说。
“塬上——应该是一篇散文。”友人说。
在发现海棠树之前,我在塬上挖了许多苦苦菜,只花了一会儿工夫就铲了满满一篮。农人在其中一块地里种了油菜,可肥肥大大的苦苦菜反倒成了主角,抢了油菜的风头。除了油菜和苦苦菜,地里还长着许多杂草,甚至还盖过了苦苦菜和油菜的风头。很多时候,杂草总是锄不尽,它们在泥土之下蔓延根系,纵横交错,始终处于蠢蠢欲动的状态,只要遇见雨露,在阳光的加持下见疯长,如若农人不维护庄稼而一遍遍将它们腰斩,它们必然会是田地里长势最旺盛的群体。
如今的塬上,除了小面积的油菜和小麦,更多的则是苞谷,和苞谷一起套种的还有蚕豆和南瓜,也有更少数量的香菜和香豆。蚕豆和南瓜会存不同的季节里开出不同颜色的花朵,而香菜和香豆在未开花之前就已经被采摘,成为餐桌上的点缀。庄稼地另一侧大面积的果树在清明时节相继开花,此起彼伏。蚯蚓和鸟雀是田地里的常客,没有蚯蚓和鸟雀的田地是贫瘠的。果树开花时,会有养蜂人从远处赶来,蜂箱一字排开,整个田野的声音变得壮大,养蜂人赶在苹果花凋谢之前离开,去寻找下一个开花点,开着拖拉机远去的背影就像是逐水草而居的牧羊人。
塬下村庄里清晨的炊烟过后,带了馒头、茶水和农具的农人掩上木门,将一把老式的铜锁挂上门闩,顺着一条弯曲的水泥路攀爬,走走歇歇,一步一步用缓慢的步伐往塬上行进。太阳的光线在东边的山岭之后若隐若现,路途遥远且陡,还未开始劳作,汗水已从身体的每个毛孔里迸发,湿了衣背。他们拄着农具做短暂的休息,喘着气喝一口提在手里的酽茶,然后又挪动步伐。有时农人到达田地,庄稼之上的露水还未散去,只好再等。
地里的活儿总是干不完,未到立春时就要给苹果树剪枝,用蜡封住伤口,清明之前还要播种,播种时得考虑倒茬,去年种了豌豆,今天就种小麦,若是去年种了油菜,那今年就种豌豆或洋芋,总之,不能一成不变。如果违背播种规则,一意孤行,即便农人将同样多的关注给了它们,它们不会反馈于农人同等的收获。
塬上农人忙碌,塬下村庄同样也在繁忙之中:会有公鸡不分时段的打鸣声,有驴子不明就里上气不接下气的叫唤声,有鹞鹰追击鸽子落在屋顶时噗噜噜的声音,有一两只小羊在巷道里撒欢奔跑时的嗒嗒声,时而还会有几声隐约的叫骂声……这样的声音从村庄深处传递到塬上,再从塬上的阡陌小道传向四面八方,犹如一场混合了祝福和诅咒的暴雨。
午后,村庄也会响起叫卖声:“黄瓜,菜瓜,茄子,辣子,洋芋,西红柿,卖菜了,便宜了。”那一连串起伏的声音像是秋天悠长的午后有鸽子在屋顶飞过,携带的哨音在树梢间流淌回旋。小贩售卖的都是农人地里种植且唾手可得的品种,因此,短时间内拖拉机“突突”的声音和叫卖声消失在村庄的边界。
二
立夏时,塬上果树的花朵悉数落尽,有着细小绒毛的青色果实挂满枝头,就像是出生不久的小婴孩还未褪去胎毛。几经风雨后,绒毛消失不见,在寒露之前,果树进入漫长的孕育期。
其间,农人所有做的事情细小繁复:浇水、施肥、修枝、打药、锄草……似乎,他们的工作没有尽头,尽头的尽头依然是劳作,只是,看到果实日渐膨大,他们喜形于色。即便有那么一天,地里实在没有要干的活儿,他们也要在田间地头转一圈,这样心才能被装满。
有时,在工作的间隙,他们会站到一起互相吹捧:“看你家的富士苹果长势那么好,今年肯定会有一个好的收成,口径至少在十公分。”
“再怎么也比不过你家那棵高大梨树上软梨的产量,那棵梨树从来没有歇过气,去年一斤软梨的价格有一元八角,今年肯定还会再涨。”
“富士苹果好储存,即便卖不出去也不会烂掉,不像软梨,到期如果没人要就全烂了,满地都是黄葱葱儿的软梨,看着心疼。”
“老天爷长着眼哩,不能白白糟蹋我们的劳动成果。”
但有时他们也争得脸红脖子粗,寸步不让:
“你说塬上就这一股水,大家都是交了水费的,凭什么让你浇那么长时间?”
“我这是三亩地,比你的两亩地要大吧,凭什么浇水的时间和你一样多?”
“总不能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吧?我能等你,但是庄稼不能等,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庄稼在我的眼皮底下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
“你要是敢截我的水,我就敢豁上老命。”
他们惊心动魄的吵嚷声惊动了整个村庄,剑拔弩张的气氛似是一场杀伐迫在眉睫。村支书闻讯赶来,给怒目相向、一触即发的两人各敬一支烟,然后拍拍他们的肩膀,他们便各奔东西。
他们也热衷于嫌弃别人荒掉的庄稼:
“你看张三的地里全是杂草,也不知道他整天在干些什么。”
“是呵,我们又不好当着他的面说,过不了几年这地差不多就荒了。要是我们侍弄了一辈子的土地最后都长满了杂草,回去怎么和先人们交代,会被骂死的。”
他们嘴里的“回去”是指死亡,“回去”后他们会被埋葬在塬上事先选好的一块地里,他们长眠于此,和终身劳作的土地融为一体。他们回去时会有哭声悲恸,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哭声销声匿迹,代替哭声的可能会是漫不经心的嬉笑声,但每逢重大节日时也会收到上亿元的纸钱,回去后的他们肯定不愁吃穿,过着天天有余的生活。
走在蜿蜒水泥路上的农人多半都有着佝偻的背和缓慢的步伐,他们和农地一起成长,将自己的青春长出纹理,长出褶皱。他们的孩子几乎都离开了村庄,孩子们有时也奉劝自己的父辈:算下来那几亩地的收成根本都不能保本,你两头不见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根本就不值当,不如坐在巷头里晒太阳。
“你懂个啥?”农人忿忿地说,根本不想接他的话茬儿。
“不然我接你去城里享几天福,你这整天灰头土脸的。”农人的孩子又一次开口劝。
“我才不去你鸡笼一样的楼房,出门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让我闲闲坐在那里不生病才怪,你以为你是接我去享福,实际上是让我受罪哩,你看我地里的庄稼和蔬菜,哪个不比你精神?”
因此,他们依旧在合适的时间种植豌豆、玉米、土豆,在缀满果实的苹果枝末端绑上装有泥土的矿泉水瓶,以便将苹果枝压弯,减去瘦小的果实;端午时节,给抽穗的麦子追肥,拔去一两棵混在麦苗中的燕麦;当洋芋开出花朵时,提一把老锨,细细地壅土;豌豆结出豆荚时还要提防邻家的小孩采摘豆荚,拉断豆秧;麦子成熟时,要赶在雷雨之前将麦捆摞成麦垛;在寒露前夕,要搭着梯子将高处的软梨摘到竹筐里,并用板车运到收购站;霜降之后要将树上有了糖心的富士苹果悉数采摘。
他们兴高采烈地走进盛大的秋天,再筋疲力尽地从盛大的秋天走出来,好在漫长的冬季给他们养精蓄锐的时刻,可是也有一些人在一个冬季的早晨离开,画着龙的棺材在寒风里,在雪地里,在别人或真诚或假意的哭声里向着塬上前行。
三
塬上长着各式各样的野菜。
最先露出地面并开出黄花的是蒲公英。记忆中的蒲公英是喂猪的好食材,春天的蒲公英开得满山满洼,不出一小时就会铲到一背篓,猪将拌了麸皮的蒲公英吃得砰砰作响,吃了蒲公英的猪长得壮实。后来,蒲公英成了药材,药店里的蒲公英可以消炎、杀菌、清热解毒,因此以往的猪食变成了人人卖钱的药材,满村庄的人从早到晚流连在塬上,找寻长得壮实的蒲公英。之后会和前来收购蒲公英的小贩讨价还价,拿到为数不多的钱币。人们喜形于色,每个人的内心都生长着一片茂盛的只属于自己的蒲公英。当蒲公英成为城里人饭桌上神往的野菜时,它变得高贵而稀少。塬上的蒲公英还未完全展开时,四面八方的人涌向这里,他们驱车百十公里的疲惫在见到蒲公英开出的鲜亮黄花时一扫而光。但是,即便他们在春季将整个塬上的蒲公英以地毯式搜索,仍有白头的蒲公英春天之后就在风里吟唱,并将种子撒落在塬上的任何角落,甚至飞向塬以外的广阔土地。
紫花地丁如同村庄里包着头巾的村姑,极尽朴素,清明时节在塬上一隅小模小样地开出几朵淡紫色的花朵,很容易被路过的人忽略。实际上紫花地丁也是可供食用的药材,只是和蒲公英相比较就显出不被重视和广为人知的冷落,一个像是受宠的贵人,而另外一个则是常在。当然,有种喜爱也是因人而异,谷雨时,久居城市的友人回到乡下兴高采烈地发信息给我:“我要把田间那些紫花地丁挖回去栽种在我的花园里。”
大多生长在田间地头及路边的野菜都有着差不多的命运,除非有毒,否则就是喂猪喂羊的好材料。叶片厚实、坚韧的车前草也难逃此运。不知车前草的姓名因何而来,我亲眼看见载重的木板车从车前草身上碾过,它依旧是完好无损的模样。而一只羊从它身边经过,它必定残缺不全,甚至连根茎都被拔出。后来在中药木柜的表面写着中规中矩的毛笔字:车前子。原来车前草的种子也是中药,瞬间觉得以往灰头土脸,被板车碾压,被羊群啃食的车前草登了大雅之堂,且正行进在治病救人的道上,岂是鲤鱼跳龙门所能比拟的。
HQLZSxMEJ7eOQf9nzDE2vOdpLLQ9pjfOWbbN7EN7hWs=塬上无边空旷,盛放寂静。麻雀倒是很多,风一样飞来飞去,时而落在被称为防风的植物脚下,不知道在啄食些什么,之后又跳起来飞去别的地方。通常情况下,防风长势旺盛,叶面在茎秆上散开,伸向四面八方,叶片翠绿多汁,如同被水浸过。防风无疑也是中草药的一种,具有解热镇痛、抗菌消炎等疗效,但农人却喜欢叫它们马缨子,将马缨子水嫩多汁的叶片采来做凉菜、包饺子,都是令人垂涎的佳肴。因此农人在田间地头行走时,眼睛总是不自觉地向方圆百米内的距离张望,眼神里盛满了希冀。
塬上还有药方中不可或缺的甘草,它将细长的根深埋于泥土之中,常常在秋收时被喜欢香甜味道的孩子们发现。他们拿着铲子奋力地将地面挖得面目全非,即便掘地三尺,也不一定将甘草的根部全部挖出。他们会将挖来的甘草晒干,再折成火柴梗长短的长度藏匿在木抽屉里,以便开学后泡水喝。当然这些事情发生在早期物资匮乏的时候,发生在我这般年龄的人身上,现代的孩子忙于学业和游戏,鲜有时间去辨识甘草和洋芋,他们见识的甘草存在于治疗咳嗽的甘草片和甘草合剂中,小颗粒的甘草片呈现黑黄瘦的状态,很难和长在山岭里翠绿植物相联系。
除此,塬上还有坟地、草莓地、石块地里的豌豆,也有丰乳肥臀的牛蒡和骨瘦如柴、长满小刺的飞廉,有泛着银色叶片的灰灰菜,开着细碎黄花的芥菜。土地时而湿润又时常干涸,农人时而绝望又长时间充满希望。昆虫担负着传粉酿蜜的责任,又经常命殒意外。一场雨后,蚯蚓在泥土里打滚,杂草和庄稼齐头并进,麦地里未择干净的燕麦像一面面耀武扬威的旗帜。夏天有时HQLZSxMEJ7eOQf9nzDE2vOdpLLQ9pjfOWbbN7EN7hWs=焦渴,有时又大雨倾盆。当炽热的温度炙烤大地时,焦黄的榆树叶卷起为刚到世间的小虫遮风避雨;当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雨来袭时,纤细的麦秆如波浪般倒伏。很多时间里,农人会用干涩的舌头舔舐干涸的嘴唇,有时半张着嘴,露出深紫色牙龈和黄色牙齿。
不管有没有用,他们会在地边绑一个长袖善舞的稻草人用来吓唬日渐增多的鸟雀,鸟雀有时也站在稻草人的肩膀上左顾右盼。
四
没有人知道塬上之前的高大梨树存活了多少年,哪怕是村庄里最老的人,也说不清这些梨树被何人栽种。他们说,从他们记事起,梨树就这般大小,后面几经分配,便都有了自己的主人。
大概这些梨树已经正式进入暮年,有些枝丫显露出干枯的状态,果实小而多渣,秋后的收益已经无法和农人的劳动付出相匹配。也有些梨树整个树体彻底干枯,在土地中央日夜站立。一棵干枯的梨树以黑黢黢的躯体立在大地中央,似乎进入比生更漫长的无花无叶的枯木,因此看上去比活着的梨树还具有存在感。但很多梨树被砍伐,原因是日渐老迈的梨树既不能带来经济效益,还会影响别的农作物生长。农业不是墨守成规,也不是坐以待毙,是敢为人先,是革故鼎新,因此要把原来存活了几百年的梨树砍掉,新成立不久的合作社要在原址种上大黄和黄芪,让整个塬的效益得到大的提升。
电锯的声音在塬上弥漫成一片,似乎有些力量生来就有着无可抵御的震撼力,高大笨拙的梨树一棵接着一棵沉重地倒下,在和大地接触的那一刻发出沉闷的叹息,之后进入无边无际的寂静。有人兴奋并憧憬,也有人愁苦并惋惜,惋惜的人站在距离稍远一点的地方舔舐着干裂的嘴唇,用佝偻的神态目送一棵树的离开,似乎在一场葬礼上看见了自己死亡的样子。叹息的声音很快被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掩盖,合作社雇来的劳力在土地里一字排开,进行着一场声势浩大的劳作,塬上很久都没出现过如此繁盛的场景,那些曾经在田里劳作的人,成了站在边上看风景的人。
塬上的梨树被不同的新物种替代,村庄里存活的为数不多的几棵梨树被有心人标价买下。梨树的原主人收到梨树为他带来的最后一笔财富时很是惊愕,想不到一棵濒死的梨树还能有这么高的价值,而且那人也明确表示梨树还会在原来的地方,不会因为买下它而将它移走,这摆明了就是白拿了一笔钱。他的行为,令很多人匪夷所思。
那些没被砍伐的高大梨树和新栽的药材一起成长,因为药材的长势和价格时好时坏,合作社主人的表情也是阴晴不定。无论怎样,药材的经济效益立竿见影,塬上日渐热闹。他们高谈阔论,眼界高远,理想丰满,商量在塬上建一个药材加工厂。而村庄里的梨树看上去和之前没什么两样,树冠的面积、树干的直径和树木的高度几乎没什么变化,但它们依然顺应节气完成自己的使命:开花,凋谢,结果,掉落。有人专程为它们浇水,施农家肥,不知什么时候又有人在树身上绑上哈达,每到节日还会献上水果和酒水,再后来,为它们修建了栅栏,栅栏旁边还栽种了月季,因此,老迈的梨树又成了村庄里鲜活的风景。
种药材的老板在售卖完最后一批药材后召集了村庄里为数不多的老人,他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餐食。老人们感激涕零,从没有一个陌生人为他们慷慨解囊,承包土地的药商感慨更多:“种完今年我就不种了,这三年多产出并不好,当初将那么多梨树砍伐,实在是罪过之举,我的收益出乎想象也在情理之中。好在我及时醒悟,留下为数不多的高大梨树,为表赎罪的决心,打算将它们守护到底,从明年起我就将土地交还给你们,你们该种苞谷就种苞谷,该种豌豆就种豌豆……”